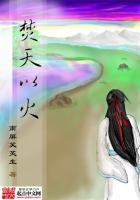琼州东南海岸棕榈树处处可见,楚浩把那里的灯塔命名为棕榈塔,海湾命名为棕榈湾,住处叫做棕榈台。
到琼州三个月,楚瀚仍然没能为大型海船找到新的动力。
他们在一个山坳的沙滩上实验了很多种方法,试验基地时而传来巨响,时而冒出浓烟,时而闪着刺眼的光,尽管阿吉丽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楚瀚曾经双目失明,她仍然时刻担心他的安全。
今天楚瀚他们要去一个无人岛上做实验,不用问阿吉丽也知道肯定很危险,她默默帮楚瀚把衣服穿戴整体,又帮他带了一个防晒的棕榈叶编制的帽子。
楚瀚顺势抱住她:“放心,鼓捣多年,都是经过计算的,不会有事儿。”
“我可以想见是什么情景,否则怎么会去无人岛,你呀也不用安慰我,自己当心要紧。”
楚瀚去了无人岛,连楚浩都焦急地在海边等。
冬季少雨,琼州依然湿润,他把燕西也叫来散散心。
天气凉爽,棕榈林子下面放了胡床和长榻,楚浩亲自手动研磨,准备茶水。
“阿吉丽应该不会来了。”楚浩说。
燕西点点头:“阿吉丽过于担心,不敢看。”
此次来琼州,楚浩把母亲和弟弟们都接了来,他和燕西难得单独出来。
楚浩盯着无际的大海,小心翼翼地问燕西:“去年我去东罗马,你的哥哥来找过你?”
武三思是燕西唯一的亲哥哥,常来常往不足为奇,燕西知道楚浩指的是什么。她把手里的杯子放下,也盯着远处。
她的病不单是因为楚浩和耐尔洁,不单是因为产后抑郁,楚浩和她同样清楚,只是楚浩考虑到她的病情,一直没有问。
“此去两京数千里,你我还需要隐瞒吗?”
“找过。”燕西承认道,海风吹过她的头发,在风景优美,温度适宜的地方,忧烦的事情瞬间让人僵硬。
楚浩收回目光,落到燕西的脸上:“为了太后夺权?”
燕西艰难地说:“他们要想拉拢你,利用兑柜和生意的线索追查李唐宗室的反叛证据。”
“太后当政,剿灭宗室是迟早的事儿,况且并非从今春就开始的。”
“宗室惨烈,西汉吕后专权,诸吕下场同样可悲。你我皆处于核心,纵然跑到琼州,小溪、二哥、新父、新母都在两京。我虽然不支持武氏,可他们毕竟是我的兄弟。”
对燕西来说,讲出来和不讲出来一样令人绝望,楚浩纵然再有能力,面对皇权更替,他也只能躲避。
***
寒风刺骨,茵儿一出国医塾,就被吹的浑身凉透,到大门口上了马车,楚岳居然坐在里面。茵儿瞪大眼睛,还没说话,楚岳就拉她坐下,紧紧抱住。
他差不多两个月没回来了,行踪不定,常常来不及当面告别,就出京城了。
茵儿感觉手上沾到什么,粘稠的,职业敏感,她嗅到了血的味道。
她想抬起头问他,他把她抱得更紧。
“嘘,回家再看。”
烛光下,楚岳的左耳后到肩胛皮肉翻开,包着的白色围巾粘连上去。茵儿立刻去取药水,轻轻化开血痂,把围巾拿下来。
兵器的伤口在京城不多见,茵儿处理的不多,城中宵禁,现去国医塾不太可能。她小心翼翼缝合伤口,控制着不让自己掉眼泪。
“夜深了,睡吧,明天你还要去教学。”楚岳歪靠在胡床的一侧,哄她说。
茵儿从不过问他的差事和职务,他偶尔有个擦伤,都无大碍,可这次是在脖子上,差点伤到筋骨,作为大夫,她想要嘱咐的太多,却只能默默守着。
“我想回到长安的昆士牧场,画上浓妆,在滑稽戏里面演一个角色、自己设计的角色。”
“我们都在滑稽戏里,虽然没有画浓妆,却戴了整套的虚假外壳。”茵儿帮他掖了掖被子,安慰他说。
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楚岳已经反复衡量多次,这和两国打仗不一样,皇上的儿子还是皇上的妻子,他要选一边,那么另一边的人则要付出血和生命。
他努力挪了挪位置,痛苦道:“我真羡慕你的职业。”
“大夫能够保持中立,是因为国家太平。”
楚岳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又出了城,告诉茵儿腊月之前回不来。
腊月十五这天,茵儿回家,丫鬟交给她一个铜牌:“将军说请夫人到洛泰楼相见。”
茵儿不禁笑了,他们也算老夫老妻了,还玩儿这种浪漫,而且茵儿从来不去酒楼那种地方,楚岳应该知道,不过既然是邀约,又是自己的丈夫,茵儿还是装扮起来去‘捧场’。
洛泰楼属于楚浩的产业,早先由玛瑞娜帮忙打理,现在不知道轮到下面哪位“口”字辈的小兄弟经营。进出的都是有身份的人,不是谁都能拿到铜牌。
作为大唐的女医长,京城的名媛贵妇几乎都见过茵儿。单独去看病是一回事儿,在酒楼这样的场所见又是另外一个场景。她们聚集到一起对茵儿指指点点。
“看,是那个女大夫,知道吗?她是个孤儿,没身份、没地位,居然做了定远将军的正妻。”
“哎吆,是吗?要摸样没摸样,要身段没身段啊,看她穿的,就是个男人的袍子啊。”
“哈哈,跟她走路的姿势倒是很搭配,楚家兄弟两个在两京可是出了名的帅气,又是太后身边的红人,怎么一个娶了郡主,一个娶了个孤儿?”
楚岳在二楼看到茵儿,也看到那些长舌妇交头接耳议论,此刻的他早不在这种事情上假清高了。茵儿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想要什么,某些方面,她就是楚岳的主心骨。
他眼里的茵儿充满着知性的魅力,尽管她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却自信从容,正是他想要的样子。
他走下来,把茵儿接上去:“是不是很惊奇?”
“是的,为什么?”
“放松一下。”
二楼屋顶整个被包厢围了一圈,中间的下沉舞台上铺了乳白色厚地毯,有三个入口可以通向舞台,还有一个口通向正门。
台上正在表演的是江南特有的梅花舞,音乐婉转悠扬,服装多彩,舞姿曼妙。
“葡萄酒给我的夫人,再加一坛米酒和两份羊排。”楚岳吩咐酒厮。
“好的,记下了。”酒厮小声说道,然后轻轻退下。
歌舞轮换登场,楚岳和茵儿杯觥交错,很是尽兴。
“我以前常去青楼,浩开得这家携夫人来很合适。”
楚岳举杯看着茵儿,余光扫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不动声色把酒厮酒厮叫来,加了菜,悄悄压了个纸条在空盘子地下。
不一会儿,那边包厢就被官兵控制起来,有一个人从包厢跳到舞台,向西南出口跑去,楚岳用酒杯遮挡,给那边的官兵指了方向。
茵儿刚要扭头,楚岳揽住她的肩,在她耳边悄声说:“不要看,喝酒。”
当晚,楚岳喝的烂醉,茵儿也微醺,夫妇两人住在道德坊的驿社里。
早上,楚岳不在床上,茵儿坐驿社的马车回家,换了衣服去国医塾。
丫鬟跟她讲说:“夫人听说了吗,昨晚就在道德坊西边隔壁的道术坊,殿中监裴承先被杀死在街上,据说是从道德坊的洛泰楼跑出来的,夫人可有看到?”
“洛泰楼那么大,跑出去一个人,谁能注意到啊。”
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儿,茵儿当然能看到。
楚岳说的没错,他如果能被派往突厥边境,突厥一定不会那样张狂。可偏偏太后要把他留在身边,那么李唐宗室只能倒霉。
***
小太监三羊从来不给太后身边的人送任何好处,他只说好话,告诉他们怎么得到好处。
这是徐昭蓉教育小溪的,不能让太后发现她们在贿赂太后的人,那样非常危险。而且以太后对小溪的喜爱程度,小溪也无需贿赂,宫女、太监巴结还来不及呢。
三羊到了观风殿,问清楚了情况,正要回去请小溪主子来,太后身边的太监叫福海的从大殿出来,见到三羊,忙喊道:“羊,羊,太后命我去请熙郡主,你给领个路呗。”
“好啊,这会儿熙郡主正在上林苑。”
两人边走边聊,到了上林苑,小溪却去了明堂北边的工地。
薛怀义不在工地上,小溪让工地的头子给她搬些木头到上林苑,在上林苑最大的一棵树上建一个木屋。
工地的头子为难道:“这,这要经过堂使的同意啊。”
小溪很不高兴:“难道堂使会不答应?”
“不,小的不是那个意思,小的是说堂使同意才能送过去。”
“既然不是那个意思,堂使也会答应,那就现在送去吧。”小溪扬起下巴。
三羊跑过去,禀报说:“郡主,太后陛下有请。”
小溪转身又看了看工地头子。
工头无奈道:“好,好,小的这就差人送去。”
“算你明白。”三羊冲工地头子甩了甩拂尘。
小溪到了观风殿,确定里面只有太后在,她便爬到寝阁的热炕上,挎住太后的胳膊:“小溪见过太后姥姥,太后姥姥万岁。”
“呵呵呵,小溪的礼仪学的很好嘛,这是打哪儿来,手怎么这么凉?”
小溪吐吐舌头,把手捂在铜炉上:“姥姥,日本国来访的公主说话绵软极了,实在太好听。小溪想学。”
“日本国公主是来参加正月朝觐的。”
“万象神宫大飨?”
“是啊。姥姥可以另外帮小溪请一位师傅教就是了。”
“师傅,不要了吧。小溪可以和日本国的公主做朋友,在上林苑的树上建个木屋,我们在木屋里玩儿……”
“小溪?”
“好吧,好吧,我去工地要了木头,让他们先送到上林苑了。”
太后摇摇头:“先斩后奏。哎哟,你整天搞出多少事情啊?姥姥想起来了,姥姥叫你来是要问你昨天偷偷出宫,干什么去了?”
“不是小溪来看姥姥的吗?”
“小溪玩疯了,哪里顾得上姥姥。”
“前天刚来过啊。”
“姥姥问昨天。”太后放下手里的毛笔,盯住她。
“昨天,昨天小溪去了太平姨母家。”小溪凝重道:“姨母很伤心。”
“因为驸马吧?”
“是的。”小溪凑近太后:“让姨母更伤心的是连驸马都背叛了太后姥姥,姨母说驸马姨丈父母双亡,太后姥姥对姨丈视如己出,姨丈这样做,太后一定很痛心,姨母心疼太后姥姥,小溪也心疼。”
她钻到太后怀里,抱住太后。
小溪没有见过太后落泪,今天她却哭了:“我的孩子,你们才真正是朕的孩子!”
正月大飨,太后专门邀请了太平公主。
可太平公主还在气头上,她非但没有给送懿旨来的太监打赏,还让太监在冷风里等着。幸亏玛瑞娜在公主府,忙把太监请到内厅。
“公主染了风寒,新府邸的下人们不懂规矩,公公莫怪。”玛瑞娜说着,让汪嫂给太监一包钱。
“哪里,哪里,太后的嫡公主只有一位,杂家也是公主的奴才呢。”
玛瑞娜不接他的话,问道:“公主的心情想必公公也知道,万象神宫大飨恐影响太后陛下的兴致,公主不如去上元日的家宴。”
“好,杂家回宫会跟太后讲明白。”
“多谢公公!”
宫里的太监好对付,让太平公主振作起来去见太后,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尽管小溪和玛瑞娜绞尽脑汁,公主仍是铁板一块。
公主和太后需要解开这个疙瘩,最起码表面上要保持和谐。
“我把孩子抱到一旁,夫人再跟公主谈吧,不然,公主拿孩子说事儿,夫人不好劝。”汪嫂说。
玛瑞娜捏了捏太阳穴,点点头:“换做是你我都做不到,贵为公主却要忍常人所不能忍。”
太平公主最近常常出神儿,薛家兄弟三人一个不剩,全部被杀,奇怪的是她此刻想的却是薛氏族长的话。
嫁给薛绍的时候她还小,不懂族长的话是什么意思,看来当年族长并非过度揣测。
如果驸马八年前就掺杂在反对太后的阴谋中,那这八年的婚姻是真情还是利用呢?
驸马在男女问题上没有做过对不住公主的事儿,政治上呢,算不算是对婚姻的背叛,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背叛,她们的婚姻彻底是个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