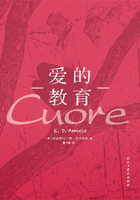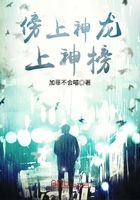清明节是个伤感的日子,这种哀婉凄凉的气氛,被唐朝诗人杜牧的那首七言绝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如断魂;翻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渲染得淋漓尽致,以致清明节的前后几天,不由得人人心生思亲念祖情怀——其实,清明节祭扫英烈和先人陵墓,缅怀他们为国家和后人付出的心血与汗水,乃至最宝贵的生命,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对于逝者是一种思念和告慰,对于生者是一种传承和寄托,皆属情里之中。
然而清明作为传统节日,各地的风俗民情必然独具一格,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雨”。以我们蓬莱为例,地域不过千余平方公里,东南西北的习俗亦有差异,但大体上是清明节前四天祭扫新坟,前三天祭扫旧坟,前两天给坟墓添土,前一天为寒食节。寒食节旧时家家户户禁止动烟火,据传这是为了纪念春秋时代晋国的介子推。史载,介子推曾追随晋文公流浪国外,后晋文公归国赏赐随从近臣,唯独没有封赏介子推,介子推遂和老母隐居于绵山之内,晋文公为迫使介子推复出,便下令放火烧山,但介子推最终被烧死也未曾露面,这一天恰是清明节的前一天。寒食节不动烟火这一旧俗虽早已废除,然介子推的故事却流传至今。清明节当天,机关学校祭扫英烈陵园自不必说,近几年来民间百姓为父母先人树碑植松、游子归家拜祖谒宗之风也日渐兴盛,这并非封建迷信,而是太平盛世人们追根溯源的一种善举。试想,连自己的“根”都忘记了的人,不管他(她)的官职有多么显赫,家资有多么豪富,恐怕也要被草木之人嗤之以鼻的。
在蓬莱的清明节民俗中,有两个习俗令人称奇,尽管现在早已淡化,甚至不复存在,但它毕竟作为一种地域风情而存留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一是清明节这天,新婚的媳妇不能在婆家吃夜饭,主要说法是姑娘初嫁,公婆视若己出,待如亲女,表明婆家今后绝不会拿媳妇“当牛作马”使唤。这一习俗似与另一习俗紧密相联,即清明节这天,农家有给牛马驴骡喂高梁米饭的风俗,此举谓之“打一千,骂一万,不忘清明节一顿高梁米饭”——其实这很好理解,过了清明节,春耕便开始了,一闲了一冬的牲口,就要从早到晚地躬身于各种繁重的农事劳作之中,这个时候喂它们一顿高梁米饭,既有主人的“犒赏”之情,又有主人的“祈望”之意,即企盼牲口身强力壮,甘为主人的农事出力效劳,这无疑是老辈农耕时代遗传下来的习俗,而现在乡村中的牲口已不多见,替而代之的则是各类农用机械,这一习俗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但如果将这两种习俗连在一起看,农家祖祖辈辈渴求的“家庭和睦,人丁昌盛;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便是令人神往的无比美好和温馨。
至于人们清明踏青,阅春光秀色,品自然情趣,现已成为国人的一种“时尚”,更可谓各具特色,千姿百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