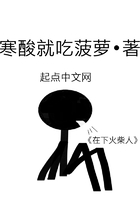星河一愣,脑海中一道黑色的人影形象闪过,他隐没于黑夜,眼睛血红带着疯狂;他的存在于刹那,诞生和消亡不带一丝云烟;他的生命短暂,却又什么都想得到;他是黑夜的过客,理性与欲望的矛盾体。
星河不知道为什,听到赵高缓缓吐出那个字时,心中莫名一惊,脑海中突兀闪过一道黑影,又很快淹没与无形,那道黑影让他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不禁脱口而出,反问赵高。
“人?”
赵高眼神在深邃,一双眼,眉骨不高却又迥然有神,目光死死望着远处密林,逐渐拉长。
星河顺着赵高的视线望去,密林深处依稀可见斑驳交织,漆黑的魅影在其中悄然窜动,处处透露着诡异,那是未知的危险,那是断谷的禁地,即使赵高自己也不敢轻易涉足。
星河有种想逃离这个地方的想法,如同种子,播种后便不可遏制的疯狂生长。
“怕了?”
赵高看着星河似笑非笑,他看到了星河眼中畏惧!畏惧不是丢脸的事情,这世界,弱者本应畏惧。
远处林中的黑影,应该是是影狼,它在林中窜动,如果推测不假,应该在组织着一场狩猎,黑夜是它们的世界。
赵高面露回忆之色,有的时候,相比面对思量着牙齿硬度可以咬不咬得动自己的野兽,他宁愿对手是野兽,而不是叵测的人。
没有任何动机,或可因为任何原因,便会在背后捅刀,相互赖以生存,却又相杀,很矛盾,很可笑?
“人心叵测!”
这是赵高的回答。
他说完,手不由自主的摸向了自己腰间,那里有把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武器,一把已经快磨废了的铁质打柴刀。
似乎只有当手触碰到腰间柴刀,才能让这个魁梧的大汉拥有安全感。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和小妹生活在这里,不愿意出去吗?以至于被困在这座牢笼。”
赵高目光注视着星河,星河被赵高的目光注视,颇感不适,如同智障儿童被长辈用关爱的目光注视,那种感觉,有点让他不舒服。
赵高盘膝不动,右手抽出腰间破柴刀,搁置于前,火堆里射出的火光照耀下,柴刀显得格外漆黑,那是岁月的斑驳,树脂的侵蚀,斑驳太多,以至于让它褪去了原本该有的颜色。
虽然刀身破败不堪,但是其刃口依旧锋利如初,在火光的摇摆下,闪动着深寒,代表着它依旧可堪一用。
“十年前!十岁的我,背着四岁的小妹逃离了西河镇!”
星河看着面前的大汉自诉,盯着赵高瞧了又瞧,大哥!你这么说,现在你才二十岁?
大胡子加豹子头,横向肥膘,这坨肉,估摸着有两百来斤,以目前35块钱一斤的猪肉价格来算,少说也得3500块钱吧……完全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四十岁的黑脸张飞,你说你才二十岁?
星河再次确定赵高的年龄,吐槽不已之余,赵高的叙述却未停止。
“那些熟悉的面孔一个个远离,水灾淹没了大半个西河镇,死了很多人,我带着小妹在山上割蒿草,侥幸躲过一劫。死了!死了!都死了!家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母亲,父亲,奶奶他们都不见了……”
赵高叙述着,眼中回忆之色渐浓,这个多年以来未曾流泪的汉子眼中亦有水雾滚动。
听到这里,星河不由一呆,无意识的瞟向旁边小手抱着蛤蟆的赵灵涵,发现这个女孩正悄悄摸着眼泪。
是啊!自己,和她们待在一起,也才几天,这个女孩却对自己那么好,说到底,赵高这个人表面上凶了一点,其实骨子里也不坏,就是动不动就给自己来一下立威,好像欠了他千八百万似的。
“光是如此,我亦可以带着小妹在西河镇生活,我家有五亩地,可以勉强维持,可随之而来的铁蹄,打破了所有的规划,我才知道,原来这洪水是人为的……”
赵高恨恨,紧握拳头。
战争是不折手段,作为弱者的贫民,只能充当战争的牺牲品,铁骑的践踏者。
星河听了赵高话,内心亦有所触动,他虽不是历史专业,但历史成绩从小到大一向很好,是啊!纵观古今历史……死在人类自身战争中的同胞远远高于自然消亡,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不对劲!”
赵高一惊,乍然开口。
星河被赵高话惊觉,打破了沉思,一脸茫然的看着赵高,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