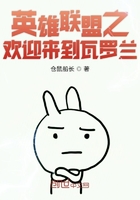曾涛柱在中午大概两点钟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打电话的是个陌生的女子。这女子粗声怪气的对他说:“某天某时有人亲眼所见,你往金茉莉的小灶里下了毒,想知道此人是谁,一小时后杨柳镇得顺楼二楼三号单间见。两根金条可得平安,机不可失,请珍惜。”曾涛柱年近四十,方头大脸,个头较猛,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完这个电话,前思后想,在屋里走了好几个来回,抽了好几颗香烟,最终他自语道:“难道是她?”于是他赶紧走出办公室,去后勤处问了一下炊事班的刘文华上班了没有。后勤处代理主任老金说:“她一共请了七天假,后天上班儿。”曾涛柱又问:“其他几个女同志,都谁没在班上?”“都不在班上,有事吗?”老金答完便问。曾涛柱愣了一下:“哦,没事。你忙你的。”曾涛柱返回办公室,坐立不安,一脑门子的焦灼。
母亲无凭无据,觉得大张旗鼓逮捕曾涛柱,万一他死不承认,势必不好收场。于是他叫马笑天返回白古屯,把那年生叫上,三个人一起去了杨柳镇。
马笑天和那年生茫然不解,不知母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等到了杨柳镇,他们进了德顺楼饭庄,屋内只有一个跑堂的。
马笑天迫不及待的问:“你把我们带到这来,不会是只是请我们吃顿饭吧?”
母亲冲马笑天挥了挥手,马笑天没追问。看着母亲很客气的跟这个跑堂的说:“我们是军管会的,配合一下,给我们找个包间,我们借用一下。”
那跑堂的愣住了,脸上略带疑问。马笑天亮出证件,对方立马一脸笑容:“行…行,楼上有包间,我带你们去。”
母亲说:“你先带他们上去,我打个电话,随后就到。去吧,别愣着了。”
马笑天瞅了瞅那年生,两人茫然的上了楼。
母亲刚打完电话,跑堂的下了楼,母亲对跑堂的严肃的说:“我们在等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来了,问起你,你就说是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中年男子,记着,不要多说一个字。”跑堂的神色慌张的点了点头。而后,他把母亲送到了楼上三号包间,点头告退。
马笑天脸都憋红了:“你给谁打的电话?到底想干什么?”
母亲把手一挥:“先别打听,事不宜迟,你们马上把车藏起来,不能停在门口,顺便给我买件长衫、礼帽、墨镜、假胡子,快去。”
马笑天略知其一,母亲这是想跟什么人接头?于是他冲那年生挥了挥手,便紧着下楼去了。大概过了二十分钟,马笑天拎着母亲需要的物品和那年生上了楼。母亲正在聚精会神的看她的笔记本。本子里都是通过那年生给她提供的详细的审问记录。她着重分析炊事班所有人面对专案组一问一答的每句话。
炊事班刘文华在自己家里接待了以那年生为首的专案组调查人员。那年生问她:“除去炊事班的人,都有谁接近过金茉莉的小灶饭?”
刘文华回答:“如果监狱长算一个,就他和于主任没别人。”
那年生再问:“他们两个是谁先到的炊事班?”刘文华回答:“让我好好想想,嗯…应该是监狱长吧。对,没错,就是他。”刘文华的所答,在母亲看来,这些人是在暗示那年生是曾涛柱下的毒。也就是说,刘文华只偷看到曾涛柱往金茉莉的小灶饭里下毒,并没看见于得水下毒。母亲确定了刘文华是唯一的目击者,曾涛柱杀人灭口已板上钉钉了。母亲这次要让曾涛柱不打自招,所以,她才出此下策。索性假扮敲竹杠的,直接给曾涛柱打电话,揭开他投毒秘密,促使他自投罗网。此刻,母亲才把来此意图全都告诉了马笑天和那年生。
没等马笑天说话,那年生有点火了,压着嗓门儿说:“简直胡闹,曾涛柱是什么人?长了毛比猴还精,他怎么可能上你这种小儿科的当?”
母亲说:“对付这种老谋深算的人,往往用小儿科的办法或许更行之有效,这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再说了,他内心有鬼。怎么可能置之不理。好了,别耽搁时间了,你们到隔壁候着,我以摔杯为号将他拿下。”
那年生看了看若有所思的马笑天:“马队,这可不行啊,这万一抓错了人,可不是小事。”
马笑天把手一挥:“错不了,我分析了一下,刘文华肯定是在暗示你,这个人我了解,这人很精明,做事一向十分谨慎,这种暗示很符合她的性格。好了,既然已经打草惊蛇,咱们就给他来个快刀斩乱麻,将其拿下,出了事我负责。”
马笑天又深情的瞅着母亲,说:“你一定要小心,见机行事,万不可冲动。一旦发现情况危险,马上发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
母亲微微一笑:“放心吧,他还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不会把我怎样。”
马笑天看了看时间:“差不多了,你好好准备一下,我们撤了。”
这个不大也不小的两层楼饭店,除去跑堂的空无一人。马笑天刚才问过那个跑堂的,这饭店怎么就你一个人。跑堂的说这饭店生意不大火了,大掌柜家里又死了个年轻的,他带着伙计们都去了大佛寺,求个吉祥。
一个小时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曾涛柱竟然带着马笑天手下的五名专案组的队员以及一个班的警卫连战士,拿着枪冲向德顺楼饭店。母亲透过窗户看的一清二楚,有辆军用的敞篷卡车朝着德顺楼开了过来。她不慌不忙脱掉假扮男人的外衣。
马笑天和那年生这边也瞅见了这辆卡车,她俩有些惊慌失措,来不及多想,他们赶紧来到母亲这屋,马笑天直拍大腿说:“坏了,坏了,搞砸了。这…这…。”
那年生急了:“我…我说什么来着,你…你就是胡闹!破了个案,你就觉得了不起!你…你这叫骄傲自大。你说,你叫我们怎么收场?”
母亲略显轻松的说:“慌什么,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我怕的是他无动于衷,跟我去会会他。”
母亲在前面刚走到一楼楼梯口,曾涛柱拎着手枪,他身后跟着十几个人就冲了进来。曾涛柱愣了一下,表情中有几分敌意:“怎么会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曾涛柱带来的人都愣了,互相对视,茫然不解。母亲不慌不忙往前走了几步,拉过一把圆凳,坐在柜台前。曾涛柱不敢和母亲对视,但表现出临阵不慌的样子,把枪一收,两手往胸前一抱,原地挪了几下脚步,目空一切的说:“那总指挥,是不是应该你来回答我呀。”
母亲咄咄逼人的说:“把脸转过来,你先回答我,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曾涛柱当众之下,不得不把脸转向母亲,故作镇定的说:“有人企图敲诈我,我怀疑敌特分子另有阴谋,难道我不该来吗?”
母亲说:“我要听原因所在,这儿没外人,都是自己的同志,说吧,到底怎么一回事?”
曾涛柱冷不丁的笑了一下:“嗨,说来真可笑,竟然有人说亲眼所见,是我给金茉莉的小灶饭里下了毒,要我出两根金条可保平安。你说这样小儿科的举动,能扰乱我们的侦察方向吗?所以呀,不论这个特务有价值与否,我都不能放过他,跟我斗,还嫩了点。”
母亲语锋尖锐的说:“你刚才说,敌特是在扰乱我们的侦查方向,照你理解,金茉莉一案,特别专案组把重点放在监狱里办,这个侦查方向是对的啦?”
曾涛柱丝毫没打奔儿:“那当然,炊事班所有人无可非议,都不能排除嫌疑。”
母亲说:“你的话听起来好像监狱任何人都有涉嫌犯罪的可能,唯独你这个监狱长例外了。”
曾涛柱说:“我搞不懂你在说什么。”
母亲突然放大了嗓音:“你不是不懂,而是逃避现实!”
曾涛柱有点乱了阵脚:“你什么意思?怀疑我吗?那好,证据呢?”
母亲言辞铿锵:“人所共知,你有诸多疑点涉嫌下毒,你却目无办案原则,行使特权,逃避现实。就凭这些,审你一百次都不为过。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我提醒你,你已经到了同恶相济的地步,如若你还存在侥幸心理,只能罪加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