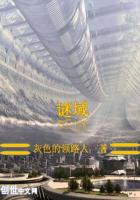卢国横跨蒙河南北,是中土大陆、南方地区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它在蒙江之南有广丰、邵武、宁化、长恒、会昌五郡,蒙江之北则有余阴、新丰、连平三郡。加上高京直隶之地,合称“东南九郡”。
它北接栗国,南邻越国,东面大海,西近宁地。其国广有千里物产丰饶,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又因其水军强大文化荟萃,素来和地域最广的栗国齐名,有“南卢北栗”之称。
只是近几十年来,由于连续三位君主的早崩,它的情况早已外强中干岌岌可危。
尤其是去年年中。那位兄终弟及的“桀皇帝”莫名驾崩,他的太子又先一步被其逼走,新继位的小皇帝据说有弑父嫌疑,自己又是个年少轻狂的性子,朝野都在传说:只要前太子出现在世人面前,当今的皇帝陛下必然不得善终。
朝廷大事竟然闹到世人皆知,可见当今的皇帝有多么的不得人心。他也是个不管事的,更是个没什么城府的少年人,因此朝中的大事小情尽皆落入他外公、及舅舅们一系的手中,
就是在这么一种全民躁动的氛围中,马友选定该国一处偏远山区,跨出了自己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招摇山,松子峪,新田村,一户刘姓人家。
刘赶山是一个烧炭工,贫民中的贫民,底层中的底层。
他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智力偏低的妻子,以及三个半大不大的小儿女。大的十三岁,中间的九岁,小的才五半不到六岁。
他的大女儿叫刘招弟,三儿子叫刘狗碰,小女儿叫刘来儿。
刘来儿长长的脖子顶个大脑壳,圆圆的肚子上不着寸缕印出清晰的血管纹路。纤细的四肢皱巴巴如干材,粗粝黝黑的皮肤紧贴着骨头似鳞路。
只一眼,她就引来马友的关注和心疼:这姑娘跟他本体的特征太像啦!只是这身子,恁瘦弱了一点,跟前世的非洲难民们有得一比。
马友自包袱里拿出一块黑黑的饴糖,犹如大灰狼诱惑小白兔一般的对她说:“乖宝,来,叔叔给糖你吃。”
他此时的样貌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刻意拔高的身材倒也不那么怪异了。
刘来儿既不接话也不近前,只是两只如鸡爪似的小爪子扣住充当门扇的芦苇杆子,用着犹如ET一般暴凸的大眼睛怯生生的看着他。
“不可以,不可以!”刘赶山放下背负的粟米、慌忙上前拦住,同时一把把刘来儿掼到门外,口中邀请着马友:“马兄弟,您里面坐,里面坐。”
马友一只关注着那个小小的身影。他见刘来儿被父亲一把摔出去三四尺,头皮都磕破了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他看着她艰难的在泥地上翻身,木呆呆的擦拭着自己的创口。
马友只觉得一股气息堵在心头,想要发泄,却找不到理由。
刘赶山见他不应也不动,不由小心翼翼的探问:“马兄弟?”
“没事。”马友摆手。他紧走几步把轻若无骨的女童抱起,转头对刘赶山说:“这孩子与我有缘。我欲收她做个干女儿,不知阁下能否同意?”
刘赶山先是一愣,想不明白马兄弟怎么看中了这个赔钱货,继而反应过来,惊喜无限的说:“同意!同意!马兄弟开口,咱们怎么可能不同意呢?”
送出去一个拖油瓶,还能换来马兄弟的好感,刘赶山显得更热情了。
“马兄弟,您请里面坐。”
马友不再抗拒。他把饴糖捏下来一小块,小心翼翼的塞进刘来儿的嘴里,看着她的大眼睛一下汇聚满惊喜,他的心里就甜滋滋、酸涩涩的。
马友暗运内息轻轻拂过她的额头,装作若无其事的向着草棚子里钻去。
这是一间用原木夹着芦苇杆扎就的低矮“草屋”,内里阴暗又潮湿,直通通的有二十好几个平方。
一进来就有个老妇人,穿着缺了双臂的蓑衣,颤巍巍的给他搬来一只原木墩:“家中简陋,小伙子不要嫌弃。”
“多谢阿姆。”马友放下刘来儿,从门外拎进来一只麻袋,从里翻出一匹麻木递给她:“初次见面,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这,这,这太贵重了!”老妇人昏花的两眼顿时闪亮,她在粗粝的布面摸了又摸,终究还是不舍的推拒给马友:“无功不受禄,小伙子还是拿回去吧!”
“是呀!”刘赶山在一边搓着手帮腔:“您已经给过一袋粟米了,俺们怎么能再要您的东西呢?”
“两位不必推拒。”马友语带真诚的说:“小子初来乍到,以后用到刘大哥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些权当提前支付的报酬吧。”
“好!好!”刘赶山笑得见牙不见眼,一个劲的应承道:“从今往后,只要是马兄弟你的事情,俺刘赶山一定不推辞。”
强推着刘母坐到上首木墩上,马友这才得空打量他家的内部环境。
这是一座圆形的建筑,圆心位置是一处火塘,上面用树枝支了一个架子,架子上挂了一只瓦罐,里面的炭火带着余烬,罐子里不知道温着什么。
马友的视线向四周打量,可以看到有六根碗口粗的柏木作为立柱,支撑着斜斜搭在一起的几根同质房梁。这些主梁之间用副梁连接,其上铺着芦苇捆扎的席子,间隙漏出点点干结的淤泥和茅草。
这房屋的约三分之一处,有一面芦苇扎起的屏风,把本就不大的空间分成了两部分。马友猜测,那后面估计是他们的卧室,因为他感知到屏风后面有两个人在透过缝隙,往外面偷偷窥探着。
“小伙子你喝点茶。”刘母递过来一只缺了口的陶碗,内是一碗散发着微温的白开水。由于人老手不稳,刘母的大拇指是扣在碗沿上的,半截黝黑的指甲都沁在了开水里。
马友接过来一饮而尽,这才谢过老人家的好意。
“好!好!”也不知道她好的什么,这老妇人已撩开帘子往屏风后去,一掠而过的间隙,他看到一大一小两个女人的脸孔瞬间闪过。
“这两人穷的蓑衣坏了。”马友心中明悟。继而反应过来:怕不是蓑衣坏了,而是根本就没有衣服。
这也符合他打听到的刘家情况:刘赶山每天烧炭卖炭,刘母带着刘招弟操持家务。刘妻因为智力障碍,只能做些烧火砍柴的笨活。剩下的两个孩子还小,编织蓑衣这种繁复的活计,仅靠一老一少显然是忙乎不过来的。毕竟,这东西恁不耐穿了。
“这还真是,家徒四壁、片缕不沾啊!”
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