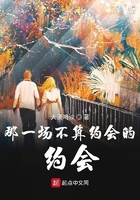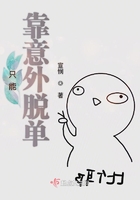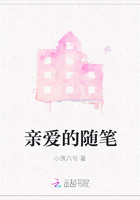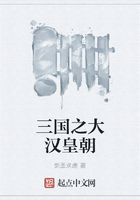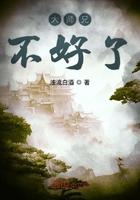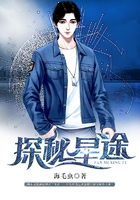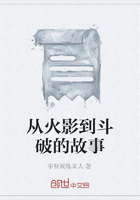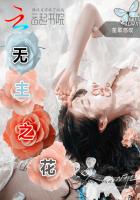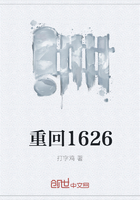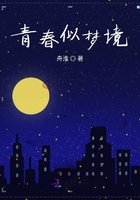写在前面:
1、本故事所有人物对话等内容均为文中人物观点,涉及人名、地名等不存在任何特指与偏见。切勿断章取义。
2、本故事情节非作者亲历,大多虚构,请勿寻源,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父母生于江苏北部的农村,各个村子相隔很近,以大片的农田作为划分,村名大多贴合地气,付村与周乡便是父母出生的地方。
母亲比父亲年岁稍长,结婚那年父亲十九岁,母亲二十二岁,由亲眷介绍相识,没有恋爱过程,只互相有眼缘,便匆匆结了婚。母亲说结婚时并没有大办酒席。按老家当地的习俗,出嫁之喜需要大摆三天三夜的流水席,宾客多为亲友和村邻,哪怕只是路过,也可招呼坐下喝上几杯。
我儿时也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宴席,听长辈们说厨子是县里某个大饭店请来的,我因好奇去看他们炒菜,偌大的铝制圆底汤勺,足足比我的脑袋还大,而手法娴熟的厨子却用得游刃有余。双耳大铁锅架在由半个油桶做成的炭灶上,锅里是可供十数桌宾客食用的红烧肉,淋上酱油翻炒,每一块肉肥瘦相间甚是好看,我馋得咽口水,厨子用大汤勺挑了一块递给我,我开心得要跳起来。
如今虽已忘了那块肉的味道,却始终怀念那时的年岁。
我出生前,父亲便带着母亲到了江南一个小镇打拼。父亲有两个姐姐,于我要称姑姑。因是大姑嫁到了江南小镇,大姑父在镇上有个小厂,于是小姑一家与父母皆来了此地发展,那年是父母亲结婚的第二年。
父母没有上过几年学,母亲读完小学便辍学在家帮衬家里的农活,父亲倒是多读了两年初中,后来也因交不起学费放弃了读书。初到江南人生地不熟,好在大姑父在镇上算是有些头脸的人物,有他带着,从苏北过来的两家人也不至太过陌生。
不过在我年幼时,时常听人私语来自苏北的我们,称我们为“江北佬”,这个词在江南话里是带有贬义的。仅相隔一江,却成了他们眼里的差距。
最初的两年里,父母只能住在由水泥和木头砌成的货船上,他们要从苏北老家将收来的废铜烂铁或是参杂铜矿的泥土通过水路运来江南,再将它们卸货进大姑父的厂里,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少则数日,多则十天半个月。我对此颇感兴趣,母亲却很少与我提及那段日子。不过可想而知,在那时候的时代背景下,水上来往货船的景象定是繁荣至极的。这与现代的陆运与空运有很大的不同,后来我查阅相关资料,才了解到那时的食物、生活用品与工业货物,因为量多且重,大多通过水路运输,船只相会的时候人们互相问候并互换食物与补给,却都是匆匆一面,再难相遇。
就在那样的年代,我的姐姐出生了。不知道是不是她生在船上的缘故,从小水性就极好。姐姐虽喜欢游泳,在泳池里也是如鱼得水,却在大多时候安静乖巧,定是遗传了母亲的温婉。
母亲说我出生那年姐姐四岁,江南发了大水,大小乡镇无一幸免,大水甚至漫过了膝盖,距离床面仅相隔数寸,一家人睡在一张床上,却也只好勉强地睡,好在是夏天,床上垫着凉席也不怕沾湿。直到如今,家中还存留了一张黄渍斑驳的老照片,照片中的背景是父母在江南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门前,母亲卷起裤管坐在椅子上,双脚浸在水中,双手抱着襁褓中的我,面容年轻而温暖。我无法想象母亲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将我生养,只是每次看到那张照片,眼睛总要酸涩。
我时常自问,什么是苦难呢,却从未有过答案。也许苦难一直在我们身边,也许苦难仅仅是人们脑海中的不甘与无奈罢。
岁月有着自己的魅力,它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也是一切问题的开始,每个人悲喜于其中,亦困顿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