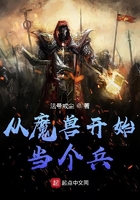萧江沅说到做到,对于李林甫便再无帮助,毫无修饰地将看到的一切都告知了李隆基。
“如此,我便放心了。”听萧江沅说完,李隆基舒展着四肢,平躺到了席上,一时心情大好,便要寻几个兄弟入宫饮宴奏乐。
见李隆基没有为李林甫的作为而不悦,萧江沅也没有多说什么。她也想让李隆基舒坦舒坦,此番便由着他去了。
可是等了许久,也不见诸王前来,就连派去的小宦官也不曾归来。萧江沅心下不安,便随李隆基登花萼相辉楼,将那宁王和薛王的宅邸纷纷看过,只见自从她落水那日起,便被李业留在萧江沅宅邸行医的韩四,此刻正急急地入了薛王宅的大门。
萧江沅尚未反应,李隆基已经转身下楼,一边疾步一边急道:“备马!”
等萧江沅和李隆基抵达薛王宅的时候,宁王李宪和玉真公主都已经到了。
“五郎怎么样了?”李隆基一挥手便免了众人的礼,然后扯住了大哥李宪的袖子。
李宪温和地道:“三郎莫急,五郎只是……到时候了而已。”
自从萧江沅落水那日被惊了一番,而后去了曲江又受了凉,李业便开始长久地卧床休养了。其实包括李隆基在内,所有人都知道李业身体久久不好,这一下恐是病入膏肓,来日无多了,但李隆基始终没有放弃,名医良药不断地送,竟让李业多活了这么多时日。
听大哥这么说,李隆基的心瞬间抽痛了一下:“什么叫到时候了,五郎是我们中年纪最小的,虽然身体一直不太好,但也……”
玉真公主眼中含泪,却仍固执地微笑道:“想想四郎,还有前年去世的金仙阿姐,年纪又大到哪里去了,还不是病甫一起,便急急地丧了命?像五郎这样拖了许多年,已经是又福气的了。想我李家子孙也不知是得罪了哪一路神仙,类似的病症竟如这皇位和皇亲的身份一般,也一代代传承了下来……三哥,你可要好好保重啊。”
或许是习惯了这样的病症,或许是看多了生死,任是再如何炽烈的哀恸,也终将被悠长的岁月抚平,成为一块淡淡的疤痕。
但李隆基接受不了。从韩四的口中得知五郎只剩下一个月左右的寿命之后,他怎么都不认,非要勒令宫里宫外所有的名医,让他们无论如何,务必要从上天手中把这条命抢过来。
他曾经成功地抢夺过,如今也一定可以!
但他忘了,天道总无情。
最终还是萧江沅安抚住了愤怒而狂躁的他,让他回了兴庆宫。
而她,在李业的请求下,“借”到薛王宅当值一个月。
这一个月,李业谁也不要,只让萧江沅在身边陪着,或出宅逛逛曲江芙蓉园,或去西市买些物件,用些好吃的吃食,或干脆就呆在家里,随便做点什么都好。
与其说是萧江沅陪李业,不如说是李业陪伴萧江沅,将她曾经想要做的事,都一一地做了一遍。萧江沅怎会感受不到李业的温柔与体贴,可她曾经问过李业,难道他自己就没有什么想做的事么,李业却没有任何回答,只看着她笑。
这一个月来,李宪和玉真公主也总来薛王宅。在萧江沅的心目中,李宪一直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她便将自己的不解问给了他。
李宪遥遥地望了一眼在卧榻上沉睡的五郎,温然一笑,道:“这便是他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事啊。”
“仅仅是如此?”
“如此便足够了。”
萧江沅是个不知足的人,所以她无法理解,竟然有人会有这样的知足。但事情既然已经弄清楚了,她便可以安心地伴在李业身边,陪他走完人生中最后的时光。
李业的妻妾儿女,也早就对他的生死,做好了心理准备。心知李业待萧江沅关系甚好,却终此一生没什么机会和她相伴,既已时日无多,他们便由着他放纵自己了。
让人无奈的是,萧江沅总是在这种时候特别迟钝,众人都心有所觉,但亦作不解,唯独她是真的不解。
玉真公主有些看不下去了,便私底下问李业:“既已做得如此明显,何不干脆让她知道?”
李业望着院中树荫下专心处理着事务的萧江沅,装傻道:“知道什么?”
“你以为你藏在枕头下的那方丝帕,我看不见?”
“……一方丝帕能说明什么?”
“那要不我替你还给人家?”
一听这话,李业只得如儿时一般乖巧地靠着玉真公主的肩膀,心急得要喘上好几口气,才能把一整句话说完:“为什么……非要让她……知道呢?这样就很好了……”
玉真公主只以为是五郎不愿与三哥争抢,便道:“你不用担心三哥,他那里有我。情之一字最讲究你情我愿,不是他身为天子便能胜的。”
“可是……阿沅的你情我愿,早就在多年以前,便给了三哥了……我……从不曾让她知道,阿姐你也千万别……”
玉真公主只得叹了一口气,道:“也对,若真你情我愿,她又怎会迟钝如斯?也不知道你们到底都是怎么想的,贤妻美妾不缺,却偏偏看上一个宦官……情之一字,也真是最没有道理可讲。”
李业笑道:“就像阿姐和摩诘?”
玉真公主忙道:“怎么连你也这么想?我和摩诘真的只是知己,清清白白!你这副表情是什么意思,你别不信我啊……”
姐弟二人说着便闹将起来,一如儿时一般言笑不断。李宪正在院中侍弄花草,见到此景,与刚入院中的李隆基相视一笑。
就这样悠闲而快乐地过了一个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萧江沅为李业送药和早膳的时候,发现李业衣冠整齐,竟是在睡梦中与世长辞。
七月初七刚过了三日。因着近几日的天光都甚好,萧江沅帮李业晒的书还没收起;李隆基在这里住了几日,昨天才不得不回宫去;李宪特意从自己的宅院中移栽了一些名贵花草,花苞尚未开启;玉真公主答应了去催王维的新诗,诗稿亦尚未拿到手里。
一切分明都还在继续,一切偏又都有了结局。
萧江沅忽然想起,昨夜的蜡烛曾燃烧得分外炽烈,蜡液不住地垂落,李业还说,那真像是眼泪。
他没有看到烛火正如他的生命,正在将生命的最后一点火热尽情地释放,却注意到了烛台上流淌不止的“眼泪”。他甚至微微笑了一下,指着那烛台说:“那是不舍的眼泪。”
说完,他破天荒地早早便催萧江沅去睡了。
等萧江沅离开,他起身将衣冠穿好,把枕下的丝帕取出,塞入了衣襟里。然后,他才安下心来,缓缓地在卧榻上躺好。他最后定定地看了烛台一眼,然而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他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唯独还能说话:“若有来生……”
静了半晌,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便只留了这半句,从容睡去。
李业葬礼那日,天降大雨。
李隆基把每一个死去的亲兄弟,都追封了太子之位。二哥李撝是惠庄太子,四郎李范是惠文太子,五郎则为惠宣太子。几个兄弟都是以太子之礼,随葬于睿宗桥陵,去陪伴父亲。
“大家让几位太子都去陪伴睿宗皇帝了,那大家自己呢?”
这一日,长安众官员都去参加了惠宣太子的葬礼,而葬礼是由李宪亲自主持。所有人都怕他哀思过度,不肯让他送五郎最后一程。
萧江沅却是必须到场的,故而李隆基便去了武惠妃那里。可没过多久,也不过一时没注意,李隆基竟然失了踪影。武惠妃几乎把整个兴庆宫都翻了过来,也还是没能找到。天子失踪,此事可大可小,她第一次在宫里发了大怒,直到萧江沅心绪不宁提前归来,她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萧江沅听说兴庆宫里没有李隆基的踪迹,便直接把找寻一事揽了过来。她谁也没带,径自出了宫,走到了薛王宅的大门前,果然在那台阶上看到了李隆基佝偻坐着的身影。
大雨滂沱之中,她出来得急,没有带伞,偏偏李隆基也没带,两人便在雨中淋了半晌,衣服很快就湿透了。
李隆基显然比萧江沅淋雨的时间更长,嘴唇都开始发紫了,萧江沅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思来想去便开了这样一个口。
李隆基沉声道:“我谁都不用……”
历代帝王陵寝都有无数亲眷臣子的随葬墓,可在他看来,后妃也好,皇子公主也罢,生前已经牵绊了一生,死后又何必继续纠缠,永世不得安宁?
萧江沅跪坐到李隆基面前:“那……臣呢?”
李隆基缓缓抬起头,只见萧江沅正认真地凝视着自己。有水滴不停地在她脸上滑落,不知是雨水还是眼泪。他伸出手,轻抚住她的脸颊,默然良久,忽地唇角一勾:“平日你侍奉我,已经够累的了,死后不想好好休息休息?”
“臣当然想,但臣更无法放任大家孤身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