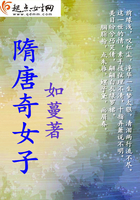元历7年,京城。
“这位施主,敢问楚将军的宅邸该如何走?”
只见白虎门前,一僧人头戴斗笠,身着麻衣,背上挂着个尚在襁褓的小孩,施施然对着个过路人行了个佛礼,问道。
那路人上下打量了僧人一番,只觉这和尚气度不凡,想来是个高僧,语气也就多了点敬意:“楚将军的府邸啊,沿着这街走,过三个巷子能见着一个卖点心的铺子,再到那惊鸿楼后面去,在朱雀街的当口就是了。”
僧人闻言,道谢之后循着那人的口径走去。
这路说在口里是不觉得长,僧人走了一个多钟头才找到那朱雀街,他抬头看了眼将军府的牌匾,抿了抿嘴,不知是想到了些什么,就见他取下背着的婴儿抱在怀里,轻轻叹了口气,才上前敲门。
片刻,那门开出了一条缝,里面的侍童警惕地瞅了瞅门外,见是个和尚,虽说疑惑他怎么抱了个婴儿,却也没多想,慢慢把门打开探了个身子出来。
“师父是来化缘的吗?”小童问道。
“贫僧来拜访这里的主人,并非化缘,劳烦通告一声。”
谁想那小童听了这话,脸色变了变,却还是强装镇定:“师父来的不是时候,近来府里杂事多得很,将军和夫人怕是抽不出时间,不如师父择日再来?”
僧人对这逐客的话,倒也不恼,却也没有打道回府的意思:“贫僧有急事相告,事关将军,一日不可耽搁,小施主只需帮贫僧传达两个字,将军自会召贫僧进去。”
小童转了转眼珠,应了下来。
“是哪两个字?”
僧人笑笑。
······
“不心。”
“不心?”
主室内,座上坐着一男子,虽年过中年,却依稀能见着当年风貌,一身的书卷气,若人见了,定然都说这人是个书生文官。其实不然,这位看起来风度翩翩,实则却是个实打实的武将——
南鸣国的大将军,楚行,字行之。
要说这南鸣百姓,不知楚行之者寥寥无几。
楚将军骁勇善战,17岁便随父上沙场,立下战功无数,战无不胜,又是个痴情的种子,他与夫人的话本都不知出了多少版本。如此之人,天子却也不忌惮,世间众口纷纷,甚至连他和天子的禁断之恋这不靠谱的说法都流传了出来,可这样一来,不就毁了他那痴情的说法,最后还是归结于当朝天子廉洁善政。
此时这位将军衣着凌乱,愁眉不展,脸色也显得苍白,听了侍童的话,却是精神一震,便是邻座的将军夫人也捂起嘴。
侍童一头雾水,不知这两个字里究竟有什么玄机,能让将军和夫人如此失态。
“快将那和尚请到候客间。”楚行之深深吸了几口气,命道。
“是。”
也难怪两人如此失态,十几天前,一神棍打扮的怪人不知怎么出现在他们府上,说是近些日子府上有难事,与刚出生的小公子有关。将军府安定多年,小公子又是刚接回府上,这来路不明之人一来就报丧,怎么叫人欢喜的起来,只当作是骗钱的给了些碎银就打发走了。那神棍抱着银子,走之前还声情并茂道:“不信小生无妨,但事发之后会有一个秃驴找上门来,虽说我与那秃驴不对头,不过你们还是见一见他为好,到时他定会与你们说两个字‘不心’。”
这怎叫人相信的起来?!
结果在那人走了七天之后,小公子便失踪了。
楚府调动了几十号亲信,日夜寻找,至今七日,无果。
要说这小公子,并非是楚行之的亲生子,但论起身份,却是比亲生子更为重要。
小公子单名一个怀字,是当今天子亲自赐名。
这小公子,是天子的第九子,乃后妃霖姬所出。霖姬生小公子时难产而死,她本人又是个没有势力支撑的,天子为了保护这孩子,降他为官籍,继在楚行之名下。
哪怕小公子改成了楚姓,但他身子里流的到底是龙血,如今进府一月不到,便失了踪迹。这孩子尚在襁褓,七天寻找未有结果,又怎么会是活着的。
这是大罪。
楚行之和他夫人日日盼着那怪人口中的“不对头的秃驴”,今日终于盼到,好不欣喜,才一时失了神。
小童把僧人引进来,一路上时不时偷看几眼那和尚抱着的婴孩,很是好奇。
待他们走到屋里,楚行之和楚夫人已在此处等候了。
楚行之使了个眼色,把侍从都遣了下去,楚夫人忍不住上前,问道:“大师今日光临寒府,可是为了小公子一事?”言罢,才觉自己太急切了,忙道:“是我唐突了,还请见谅。”
僧人摇了摇头,表示无碍,楚行之走到夫人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
“大师,此事关乎我府上下,还请赐予良策,楚某感激不尽,今后若大师有事,但来楚府无妨!”
对于楚府来说,这就是最高的承诺了,是世人万金也求不来的一诺。虽只是简单的一份人情,但若出自大将军之口,那就是让他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了。
僧人念了句法号,道:“贫僧本就是为还人情而来,又怎会再多奢求。
“将军此事,是命中注定,枯木逢春,所以将军不必忧心。
“七日前,贫僧在寺庙前捡到了一个婴孩,脖颈后有胎印。那小公子身上也必定有一个吧。”
楚夫人睁大眼睛,忙看向那孩子:“大师抱着的,莫不是小公子?”可这小公子又怎会出现在寺庙外面?
僧人把婴儿递给楚行之,他与楚夫人仔细看了看孩子的五官,多日未见,又是婴孩,只能看出大概,与小公子样貌并无多大差异,在确定颈后的胎印后,夫妻二人猛地抬头,眼中满是欢喜,他们双手微颤,正要说些什么。
“是,也不是。”僧人开口,打断了二人。
楚行之听了这话,眼中欣喜骤然褪尽:“此话怎讲?”
“这婴儿早已是无命之躯,体内仅存一缕残魂,却不知怎么与小公子的魂补在了一起,这才活了下来。而贫僧刚捡到这孩子时,相貌还不是如此,只有颈后胎印与此时无异。”
僧人话音刚落,就见楚夫人双腿一软,险些跌了过去,辛亏楚行之扶住了她。而楚行之自己也控制不住地颤抖了起来:“那······大师所言,怀儿是······没了?”
僧人沉默不应。
“如今怀儿魂魄在这躯壳里······”楚行之喃喃道,迫使自己冷静下来:“那大师可曾知道···知道怀儿的尸首在何处?”
“······贫僧,无能为力。”
“如此······”
偌大的房间,瞬时没了声音。
其实僧人哪里不知道那小公子的尸首在何处,只怕是说了,平添伤感罢了。
半晌,那僧人才继续道:“二位不必如此,小公子躯壳已去,魂魄还是在的,只是······”
他看了看婴儿,突然断了声音,倒把夫妻二人的心悬了起来。
“只是还有一些麻烦,这婴儿,是女儿身。”
女儿身。
三个字,重重压在楚行之和楚夫人头上,待他们送僧人出去,脑中仍是混沌一片。
直到大门口,见僧人将要离去,楚行之忙叫住他:“方才仓促,未问大师名讳,敢问大师法号?”
僧人停下步子,回首,行了一个佛礼。
“惭愧,贫僧,本无法号,唤‘无本’便是。”
······
······
“无本······”
“将军可认得这位高僧?”楚夫人将楚怀抱在怀里,还没从方才的事情里反应回来,听到楚行之念了那僧人的名字,便想起了先前僧人的话,这才问道。
谁知楚行之思虑片刻后转头对上楚夫人的视线,眼里竟是极少见的茫然:“我没有见过他。”
他顿了顿,才艰难地开口,一字一句地把后面的话挤了出来:“他所要还的,应是老爷子的人情。”
楚夫人瞳孔一缩:“祖父?!”
“父亲从前经常跟我提起无本法师,说是老爷子曾经带过一位年轻僧人来养伤,当时老爷子带他回来的时候,他尚在昏迷,遍体鳞伤,在府中待了一年多才离开。父亲常跟我形容那僧人如何像是仙人下凡,我一直没在意,把这话当作故事······”
如今将父亲形容无本的话和他本人对上,尽是分毫不差!
可别说祖父了,连老将军如今也已辞世多年,可那无本法师,单是看下半张脸,便知是连而立之年都没有到的。
房内又一次陷入死寂。
还是楚夫人先微微叹了一口气,竟是笑了起来,道:“能见到此人,我也可以够和孩子们说道几十年了。”
楚行之闻言也笑了:“夫人说的对,让他们羡慕去!”
夫妻二人相笑片刻,忽然想起一物。
楚夫人拿起一串铃铛,那是无本和尚临行前给他们的,说是此物能掩住小公子的女儿特征。
那铃铛被一串红线绑着,初见时,二人还以为那是染得血,毕竟没有一种颜料能染出如此色泽,可血是会变黑的,这绳却不会。还有那被连成一串的三个铃铛,外形只比普通铃铛小了一点,通体刻着他们从未见过的图样。
楚夫人按着和尚的话细心将它绑在楚怀的左手腕上,刚一松手,就觉得那铃铛似是又小了不少,戴在那小手上丝毫不显突兀。楚夫人可不觉得,那是自己的眼花。可近来一连串玄之又玄的事情太多,她竟是一点惊奇也不觉得了。只是向着楚行之无奈道:
“几十年光阴,没想到还是做了井底之蛙啊。”
楚行之也见到了那铃铛的变化,摇了摇头。
这一拴,就把楚怀的一生,尽数拴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