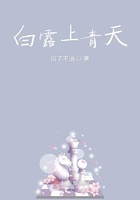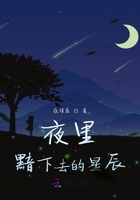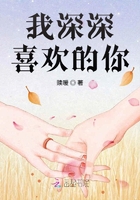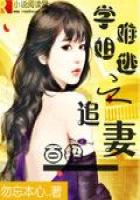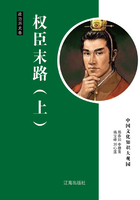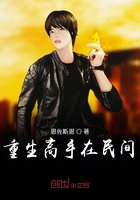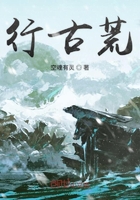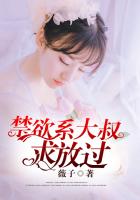初二是闺女回娘家,大姑、二姑都要来了,按说我们也应该去婆婆家,可是太远了,先把家里的近亲戚走完,我们去的是老舅家、老姑家。传亲戚回来,几个堂兄弟都在围着二姑父要压岁钱,他是国家干部,抗美援朝下来的,口袋里装着一些毛毛钱,逗着我们磕了一个又一个头,而且还要头触地有响声!
初三,我们要远行了,离婆婆家有九十里。交通不便,没法坐车,不过主要还是没钱。吃过早饭,我们姊妹几个和母亲坐上铺着席子的小平车,为了怕冷盖着棉被,父亲拉着就出发了!走县城上新济公路,时而一辆汽车疾驰而过,留下一串青烟,散发出一股股汽油味,感到很好闻!博爱玻璃厂的大烟囱,那么高、那么大,出了西关是十里铺,这里方圆十多里遍布着中国北方最大的竹林,片片竹林掩映着座座村庄,远看是竹林,走近是村庄,丹河水在林间、在村舍旁欢快的流淌着。过了博爱农场就是二十里铺,日已近午,我们拿出奶奶给准备好的干粮-纯白面馍,父亲停下脚步,路边有一家国营食堂,买了两碗面条,一碗是两毛钱二两粮票,我们吃的很高兴,实际上这是多年去婆婆家路上唯一的一次奢华吧!
过了丹河进入沁阳地界,行走不到数里,眼前就是沁河大桥,我们都下了车,沿着长长的桥坡上了大桥,好宽阔的大河,有七八里,可是水面也就几十米,我有点不解,父亲说,北方的河流大部分都是这样,那是因为降雨的季节性分布不匀,你别看现在这么小,夏天大雨一下,两岸涨满。站在桥上,极目远眺,虽没有长天与秋水共一色,但心中也似感开怀!
下了桥,走过沁阳西关,很想看一下沁阳城里是个什么样,可每次都是擦边而过。
日已西斜,还有三十里。父亲有点累意,我下了车。在我四岁的时候我曾走过这三十里,听母亲说那时很担心我的腿走坏了,那时父亲在东北,春节去婆婆家,先是到大姑家,然后大姑父架着我(骑在脖子上),母亲背着妹妹,到了沁阳城姑父就回去了,剩下的三十里就走走歇歇,天黑才走到。
沙岗,兰户铺、小金陵,前边就是崇义,再走就是婆婆的村庄,好不容易到了,一下车,每年在一块玩耍的小伙伴们就来了,婆婆家对面走车大门里叫猫的,村西头叫庄的,还有叫皮兜的、长河、都来了,我最惦记的是婆婆的本家一个叫长奇的,我喊他奇哥,他对我最好。我从远方而来,身上有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相互间都有点奇异、新鲜。
在婆婆家过得十分快乐,每天都可以吃上白面馍,晚上还不用打那讨厌的算盘,白天和小伙伴们尽情的玩耍,奇哥总是给他们说,远方的客人咱们要让着!我享受着照顾,感到优越!
婆婆家有几样东西我们感到挺新鲜,一个是做饭时的风箱,因为离煤矿远才烧锅台,用风箱助火,每次做饭时婆婆拿烧材烧火,我们姊妹几个挤在一边,争抢着拉风箱,“呼......嗒,呼......嗒!”真有意思!再有就是火盆,屋里没有煤火大炕,就是地下放一个铁的火盆,客人来了,点燃火盆里的材火,人们围盆取暖,先有点烟熏,后看着红彤彤的炭火也感觉暖意十足!还有的就是床上铺着一个厚厚的大草包垫子,用厚粗布缝的一个大包,里边装上满满的麦草,晚上睡觉躺在上边又柔软又暖和!
母亲姊妹四个,排行老二,大姨在陕西,小姨在家,最小的是舅舅。外公早逝,母亲每年这时总是和小姨在缝纫机上忙着,尽量把家中的衣服做出来。舅舅长我八岁,很好玩,白天带着我去崇义看戏,晚上带着我去打太极拳,他和一个叫全重的人在村里小学的操场上一招一式的比划着,没有人指导,但有一本带图的太极拳书。
父亲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故乡,人都叫他佟老师,有几个年龄大的专门找他闲聊,也有他当年的学生来给他拜年,我感觉到这几天父亲脸上有了一点笑意!
每年春节我们在婆婆家都要住一个多星期,度过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