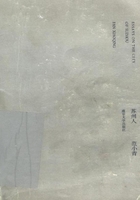由于是相体裁衣的创造,新诗的格式又必然是层出不穷的,因为诗的精神和情调总有差别。像枟采莲曲枠那样诗行参差不齐却相互对称的格式,自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即使是闻氏所着重论述的字句整齐的格式,也是有变化的。就后者而言,首先是诗行的顿数和言数都可以不同。其次是诗行的顿数相同而言数可以不同,如闻氏在文中分析的诗行“孩子们/惊望着/他的/脸色”,就与枟死水枠中的诗行“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不同,前者是四顿十言,后者是四顿九言。再次是诗行言数相同而顿数不同,由此也造成不同的格式。如闻氏枟罪过枠中的诗行“老头儿/和担子/摔一跤”,是三顿九言,与枟死水枠的四顿九言诗行不同。最后,即使诗行的言数顿数都相同,由于其中二音顿与三音顿的安排不同,格式也会有所不同,而并不像古代五七言诗那样,不同音数的音顿在诗句中的排列是固定的、形式化的。
总之,闻氏提出了新诗格式创造的正确原则,这一原则指示了新诗格式多样化的广阔前景。
第四,指出新诗格式具有“建筑美”的特点。
闻氏指出:“在我们的中国文学里,尤其不当忽略视觉一层,因为我们的文学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睛来传达的。原来文学本是占时间又占空间的一种艺术。既然占了空间,却又不能在视觉上引起一种具体的印象———这是欧洲文字的一个缺憾。我们的文字有了引起这种印象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利用它,真是可惜了。所以新诗采用了西文诗分行写的办法,的确是很有关系的一件事。姑无论开端的人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我们都应该感谢他。因为这一来,我们才觉悟了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增加了一种建筑美的可能性是新诗的特点之一。”
闻氏进一步指出新诗的建筑美不同于古代诗歌的建筑美:“诚然,律诗也是具有建筑美的一种格式;但是同新诗里的建筑美的可能性比较起来,可差得多了。”这种差别主要是,律诗即便分行书写,它也只是一种固定的格式,自然不免显得单调和呆板。新诗的格式由于是相体裁衣地创造的,其建筑美的样式可以很多,乃至无穷。
闻氏还正确指出建筑美与音乐美的关系,那就是“没有格式,也就没有节的匀称,没有音尺,也就没有句的均齐”;“当然视觉方面的问题比较占次要的位置”。这即是说诗的建筑美决定于诗的音乐美,视觉上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应该依赖听觉上有规律的音尺和格式。所以闻氏说“整齐的字句是调和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他反对“只有字数的整齐,没有顾到音尺的整齐”,因为那样“音节不一定就会调和”。这也就是说,不能为追求建筑美而不顾音乐美。虽然在创作实践上新月派诸人,包括闻氏自己,还是犯有这种形式主义毛病,但闻氏关于诗的建筑美的理论本身,却不是形式主义的。
闻氏认为格式是诗的听觉上的节奏形式(即本书所说的行式、节式等),把它与视觉方面的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分别开来。其实,如若把格式二字的意义扩大,我们也可以把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看作是视觉方面的格式。实际上,闻氏运用格式一词,有时也指诗的视觉上的形式,如他说“律诗也是具有建筑美的一种格式”;又说“枟死水枠这类麻将牌似的格式”,等等。把格式的含义作这样的扩大,关于诗在视觉上的建筑美就不单是以诗的格式说为基础的问题,而是直接成了格式说所包含的一个部分。反之,我们也可以把闻氏“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说法中的“匀称”、“均齐”二词的意义,从视觉上的建筑美扩展到听觉上的音乐美,即它们也可以指听觉节奏形式上句的均齐和节的匀称。听觉上句的均齐指诗句(行)的节奏形式是均齐的,即包含着整齐的音顿数;节的匀称指诗节的节奏形式是匀称的,一般是指对称的。当然,诗句和诗节在视觉上与听觉上各自的均齐和匀称,是既可以统一,又可以矛盾的,即听觉上句的均齐(顿数的均齐)也可以同时是视觉上句的均齐(言数的均齐),但后者也可以不是均齐的;同理于听觉上节的匀称与视觉上节的匀称的关系。下文运用“均齐”和“匀称”二术语时,就是有时指听觉上的,有时指视觉上的,有时兼指两者。
闻氏的格式论有两点不足之处。一是在字句整齐的格式和字句对称的格式中,他偏重论述前者,对后者只是略略提及(如提到枟采莲曲枠等诗的格式),几乎没有论述。闻氏这样做虽然是有针对性的,但作为一种格律理论,究竟是片面的。二是在论述字句整齐这种格式时,又着重字数的整齐。虽然他也说过音尺(顿)的整齐是更重要的,但对此强调不够,并缺乏必要的论说,所以也显出是一种偏颇。新月派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出现不少字句整齐而节奏并不和谐的诗(顿数并不整齐就是一个原因),与该派这位首席理论家在理论上的这种偏颇有关。闻氏自己的创作中也有这种情况,如:
爱,/你知道/我只有/一口气的/贪图,
快来/箍紧/我的心,/快!/啊,你走/你走———枟你指着太阳起誓枠
这是一首十四行诗的两句(行),字数相等,都是十三个字,但前一句五顿(音尺),后一句七顿,读起来节奏不大整齐、和谐。
闻氏无愧是新诗格律理论的奠基者。但他的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新诗的格律问题。例如,当时有些格律体新诗,其诗行的字(言)数和顿数都是整齐的或者对称的———这符合闻氏理论的合理要求,但节奏并不好,甚至显得板滞或破碎。这就是闻氏理论上并未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创作实践中一直存在,在理论上也一直未解决。本书下章将对它作一些探讨。
四 格律诗的均齐和对称节奏形式
初创期格律体新诗的雏形中就包含了两种类型:一种是顿数和言数整齐的,另一种是顿数和言数相对整齐的。二十年代这两种形式发展得愈益明显,有必要各自给它们一个名称:前者我们称“均齐体”,后者称“对称体”。
均齐体格律诗与古代齐言体诗类似。那么,为什么不称它齐言体诗呢?第一,因为古代齐言体是对杂言体而言,新诗却不宜有杂言体的名称,因为新诗中的自由诗和对称体格律诗都是杂言体诗,两者性质却不同。第二,因为古代诗的句式是格律形式化了的,言数有规律,顿数就有规律,所以它重言数,可用“齐言”或“杂言”来命名不同的诗体。格律体新诗由现代汉语言构成,适宜主要以顿数而不是言数来决定其格律形式。均齐体格律诗既有顿数和言数都均齐的,也有顿数均齐而言数不完全均齐的,前者与古代齐言体诗类似,后者则是独特的。
新诗中的对称体格律诗,与古代枟诗经枠对称的杂言诗及词曲中的对称形式类似,所以沿用其名。
以下简论这两种体式的格律诗在二十年代的情况。先论说对称体格律诗,因为它出现得较早、较多。
胡适枟尝试集枠第三编收入他1920 年和1921 年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对称体格律诗和半格律诗。如枟梦与诗枠: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像,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单从一节看,只是自由诗形式,至多算半格律诗形式。但从全首诗看,三个诗节中相应诗行的顿数和言数都相同,所以是对称体格律诗,并且格律较严,较成熟。
郭沫若写作自由诗比胡适晚,写作格律诗却与胡适大致同时。郭氏枟女神枠中有不少格律诗和半格律诗,它们大多是对称体。如发表于1919 年的枟死的诱惑枠,其节奏形式与胡适枟梦与诗枠类似。枟女神枠中对称体格律诗的一个特点是形式多样。如枟凤凰涅盘枠的“序曲”七节,就有多种形式:
除夕将近的空中,
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
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
街着枝枝的香木飞来,
飞来在丹穴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
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
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
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
天色昏黄了,
香木集高了,
凤已飞倦了,
凰已飞倦了,
他们的死期将近了。
凤啄香木,
一星星的火点迸飞。
凰扇火星,
一缕缕的香烟上腾。
凤又啄,
凰又扇,
山上的香烟弥散,
山上的火光弥满。
夜色已深了,
香木已燃了,
凤已啄倦了,
凰已扇倦了,
他们的死期已近了!
啊啊!
哀哀的凤凰!
凤起舞,低昂!
凰唱歌,悲壮!
凤又舞,
凰又唱,
一群的凡鸟,
自天外飞来观葬。
第一节是节内对称形式;第二节基本上是均齐形式(最末一行多一顿,可算破格);第三、六两节遥相对称,是节间对称形式;第四、五节又各自是节内对称形式,第七节基本上是节内对称形式。郭氏后来出版的枟星空枠、枟前茅枠等诗集中,也不乏对称体格律诗。
其他如刘半农、刘大白等人也很早写出格律体新诗,其中也多为对称形式,如刘半农枟叫我如何不想她枠等。
总的看,二十年代初期的对称体格律诗还不能认为是成熟的,理由有二。其一,虽然出现较多,但大多数的对称性不强;有的只是诗中部分诗节的对称是严格的,其余诗节的对称不严格,或者根本不对称,所以只能算半格律诗。其二,没有理论指导,大多数的创造可能是不自觉的。当时新诗的创作主要还是讲究“自然音节”,或者追求“内在韵律”,所以创造出长短参差的自由诗可以说是充分自觉的,充分自觉地创作格律诗却不大可能。有时,也许诗人本意是要创作诗行长短不齐的自由诗形式,客观上却写成了对称体格律诗。为什么会这样?大约是因为诗人一方面要写出长短参差的诗行,一方面又追求较好的节奏性(出于避免散文化等原因),于是写成了既有长短变化又有一定规律的形式,这便是对称的格律诗形式。此外,诗人根深蒂固的古代诗词修养,以及汉语易于构成对称、显出均衡等特点,也在冥冥中起了作用,帮助诗人写出对称形式的格律诗。这种格律诗形式当时的人们可能并未意识到,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它的规律和格式。
对称体格律诗成熟于新月派时期。新月派诸人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大都着重于均齐体格律诗,但也谈到对称体格律诗,如闻一多论格律体新诗的创造是“相体裁衣”时,提到枟采莲曲枠等对称体形式。闻氏“节的匀称”说,就包括了对称形式。朱自清后来点明了这一点。他说:“段的匀称并不一定要各段相同。尽可能甲段与丙段相同,乙段与丁段相同;或甲乙丙段依次跟丁戊己段相同。”这里的所谓段与段之间的相同,就包括均齐形式的诗段(节)的相同和对称形式的诗段的相同。他又说:“各行音节的数目,当然并不必相同,但得匀称的安排着。” [15]这说的更是对称形式:诗行的音节数目不同而又显得匀称,它们一般就是对称的。
新月派诗人在写作大量均齐体格律诗的同时,也写出许多对称体格律诗。如徐志摩的枟为要寻一颗明星枠,共四节,只看首二节: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
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朱湘的对称体格律诗尤其多样。如枟采莲曲枠,也只引首二节:
小船呀轻飘,
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
荷花呀人样娇娆。
日落,
微波,
金丝闪动过小河。
左行,
右撑,
莲舟上扬起歌声。
菡萏呀半开,
蜂蝶呀不许轻来,
绿水呀相伴,
清净呀不染尘埃。
溪间,
采莲,
水珠滑走过河钱。
拍紧,
拍轻,
浆声应答着歌声。
新月派诗人的对称体格律诗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但诗节之间对称,诗节内诗行之间也往往是对称的。以上两诗即如此。在后来的对称体格律诗中,只是节间对称而节内并不对称的形式逐渐多起来。
现在看均齐体格律诗。
胡适枟尝试集枠第三编中无整篇的均齐体格律诗,但有些诗篇的部分诗节是均齐的。如枟艺术枠一诗的首节:
我忍着一副眼泪,
扮演了几场苦戏,
一会儿替人伤心,
一会儿替人着急。
诗行是七言,但已经不是古代七言诗四顿数的“二二二一”形式,而是三顿数的“三二二”形式。构成诗行的也不是古代七言诗的双音顿和单音顿,而是双音顿和三音顿。所以它是格律体新诗。
郭沫若诗集枟女神枠中有不少对称体格律诗,均齐体诗却只有枟Vernus枠一首:
我把你这张爱嘴,
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
会使我时常沉醉!
我把你这对****,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成甘露!
每行三顿,除一行是八言外,其余都是七言。此诗写于1919 年,大约是新诗史上最早的均齐体格律诗,但格律却显得较成熟。郭氏二十年代中期出版的诗集枟瓶枠中,均齐体格律诗就多一些了。
二十年代初期只出现很少的均齐体格律诗,从反面也说明了早期的格律体新诗一般不是自觉创造的。因为如果是诗人们自觉的创造,他们一般会首先着重创造均齐体这种最明显、最符合传统观念的格律诗。在后来新月派自觉的格律运动中,诗人们就着重均齐体格律诗的创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