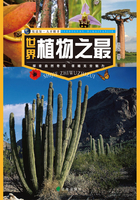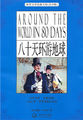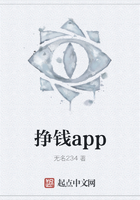那天,我走了许多路,终于找到了一个修伞的小摊。摊主五六十岁,有着花白的头发。他停下手中的活,将老花眼镜往下压了压,用审视般的眼光看着我。我说,师傅,帮我修一下伞,好像有一根铁丝断了。他撑开伞来检查,而后一声叹息,说,你们是怎么用的啊,要是珍惜一点,哪会这样容易坏的。他这么说着,口气像是训一个孩子。
其实,我是蛮珍惜东西的人,就说这伞吧,如果不珍惜,我就不会走那么多的路,不会来找师傅修了,不是吗,现在很多人都是将伞当成一次性用品的。这把伞没有什么来历,普普通通,那天风大,被吹成了“喇叭花”,一根铁丝便断了。家里人说,那就不要了吧,但我觉得太浪费,修一修还是能用的。我想起从前家里有一把黄色的油布伞,伞面补了又补,但我父亲还是不舍得扔掉,他说,修好了,不就能用了吗?
我记得这把油布伞刚刚买来时,颜色是鲜黄鲜黄的,撑开它需要用很大的劲儿。那时人小,我总是把它先倒过来,伞尖顶着地面,再用两只手顺着粗粗的伞柄往下按,这样才能撑开来。油布伞有着浓重的桐油味儿,很好闻的。见我们用鼻子一嗅一嗅的,父亲说,味道淡了,可以再去刷一遍的。一个雨天,我撑着伞去上学,结果,回到家里,发现伞跟别人的搞混了。父亲问我,你大概知道拿错谁的吧,我说,可能有三个同学,父亲就让我一家一家地去找。找回后,父亲用红漆在伞面的里边写了个大大的姓氏。上世纪60年代中期政治风暴最烈的时候,为了让母亲逃过一劫,父亲决意要母亲去乡下避风头,母亲临走时,只带了很少的东西,但我外婆执意要她带上油布伞,说刮风下雨就不怕了。母亲回家时,将油布伞也带了回来,我看到那鲜黄的颜色变成深棕色了。
我自己的第一把缩折伞是在杭州买的。那是夏天,我和几位同学结伴去杭州旅游,正在西子湖边漫步时,天一下子暗了下来,随即暴雨如注。仓皇中,我在湖边售货亭里买了把伞,但别的同学却不愿买,他们边奔跑边说,这么大的雨撑伞没用的,何况住的旅店并不远。我撑着伞跟在他们后面跑,到达旅店时,我跟他们一样,衣服全淋湿了,也成了落汤鸡,他们还取笑我呢。但是,当晚,同学们全都感冒了,只有我自岿然不动。他们探究怎么回事,我说那是伞的功劳,尽管我衣服全湿了,但头部因为撑了伞却没淋着。那时,我就想,别看一把小小的雨伞,真的是要珍惜的,因为伞是跟人走的,总会有一次为你挡过风雨。
正是这样,所以,这次伞坏了,我没有轻易扔掉,而是走了许多路去找修伞的小摊。我思忖,那修伞的师傅为什么要这样看我说我呢,他一定有许多关于伞的故事吧。
可惜的是,前些日子,我将这把修好了的伞遗落在公交车上了,因为雨停了,下车时忘了拿还没发觉。后来,我不断地打电话到车站询问,最终的回复是没有人交来过。我真的很有些失落感,尽管这把伞来历普通,但是,每次出远门,我总是带上它的,带上它,就像当年我外婆要我母亲带上油布伞一样,冥冥中能感觉到一种温暖而可靠的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