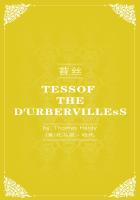透过镶有玻璃的拉窗,可以望见幽雅的中庭,小院里青松风姿俊美。客人们盖着四幅宽的绸缎棉被,在火炉间暖暖和和。美人斟酒发出啧啧之声,其景仿若幻梦,门前一排酒桶,客人们随意畅饮。
“瞧,哪来的小伙子啊,站在雪里也是一景,很有雅趣。”有客人在赏雪。
雪越积越厚,大概有五六尺深,连防雨板都无法打开了。雪一直下,天昏了下来,又是一个长夜之宴,客人兴致正浓,人们的舌头都不听使唤,开始胡说八道。
芳之助眼里除了六角雪花再没别的景致,彻骨寒冷,大雪纷纷,不知道要下多久。两三天前刚刚略感寒意,今天早起,天空便转为淡墨色,头疼的毛病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准时。强劲的西北风一直刮,日将暮,大雪飘飘洒洒宛若鹅毛,又似柳絮,日落时分,佛寺的钟声低低掠过耳畔,鸦群急急归巢。今夜这处旅馆冷冷清清,仿佛初见无常空虚的人世幻梦。酒馆的二层房间里,歌女用指甲轻轻弹着三降调[1],幽幽笑声透过小小竹帘,行人不禁驻足倾听。路边一只小狗,焦躁地摇晃着尾巴,有人呵斥一声“畜生”,小狗吓得急忙躲开。“畜生”这个词真是糟践人的话。伞上的白雪越发沉重,行人慢慢稀少,街角一侧暗淡悄然,提灯的光影掠过一阵寒风,瞬间心慌慌。这辆破车一看就是便宜货,破烂外罩剥落斑驳,夜晚还算过得去,白天可真是羞于见人。旧毛巾想必是乘客丢下的东西,这种物件大部分客人都不会折返去取。想我芳之助如今连廉价的大米也吃不上,只能在九尺二间的陋室中勉强过活。
“看,这人文文弱弱的,不像干力气活的,看起来可不像个普通的车夫。”芳之助不愿接受这样的夸奖。
“他气度不凡,不像是靠干力气活儿长大的,很想问问他的经历。”要是客人没有主动盘问,他从来不会主动张嘴。
“啊——”芳之助发出一声叹息,牙齿冻得打战。他抬起头,真是一个美男子,肤色黝黑,眉清目秀,嘴角柔和圆润,年龄在二十一二岁。再看他的穿着,那身补丁满满的窄袖和服看样子是由丝织平纹绸改成的,腰带上缠绕着金锁,一副华美耀眼的姿态,连时下流行的当红明星都难比拟这份风姿,怎么看都是富家少爷的身份。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何如此气宇不凡的男子却沦为车夫,是因为没有才艺傍身,还是没有伯乐慧眼识珠呢?
芳之助对于客人的情感全然不知。玫瑰虽美但是有刺,柔和的脸庞背后会有想象不到的事情,一想到这些经历他就会毛骨悚然。大雪里的梅花期待春天,为谋生他逐渐学会不拘小节大勇不斗。在街上等候客人的闲暇,他习惯翻阅日文典籍,带着问题观摩世界,那么面对这世间万象,就会有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夜深了,大雪覆盖住万物,行人脚印越来越少。商店渐渐落下门闩,按摩声音此起彼伏,同近处的犬吠交织在一起,听起来分外凄凉。一阵冷风袭来,路旁垂柳迎风飘动,细小的雪花沙沙作响。沉思中的年轻人感到脖子处一股凉意袭来,遂缩缩衣领,抖落衣襟上的雪花。灯泡的微光映照着他的一侧脸颊,显得十分苍白。“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更没有一个乘客,我到底在等什么呢,别人看见肯定会觉得我很傻吧。”虽这样想着,他还是没有回家,环顾四周始终没有放弃等客的心。冻僵的手指伸到灯笼下面,想要暖和一下。“唉——”有气无力地轻舒一口气,东张西望了一番后又发出长长的叹息。
停在此处,已经是第三次听到钟声了,这回下定决心回家吧。他猛地站起身,接着又将双手插入怀里,犹豫再三。
“好为难啊。”叹息声不觉从唇间溜出,芳之助独自僵立在街头,不停发出咂嘴的声音。雪下得越发大了,看样子是不会停的,肯定是没有行人了。正当扫兴之时突然听到欢快的脚步声。
“感激涕零!”芳之助回头一看,街角的路灯照耀着雪光,原来是巡警正警惕地注视着过路的行人,然后从他身边走过。不久又响起了人声,这次才是可悲可叹呢,三轩附近就是住家,他精疲力竭茫然伫立。
恰好这时后面有人搭话:“可以走吗?”有人影映入眼帘。
“上天派来乘客了,这次可不能错过。”他鼓起勇气走过去。
俗话说,过犹不及,这次居然是两个人。
“真是不凑巧,我的车只能拉一个人。”
注释:
[1]三降调。三味线的调弦法之一,即第三弦比基本调只降低一个全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