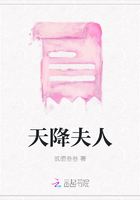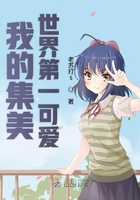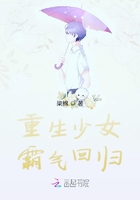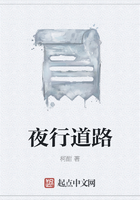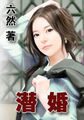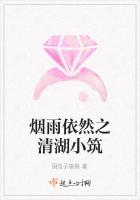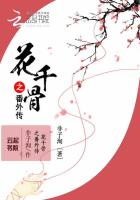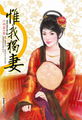阿奴幼时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很多,只记得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父母就跟着许多亲戚的步伐去了上海赚钱。阿奴也就跟着姐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留守儿童。
阿奴的童年是在爷爷家的院子里度过的。
爷爷家的前院是一块下坡但坡度不大的水泥地,水泥地旁边有一棵据说是在阿奴出生时种下的榛子树,在阿奴年龄还不大的时候,它就已经茁壮成长到能够让阿奴在它身上爬来爬去地玩耍了。
在阿奴父母还没有去上海之前,阿奴的爸爸还在院子里挂衣服的线上装过“秋千”。说是秋千,也只是找到一块木板当坐垫,再拿一根粗绳子绑住线,固定好木板,一个秋千就算完成了。
但爸爸做的秋千,阿奴已经没有印象了,听姐姐说是因为阿奴这一代表堂兄弟姐妹的争抢使得爸爸无奈只好亲手讲它拆除。
阿奴记得到的,是爷爷做的秋千。
爷爷在那棵榛子树上找到一根平行地面的又足够结实的树枝。找一块厚实的木板,又拿来几根铁丝,当然,少不了粗绳。将木板和粗绳固定在一块,绳子绕着树枝转几圈,然后打个结固定,铁丝再加一层固定,一个简易的秋千就这样做完啦。
由于树枝不够高,秋千荡的不够远,但每次荡的时候,阿奴都在想,我能荡到天上去吗?秋千往前,往后荡,阿奴的心呀,也随着秋千上上下下地起伏着。
如果你走进这个小镇,你会发现这个马路上有两棵又高又大又茂盛的树。而那棵枝叶更加繁茂的树旁,有一栋房子,这是阿奴姑妈家的。
早年间,阿奴姑妈嫁给的人家很有钱,是这座小镇上数一数二的人家,于是便在这单独建了一栋房,上层是厨房,还有摆放东西的闲置房间。
下层是供居住的房间,这层有三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很宽敞明亮,装饰的也很精致,有镜子,梳妆台,甚至还有一些当时流行歌手的海报贴在墙上。
当然,厕所也不能漏。在房子的东西两边都各有一个卫生间,方便居住的人的使用而不拥挤。
顺着姑妈家门前的小路走下去,是爷爷家的后院,后院只有一口井,阿奴小时喝的水,都是从这涌出来的。
一到打水的时候,爷爷便拿着两个桶一个扁担从前院到后院,拿起一个桶侧着没进水里,用力,把桶抬起来,等两桶水都装完了,再用扁担将水都挑起来。阿奴就屁颠屁颠的跟在爷爷身后,沿着房子旁边窄窄的小路,把这两桶水抗过去。
爷爷家除了前,后院,还有三块地,一块是菜地,一块是池塘,一块,是榛子树地。
那块菜地,阿奴对它最大的印象便是烧火。过节时,亲戚都从县城里回来,跟着两个上初中的哥哥到处乱串。先是四处搜罗干柴,像干老的树叶呀,从沙树上掉下来的枝呀,统统收下,摆在一堆,然后跑到厨房找到打火机。
那时爷爷家用的还是灶,煮饭要用火柴呀打火机呀这些来点火。
由一根带脂的枝点燃,放到灶眼中,再一根一根柴地放进灶眼,必要时,还要借助鼓风机把氧气吹进灶眼里,增加火势。除了灶眼,还会在灶台的最下方留一个洞,灶眼里的柴烧成灰烬后会通过一个个孔掉到这个洞里,不仅如此,放菜已经煮好但还没烧完的柴也可以放在这里,以留着下次煮菜时继续烧。
找到打火机后,阿奴便很快到后院的菜地里,哥哥们也早已经不知从哪找到了新砖,左右各立两块,一个小型灶台就做好了。打火机一点,沙树的枝马上就噼里啪啦的烧起来了。
火势也随着加的枝越来越旺,那团火焰,竟有阿奴般高了,火焰熊熊燃烧,让人不敢靠近,只是在周围就已经暖烘烘地要被烤掉了。
当然,阿奴的哥哥们可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来煮东西,这不,地里刚长出来的地瓜一拔,土还没洗净,就被丢进了火堆里,火势越旺大家也就更兴奋。
哥哥们甚至会去客厅里拿出蜡烛,用提前准备好的旺仔牛奶的瓶子在水泥地上磨去最上面的盖子后把蜡烛点燃流下的油倒在里面,待火势小了,把罐子放在砖头上,这下,不只是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还有蜡烛的油滋滋在燃烧,像是合奏了一首交响曲,阿奴这几个孩子跳着笑着嬉闹着,就连大人也被吸引过来。
大人看见这团火马上焦急起来,小孩子不懂火的厉害,大人可不一样,马上就到后院提了桶水扑灭这熊熊火焰,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阿奴她们。“你们知道这样多危险吗?这是菜地,要是别的东西烧起来怎么办?烧到旁边的房子怎么办?下次再这样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男孩子皮厚,哥哥们咂巴咂巴嘴,左边进了右边也就出了,等下次过节回来,又用着不同的花样玩起火。
阿奴则只能低下头,看着被熄灭的地上的惨象,地瓜表面也黑乎乎的,就连新砖也熏上了黑色的妆,阿奴觉得鼻子酸酸的,双手紧紧攥着衣服。
等大人们离开了菜地,拼起桌子打起牌的时候,阿奴偷偷跑回来看了看地瓜,捡起已经没有热气的地瓜,把黑黑的这层皮去掉,却发现还没有熟,硬硬的和没烧过一样。
这时阿奴终于忍不住了,眼泪汪汪直往下流,用剥过地瓜皮的黑手擦眼泪,就连肉肉的小脸也变得黑黑的,像是用碳抹过一遍脸一样。等哭完再回到人前,只叫哥哥们哈哈大笑,“像花猫脸一样”哥哥们是这样说的。
爷爷也笑开了花,花白的胡子都跟着卷出了一个弧度,爷爷走过来领着阿奴到放脸盆的地方,打了点水,用毛巾轻轻地把阿奴的脸擦干净。
“嘿嘿,我看你下次还敢不敢玩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