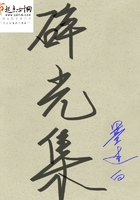晨曦喜欢闭上眼睛去听叶蓑鸟啼,
冬雪喜欢睁着眼睛去感受安逸静谧。
你若在春日前来,我定不会在秋天便选择离去;
你若在暖阳里簪一头夏花,我也定会穿着裙子等你带我去天边玩耍。
你在冬季的早晨踏云而来时,
我恰好在痴盼着远洋的帆,孤独立岸。
于是,
你不言,
我不语,
瞳孔倒影的天地垂幎,
是刹那微熹光芒潋射的爱,
夺目在你我之间。
刹那虽短,却是永恒最爱的伴。
字典中有这样一个词语,可以不分男女,不分天地,不分时节,不分东西。它有着融贯于一生的微妙之旅,也有着通天入地的可歌可泣。我们从小到大对其的期总是大于盼,在它伤尽了无数的人心之后,却依旧能大摇大摆地横行与一切灵魂之间,即便热情奔放如它,内敛羞涩亦如它,有人一生追随,有人一生伤怀,但它依然是人生过往中不可或缺的一样东西,爱情。
爱情是一个唇齿之间难以企及的词组。你会发现,它的存在,说不说出来不要紧,因为他与人思想和行为是密不可分并且毫无嫌隙的亲密关系。就好比我们经常能听到一句话,你爱或不爱,言语可以骗得别人,但行为,却骗不了自己。
初次与它打交道是在学生时期的蹩脚小说里,那时懵懂与缥缈朦胧的情愫,俨然对好奇的人是一种强劲的诱惑与灵魂的躁动。对爱情的需要,可以不像一日三餐那样不可或缺,但却比饮食更让人充满期待。于是,你会在青春期的时候,忽然发现,你人生的第一次失眠也许不是因为怕被父母数落的考卷,而是那个游弋在河中的人,他穿过了繁花,穿过了沼泽,他小麦色的肌肤在阳光下照亮了你暗淡如灰的十几年生涯。于是,你看到了漫天莺歌燕舞,你看到了琉璃碎瓦,你看到了草长莺飞的年华里,不经意间的,美好刹那。
我那个年代的人,上学期间似乎对情感的释放度恰好在社会发展的过渡期,也就是由羞涩到放开。放开不等于开放,就好比真空包装的豆子开了塑料包装还是撒在地上,还是有着区别的。所以,那些有关于好感的喜欢最后在日日夜夜的焦灼中衍生成爱,那种熠熠生辉的东西,被我们藏得极好,我们像守护着某种自己才可以窥探的人性秘密而紧张并且兴奋,写在纸上,写进日记。
当然,待我们一跃成年之后,你在回头唾弃一口狗屁爱情时,依旧会不忍心把纯真也掺杂进去。而这个不忍心,便是人生的刹那芳华,却永恒在青春的酒里。
那时年少,晦涩如酒,隐晦如茶;
我曾想提起杯盏提前去品品苦涩生涯,却最终输给了勇气和步伐。
那时年少,天晴得比20岁时要早,
我背起我时代的书包,却藏起那折在某一页书本里的小纸条。
那时年少,天蓝风筝飘,
我在路过熟悉的街角,发现了同样爱笑的你,在和我躲猫猫。
记得,我第一次去怀念十几岁孩童时的纯真情感,就是在大学校园里。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坐在大树的花坛下,聊起校园,聊起云淡风轻的青春年少,聊起那路过我们彼此生命中的人,现在是否安好?我们说着说着,忽然就沉默了。这种沉默后来演变成痛,就是那种看见身边路过的初高中孩子,会想起自己当年背着书包倔强且不可一世地走在青春的跑道上,越跑越快,气喘吁吁地最后乱了阵脚。
30岁时,再次在某个去幼儿园接女儿的路上,遇见三三两两的青少年,心里平静出奇。我在过马路的间隙回头望望等在公交车站的他们,莞尔一笑,少年,你好。
我在马路的左,你在马路的右,
当我途径你身边时,
我忽觉时光是个微妙且带有魔力的东西,
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年少味道,
吸引我的灵魂飘飘回到了校园的桌角。
这一季的校服太丑,却映衬出你青春的明艳,
我写了一封信塞给你,转身便跑。
你在夕阳的晕中羞红了脸,
是啊,岁月静好。
少年,你可还记得我?
那个男男女女肆意欢笑的拾光条?
其实,感伤是一个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东西,甚至在某些活得很现实的人眼中,是一种病态和浪费时间的表现。我个人不这么认为。人生无非就是三个状态,过去,现在,将来。你回忆的未必是某一个人,而是某一个时期,你会通过记忆中残存的某些片段去拼凑自己无言且简短的一生,从少到老,从生到死,从夏到冬。
就像,你甚至记不起来自己喜欢过的人,爱过的某个下雨天,你也想不起来日历上画了圈圈的几月几号究竟有什么秘密在背后偷偷喧嚣。
你回忆的是青春的校服,毕业的酒醉离别,含糊其辞的说爱还早。
少年的爱,如同爱春花秋草,
没有过盛的妖娆,却美过这世间最美的毒药;
你曾问我,爱到何年雨飘飘?
你曾问我,爱到断桥离别了?
如若把爱放在心间,即便雨打芭蕉,断桥亦是桥。
少年的爱,沉浸且骄傲,
它纯过人性的叨扰,它可以绕过世俗的惊骇波涛。
又是一年,恰是一年,
巫山飞作霄凌岭,
最是年少把人憔。
少年,如若不枉青春此行,爱情,就当是岁月的贺礼,贺你:
再谈青春,已无青春。
当你掩面而泣举杯换盏时,抬头望望你面前的酒,杯中影,人怜扰,犹看岁月可回首,却是沟壑心头凿。
爱,与不爱,无关紧要。
你还记得青春的小纸条吗?
流年展幅在你笔墨的某一天,你拂去书本的尘土,摊开在手,你滴落的第一滴泪,恰好落在了纸面之间。
你若问我尘封在年华的梦,究竟写了些什么?
只有四个字,
少年,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