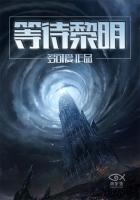沈云悠再进宫的时候,瑜妃已经将一大一小两只风筝做好了。她下了许多功夫,风筝比沈云悠初次见时好看多了。
“不错吧?”瑜妃问道,沈云悠点点头,含玉站在旁边拿着那只小一些的风筝,她似乎很喜欢,目光从未移开。
“您是不知道,我们娘娘平日里一将风筝拿出来坐在桌前,便很久都不动一下,可算是做成了。”袁嬷嬷同沈云悠抱怨道:“我总担心娘娘的身子吃不消。”
“春天还早着呢,怎么这样着急?”沈云悠问道,她记得瑜妃说过春天的时候再去放风筝。
瑜妃摇了摇头:“咱们何必等到春天,想让它飞起来,有风就行了。”
她说着接过沈云悠手中的风筝,又将房门打开。一阵风吹过来,寒意停留在了房间里。瑜妃伸出手,任风从指缝中划过笑着开口:“今日不就可以么?”
含玉兴高采烈地蹦到院子里回头向瑜妃招手:“母妃,这里!”
“你小心点儿,别摔了。”瑜妃叮嘱道,说罢挽着沈云悠的手走了过去。
幸而今日有风,但不算阴冷,三人费了好大劲终于勉勉强强让风筝飞了起来。
风越来越大,沈云悠甚至觉得除了耳边的风声,她什么也听不见。她抬起头,风筝飞得愈发高了,含玉兴奋地满院子,嘴里念着:“再高一点,再高一点。”
过了一会儿,风筝有些不受控制,不停左右摇摆,仿佛下一秒就要经受不住寒风的摧残,破碎在空中。
“啪”地一声,线断了,风筝随着风的方向渐渐远去。含玉骤然停下,她站得笔直,双眼紧盯着风筝,像在进行一个隆重的仪式。
沈云悠和瑜妃也默不作声,直到风筝完全不见了踪影,瑜妃终于开口:“可算是飞出去了。”
说罢她将另一只风筝收起来,往柜中放时,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画。那幅画滚落下来展开,画中女子笑得正明媚。
“这是?”沈云悠俯身将画捡起来,小心地递给了瑜妃。瑜妃伸手碰了碰画中女子的眉眼,轻声问:“同我像吧?”
“这可不就是你么?”沈云悠回答,虽说画中的女子青涩,画师画技也不娴熟,可还是能从画中隐隐看出瑜妃的影子。
这幅画看上去不像宋景明的手笔,沈云悠便问:“是魏泊画的么?”魏泊的画虽也好,但比起宋景明来,还是差了许多。
瑜妃却摇头,她认真看着那幅画,眼底流露的温柔和留恋沈云悠从未见过。
“这是皇上画的。”她最终回答:“可惜他做了皇帝后,便再没有提过笔了。”
沈云悠一怔,她从前也想过这个可能性,还特意问了池季远。可得到的回答是皇上不仅不会作画,甚至对画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他当年为我画了这幅画,后来他在我心中便死了。”瑜妃缓缓合上画,说起了过往:“我从前被约束、不愿争斗,可要留在他身边,只能接受这些。”
“起初倒还好,总不过是后妃之间的争风吃醋,倒也没有波及到我,直到……”那是瑜妃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她如今却还是轻描淡写将事情说了出来:“直到我唯一的妹妹被拜访的使臣看中,那时两国关系焦灼,对方一定要让她嫁去。”
“他答应我会保全妹妹,却还是强迫她嫁给了那个杀人如麻的禽兽。”瑜妃转头看沈云悠,她同自己的妹妹真的很像,忍不住碰了碰沈云悠的脸,瑜妃继续说:“她随着使团走了,还没有到那里,她便被折磨至死,后来两国还是开战了……”
“我知道这是无奈之举,可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爱恨纠葛都随着妹妹一起离开了。”瑜妃叹道,在那之后她大病一场,身体变得虚弱,同他之间也有了许多隔阂。
她留在宫中,并非为了他,只是为了成全年少的自己;他身为一国之君,为求安定牺牲许多人,虽是对的,可失去了此生挚爱,也是他应得的果。
沈云悠动了动嘴唇,过去的时光不复存在,但过去的瑜妃却回来了。而那个少年郎,她的心上人,他死在了登上至高之位的那个清晨。
“母妃,快来玩儿!”含玉站在门口摇着小鼓,瑜妃冲着她笑了笑,匆匆将画收起来,自言自语道:“这样也好。”
沈云悠知道,魏泊大约再也不用来替她作画了。她没想到瑜妃喜欢魏泊的画竟是因为,他的画同皇上当年的画很像。
瑜妃也不过是睹物思人,她虽不关心这后宫之中的纷争,也不欲同皇上重修旧好,可到底是没有放下。
而如今……沈云悠抬头的时候瑜妃正搂着含玉逗她,二人在寒风中大笑起来,如今瑜妃也算活过来了。
沈云悠过去,瑜妃拿着小鼓在她面前晃了晃,说道:“该你了。”
“什么?”沈云悠愣愣地看着她,不明白画中的意思,瑜妃不满地开口:“我都将自己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了,你怎么能有所隐瞒?”她佯怒,用小鼓敲了一下沈云悠的手臂。
“我?”沈云悠仔细想了想,自己的秘密没有一件能同别人说,她最终抬头:“我的事姐姐不是都知道么?”
“你可骗不了我!”瑜妃将鼓塞在了含玉手中,拉着沈云悠在石桌旁坐下:“你不是同我说过心中有人了么,怎么样,同池公子替退婚了吗?”
见沈云悠迟迟不肯答话,整个人都处于犹犹豫豫的状态,瑜妃骤然笑了。
“看来我没猜错!”她一副了然的模样:“你那所谓的心上人就是池公子吧?”
沈云悠没想到她这么快就看穿了自己的心思,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有些纳闷儿地问道:“很明显么?”她本以为自己对池季远的感情已经足够淡,也以为隐藏得已经够好。
可瑜妃还是看了出来,那他呢?沈云悠心中忽然冒出了这个问题,他知道自己的心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