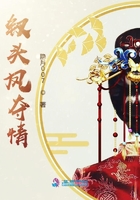紧闭的房是被人从外面暴力打开,屋里面的溪王打了个酒嗝,半趴在桌子上睡眼惺忪的,双眼久不见阳光,被外界的亮光刺激得流下了眼泪,溪王胡乱的抹了抹,怒斥道:“谁给你的狗胆,让你……”话音应声而断,他已经看清楚了,前方逆着光站在门口的人,他的王妃—— 郑令仪。
这个带给他无限希望,就让自己意识到卑微的女人。
“你就打算这样算了吗。”郑令仪板着脸吐出了这一句话,声音甚至说得上是温和,但是了解郑令仪的溪王清楚,这女人的话中夹杂着大量恶意的讽刺。
“要你管,滚开,我老子叫训我也就算了,你算什么个东西!”说者我再拿起桌上的一个酒罐扔向了门口,酒罐里还有残余的酒精,杂碎在地上溅起了一阵浓郁的酒味。
紫苏被吓了一跳,连忙双手护住郑令仪,两个眼睛警惕的盯着溪王。
溪王已经不在乎这个女人是怎么看自己的,她反而能觉得此刻更痛快,紫苏引起了他的注意,踉踉跄跄的站起来,露出邪淫的微笑,“这么用力看着爷干嘛,爷想想还有个良娣的位置,你要不要呀,余良娣说得真好呀,要是不死怎么给你让位呀,那个丢人玩意儿!”一边说着,一边还伸出手,想要去摸紫苏的手。
谁知这手还没伸过去,就让郑令仪狠狠的框着仕女图的竹柄敲在了溪王的手上,溪王痛的捂着手,嗷叫一声,瞪着郑令仪,目光像是要吃了她似的,紫苏忍不住哭了起来,边哭边喊着:“王妃,不要!”
就算溪王把自己整成这个鬼样子,他也是个王爷呀,他们主子的相公,这女人对于男人来说哪是有什么优势的呀,他们王妃这一下子就已经是犯了七出了,这时候紫苏的脑袋里甚至想了,要是溪王真把这件事喊出来,她就替主子扛下所有的罪。
“你瞧瞧你这副模样,出去躺在一边,说不得乞丐都会接济你一碗饭吃呢!”郑令仪自顾自在说,这时候你绝对不会把它和平时那个端庄稳重的溪王妃有一丝联系,仿佛站在他对面的新闻是她的仇人似的,而不是像本该相濡以沫的相夫,事实上在证明你的心中宁愿要一个很多果断的敌人也不愿意要一个窝囊得像狗一样,被父亲骂了之后就缩在一起,自暴自弃的人。
任谁过二十多年富贵无比得人上人生活,都受不了郑令仪这一番尖酸,“你竟敢……这么说我。”接着又是一顿霹雳哗啦的碎瓷片声,他本来是想直接往郑令仪的头上打的,后来终究是顾忌到她的身份和郑家的势力,罐子全都在郑令仪的脚边碎了开来,幸好这几天穿的就已经有些厚了,偶尔有几片碎瓷片扎到了腿上也只是有些疼而已,但是最要紧的是一个细小的碎瓷片从地上迸溅出来,在郑令仪的脸上划了一条浅浅的红痕,紫苏尖叫一声,赶紧用手帕把郑令仪的脸捂起来,想拉着她往外走,可是她这一番好心郑令仪只是回了她一个“松手!”
接着又向着挺拔的松树一般站在这里
她站在这里就是对溪王无声的挑衅,气得他大步走向前,一只手狠狠的掐住郑令仪下巴,居高临下的说:“你算什么个玩意,女人,你只是个女人而已,就算郑家再疼爱你,怎么没说把一个家族都交在你手上,我要告诉你,女人永远都是男人的依附而已,我要你活的好就好,要你活的不好,你就永远活守寡,你不是想要孩子吗,那你怎么不想一想,哪个男人对着你那张脸还能生出什么心呢……”
溪王说了很久,或许他是把被父亲训斥的怒火全都发泄到了郑令仪身上,越说越痛快,心中也好了很多,把这结婚之后,所有的不如意,全都滔滔不绝的说了出来,但他的话中错的都是郑令仪,是她这个妻子,太过于严肃死板,他喜欢的是林欣那种温柔似水的女子,能够把男人当成天的女子。
这些天酒喝的太多了,导致他的视线都有些模糊,尤其是迎着光厂更加看不清楚了,他以为他的妻子被他训斥的呆呆站在一边,脸上充满懊悔,可是当他再靠近一步的时候,可她发现郑令仪的脸上满满都是嘲讽,似乎是在说着:这么一点小事,你也值得放在心上,我都不在乎之类的。
酒醒了,他也渐渐清楚了,刚才被酒精麻痹了理智又恢复了,却盯着郑令仪也不再说话了。
“说完了吗!”郑令仪说话的语气冷静得想让人发火,她的眼睛也紧紧的盯着溪王,明明比溪王矮一个头,却用一种傲慢的语气说:“你说我不配,那为什么不想想你,我宁愿我的相公是个纵横八海,脚踏四地的伟丈夫,宁愿他对我没有一点爱,也不要一个受了几句骂就知道喝酒玩女人的懦弱小人!”
说完这句话之后,郑令仪毫不犹豫的一甩头,扶着紫苏的手,“咱们走!”
这一路上紫苏都有太多的话想要说,可是看着他们主子冰冷的面庞又偷偷的把话咽了下去。
走过拐角的时候,郑令仪正好看见林欣带着下人默默站立在一边,她本来是不屑与林欣这种女人说话,可不知为什么她今天却停了下来,对着微微疑惑的林欣说:“去看他吧,他更乐意看着你,也许你这种女人才能满足他内心的报复吧,哼!”最后一声说不出是对溪王的嘲笑,还是对自己输给这么一个自己瞧不上女人的讽刺。
香珠小心翼翼的扶着林欣,等溪王妃走了之后才问道,“咱们这还去吗!”刚才那个算是溪王妃的威胁吧,这时候还是继续去的话,会不会触怒溪王妃呀?
“去,怎么不去,我这不去才是不把西王妃当回事儿呢,咱们别在路上耽搁了。”这话悠悠传开,香珠紧了紧皮。
第二天溪王便重新出现了朝廷之中,宁王有些惊讶,随即又恢复了,休息了这么长时间,只要他不想放弃,就绝对不会一直沉迷下去。
等到上面太监一句“散朝!”宁王一边给跪安,一边想着琉璃居最近新来了一批古籍,趁着今天散朝时间还早,不如去看一看,还有财哥儿最近爱看蟋蟀相斗,等会回去的时候给他买两只也好。
谁知溪王却堵在他回去的路上,他比林王稍微高那么一点点,这时候显着还是挺有优势,居高临下的扫视着宁王:“怎么这一会如意了吧,以后我可不会让着你了!”
“我没和你相斗!”宁王冷冷的说,气势上一点都不落下风。
溪王对宁王的话嗤之以鼻,“哼,你以为这话我会相信,你要是真正不想和我做的话,不如学上面几个哥哥,早早回自己的封地,生孩子多好,你这个样子可没多少说服力呀!”
“不管怎么想,反正我是不在乎的!”宁王眼睛里闪过一丝讽刺,他从来都没把溪王当作自己的敌人,一个脑袋不清楚的蠢货,怎么能跟他争,他一直想追求的不过是明宗的公平而已。
溪王似被宁王眼中的讽刺激怒了,一把拎起宁王的衣领:“那你敢发誓你对那个位置没有任何的想法!”
“皇兄,请你自重!”宁王悠闲地甩开了溪王的手,不遗余力的继续讽刺溪王,“你是不是傻的天真,我也是父王的孩子,想一下那个位置岂不是在理所当然,当然,我们头顶上那几位哥哥也不是什么吃素,谁叫他们对这个位置又回来,怎么一副心思,以后关于这种问题,王兄,还是不要与我探讨了吧,我有事就先走了!”说完不顾溪王的冷脸,从容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