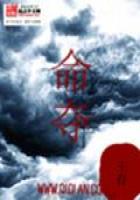第七章 谁在叫唤
昏迷时,噩梦连连,总是梦到血腥的杀戮与惨号声,四周一片火光,使人窒息在火场里,突然之间,有个声音劈开火光,断断续续地传来:
……醒来、醒来……不要贪睡了……
谁?是谁在叫唤她?
爹娘?佶哥哥?叱翱?
不!他们都不在了……不在了……
“媚君心!快睁开眼睛!快醒来,快快醒来!”
那个声音变得清晰了,却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睫毛颤动,缓缓掀开,眼前雾色淡去,景象渐渐清晰。
“啊,终于醒了!”
头上梳了两个抓髻、丫鬟模样的清秀女孩坐在床前,见床上人儿醒来,长长地吁了口气。
“你是谁?”
媚君心扶着微胀的额头,从床上坐起,疑惑地看着这个从未见过的宫女,如若没有听错,这个宫女方才还连名带姓地叫唤她。
“我嘛,”机灵地转转眼珠子,女孩娇笑,“你就叫我小丫头吧,张大哥就是这么叫我的。”
“张大哥?”她定睛看着这宫女,发觉这人的眉目间隐了些特殊的韵致,不像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闺中小丫头,倒像是坊市的瓦子莲花棚里招待过客人的机灵丫鬟,莫非……“是张缜安排你入宫的?”
“你还记得张大人啊?我还以为你脑子里只塞了‘叱翱’这个人的名呢!”
小丫头听她昏迷之中还在声声呼唤着这个人名,不由得与她打趣。
“叱翱……”心口如同被刀子一片片地剜割,她捂着心口痛苦地闭上眼,暗暗地咬唇,咬得唇破血流,也丝毫不能减轻心中的痛苦。
见她痛不欲生的模样,小丫头暗自吐了吐舌头,——幸好没有把叱翱被弃尸在乱坟岗的事儿告诉她,免得雪上加霜,让她再受刺激。
机灵地转动着眼珠子,小丫头故作不解地问,“媚姐姐胸口疼么?是不是又犯了心疾?哎呀,这会儿连圣上也找不到韩太医,这可怎么办?总不能耽误了媚姐姐的好事呀!”
“我有什么好事可耽误的?”缓过神来,媚君心颦眉问。
“成亲呀!”小丫头两手一晃,变戏法似的捧出了一顶金灿灿的凤冠,“今儿个良辰吉日,宫中举行大典,圣上要册封你为皇后,我可得抓紧时间帮新娘子打扮妥当,风光出嫁!”
“出嫁?!”听来可笑,她挑了挑眉,猛地掀开被褥,下了床,推开挡住去路的小丫头,径自往门外闯。
小丫头见她面色不善,出去定要闯祸,急得大喊:“柳媚儿,站住!”
心头一震,媚君心停了脚步,愕然瞅着小丫头,“你刚刚叫我什么?”
小丫头嘟着嘴儿问:“你还记不记得你的师父——秋娘?”
“记得!”忆及师父秋娘,媚君心神色间满是孺慕之情,“师父待我犹如亲人一般,不但教我舞艺,还请来名医为我疗去身上剑创伤疤,她老人家的恩情,我此生难忘!”
“那你还记不记得秋娘是怎么死的?”小丫头问。
“记得!”媚君心沉痛地点头。
“记得就好!请姐姐随我来。”小丫头将早已准备好的两个木匣子捧在手中,率先走出房门。
媚君心犹疑片刻,最终还是跟着小丫头走了出去。
媚娥宫掖庭西侧有一座小园,草叶枯黄,落叶遍地沙沙作响。二人来到此处,小丫头指着园中一棵樟树,问:“秋娘当年就是在这棵树上自缢的,姐姐知道她这是为了什么吗?”
媚君心走到树下,伸手抚摩粗糙的树干,幽幽一叹,“师父是为情所困,为了张缜……”
“不错!三年前,秋娘与张大哥情投意合,即将结为连理,而天帝只为了见识一下桑家瓦子红牌花魁的舞姿,就把秋娘强抢入宫。烈女不侍二夫,秋娘宁死也不愿屈从!媚姐姐,你可知道张大哥见到秋娘冰冷的尸身时,是怎样一种感受?”小丫头说着,眼眶微微泛红,“张大哥这些年忍辱偷生,一心只想为所爱的人报仇雪恨,你却如此倔强冲动,非要去图个解脱不成?你难道忘了——你是谁?”
“我是谁?我是……”喃喃着,她的思绪波动,小丫头的话,当真触动到了她的心!
“张大哥安排我混入宫中,就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天帝的心,为你而乱!我们所等待的时机已经成熟!”小丫头把手中捧的两只匣子打开,“这是张大哥托我转交的最后两份礼物,一个匣子装着霞帔,一个匣子放了白绫。姐姐如今也为情所困,是要步上秋娘的后尘,抛起白绫自缢在这棵树上,还是要佩带霞帔,为自己所爱的人做一些事?”
媚君心目光微闪,缓缓伸手接过一个匣子,匣子里叠放着七尺白绫。她抽出白绫,抬眼看了看小丫头。小丫头也看着她,目光中透出失望之色。她突然笑了,妩媚的眸子里焰芒炽烈,艳色灼灼!“丫头,你方才问我是谁,我此刻便告诉你,我是媚君心!媚——君心!”扬手一抛,七尺白绫抛于风中,她再次伸手,从另一个匣子里取出刺绣了金凤的霞帔,指尖轻柔抚过。
今日,她要披上霞帔,参加册封盛典!
卯时二刻,大将军府。
“兀刺将军!兀刺将军——”
一名将领手中高举半块虎符,匆匆奔入府中,冲正在书房整理军机密函的兀刺跪禀:“将军,圣上命属下送来虎符,今日盛典,由将军负责调遣兵马,护卫皇宫大内!”
一枚虎符,半块在圣上手中,半块落在了兀刺手中!京师南北两军,北军由他调度,掌京师的徼巡,南军由卫尉统领,掌宫门内屯兵。担当南军卫尉一职的,正是张缜!如今,圣上却将宫内警戒的重任托付给了兀刺。
“知道了,你退下吧。”
兀刺接过半块虎符,淡然挥了挥手。
那名将领退出书房后,书房左侧那面墙壁突然滑开一道暗门,大将军府的探子由暗道走出,疾步走到主子面前,拱手禀告:“主子,您让我盯的人今日便有所行动!”
“张缜终于按捺不住了?这个阳奉阴违、背地里耍花枪的跳梁小丑,这就要撕破脸皮与圣上兵戎相见了?”从探子手中接来密函看了看,兀刺手摸虎符,暗自揣测:“看来圣上也有所觉察,料定今日会有凶险,他终于把虎符交到了我的手中!”
“主子对圣上向来忠心不二,圣上这才放心把一半兵权交到您手中!”探子瞧了瞧那半块虎符。
“哼!在他眼里,我只不过是一只为他卖命效力的忠犬而已!”兀刺捂住绷带缠绑的右臂,眼神忽转幽冷,盯着手中虎符,缓缓地收拢手指,将它攥入掌心。
探子放下密函,穿入暗门,迅速离开。
将虎符收放妥当,兀刺霍地站起,大步走出书房,穿过庭院,走到一个铁皮小屋前,伸手探了探门上铁锁,确保小屋里的人逃不出这扇锁死的门后,他就站在门外,隔着门板往里喊话:“卜玄子,你这酸丁还活着吗?”
话落半晌,听不到屋子里有人答话,兀刺不死心地喊了声:“酸丁,十七年前你与天帝打赌——十七年后灭了大宗皇朝的,是破军煞星?”
屋子里静默片刻,忽然荡出一个怆然悲笑的声音:“十七了……十七年了!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十七年!终于有人来撼动帝座了?好啊!好!天帝施暴政,失民心,内忧外患,他哪里能保得住他的江山社稷?”
“十七年前,你与圣上打赌,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你这刁滑的酸丁!什么破军煞星?压根就没有这个人!”出鞘的剑又收了回去,兀刺对着门里的人冷哼,“罢了,留着你这条老命,看看这赌局里,谁输谁赢!”话落,他往门上设置的暗格里塞了一个水袋和干饽饽,关上暗格后,径自离开。
听得门外脚步声远去,铁皮小屋的门被人从里面推了几下,铁锁哐啷作响,推不开这道门,屋子里的人发出困兽般的低呜声。晨曦从卷裂的铁皮缝隙里透进来,黑暗的小屋里有了些微的亮光,道道光线照着墙上深深浅浅的一些凿痕,一个凿痕就代表了一天光阴的流逝,这小屋的墙上竟满是凿痕,一个蓬头垢面的人站在墙角,枯瘦如爪的手抓了一块石砖里敲出的碎石片,颤巍巍的往墙上又凿下一道痕迹。
十七年了、十七年了……
京师北军倾巢而出,由兀刺掌虎符调度,前往宫城。
铁蹄惊尘,雾霾浮空,今日天象阴晴难测。
辰时末,宫城之中,一条红毯铺上了御道,仪仗队两侧排开,数百名宫娥、太监迎着珠翠顶盖的凤辇,踏上红毯,徐徐前行。
凤辇行至东宫,掀开纱帘,宫娥簇拥着凤冠霞帔、手捧玉如意的媚君心行入天凤门,迈上仪凤殿。
鼓乐齐奏,掌故依照祖制礼法,主持盛典。圣上册封了后宫之主,大殿设宴,文武百官座无虚席。
酒过三巡,天帝双目微眯,看看身边人儿,媚君心容光焕发,媚眼如丝,当真姿色诱人!
“爱妃今日神色与往日不同哪!”天帝拥她入怀,往日倔强好强的人儿,今日偎在他怀中未语先笑,“今日大婚,与民同庆,圣上何不大赦天下……”
“爱妃!”天帝不悦,推了杯盏,“若要大赦天下,岂不是连那些反贼也要放出笼去,朕岂能纵虎归山!”
目光微闪,媚君心端起酒盏,吐气如兰,“不说这扫兴的事。今日良景,臣妾敬圣上一杯!”
席间,文武百官也纷纷敬酒。
天帝展颜畅笑,接了酒盏,痛饮而尽。
传令使殿上击掌,唤来乐师奏出音律,以助酒兴。
丝竹靡靡,穿着轻凉薄纱的歌女舞伎鱼贯入殿,香风阵阵,轻歌曼舞。有歌舞助兴,臣公们畅饮尽欢,有的已不胜酒力、醉态可掬,有的举起杯盏却把酒倒入袖中暗囊、滴酒不沾。这些不动声色、极力保持清醒的大臣,眼神都有些古怪。当一个身披轻纱、手持歌扇半掩花容的少女步入殿中,清唱独舞《苏合香》时,这些大臣的脸上都流露出紧张不安却又十分期待的怪异表情。
少女踏歌而舞,旋着曼妙舞姿,渐渐靠近坐在殿上的天帝,突然,少女挪开掩面的歌扇,冲天帝抛了个媚眼,坐在天帝身侧的媚君心,眉梢儿一挑,啐了一声:“小狐狸精!”
那少女似要故意惹恼她,舞着舞着,竟软了娇躯往天帝怀里倒去。
咚!
媚君心霍地站起,使了性子,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甩了红缎子的礼服罩袍,摘了沉甸甸压在头上的凤冠,一头棕红色的长发披泻,闪闪泛出一种火浪的光彩,双眸微嗔,却透着炽烈的、火焰般闪耀的光芒,紧身的一袭火红舞裙,看上去是那么狂野、那么大胆、又那么媚艳流融!
“俗劣舞姿,也敢出来献丑?”兰花指弹向那舞姿轻佻的少女,媚君心娇叱,“敢不敢与我比试一下?”
面泛兴奋之色,天帝抚掌大笑,“爱妃献舞,朕又可以一饱眼福!”
君主不尊礼教,喜怒无常,偏偏媚君心又如此大胆,当殿献舞,——皇后献舞,这还了得?众臣如坐针毡,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
媚君心挪步站到大殿中央,凤目微挑,斜睨着那少女,目光中满是挑衅意味。
少女微哼一声,迎上前来,歌扇一挥,罗袖翩翩,轻扬婉兮。她舞着舞着,却突然停了下来,怔怔地看着殿上另一道舞影——焰芒中簇绽的舞姿,惊虹艳影,众人看得嘴巴微张,魂儿也险些出了窍。
媚君心舞乱红袖,如飞蛾扑火,舞得激狂舞得恣意。天帝心猿意马,再也坐不住了,霍地起身,虎步冲上前来,迅猛地伸手抓住旋舞的人儿。媚君心这次没有躲开,由着天帝将她擒入怀中。困在他霸道的怀里,她笑着仰起脸,美目流波,妩媚诱人。
“爱妃,你这颗心是不是依从了朕?”如若不从,他也有法子让她顺从!
“臣妾早就失了心,圣上还看不出来吗?”被他禁锢在怀中,她巧笑媚兮。
今日,她已完全属于他了!——天帝仰头狂笑,如同征战沙场凯旋而归,独掌天下霸得美人,意气风发,他笑得畅快无比。
霸占欲得到满足,他打横将她抱起,阔步往里走。她顺势抱住他的颈项,把脸埋在他肩窝里。贴至他颈后的手,巧捻兰花,轻轻柔柔地沾上他的肌肤按了一下后,她突然扑哧哧地笑了。
脚步停顿,天帝猝然僵着身子钉足在殿上,突额上的“王”形纹路颤曲了几下,面颊抽搐,须发一根根地刺张,血色暴涨的瞳人罩住了怀中笑得异常妖娆妩媚的人儿。
媚君心缓缓地移开按在他颈后的双手,眸中焰芒炽烈,不屈不挠地迎向天帝噬血的目光。
丝竹声戛然而止,殿上气氛异常沉闷,死一般的沉寂,除了那些醉酒昏睡的臣公,其余的大臣们正襟危坐,一动不动,豆大的汗珠挂在脑门子上,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注视着天帝。
天帝面色铁青,膀臂痉挛似的抖震几下,突然松开了手。媚君心从他怀里脱身而出,退后几步,目不交睫地注视着天帝,鼻尖沁出粒粒汗珠。
天帝面色骇人之极,一震一抖地举起手来,摸上颈项,在颈椎上摸到异物,食指与中指一夹,随之拔出的竟是一根细如牛毛,却异常尖锐的银针!尖针刺骨,他并未觉得痛,颈椎上只是麻了一下,四肢却酸软无力。他站在原地不动,四下里望去,不见救驾的忠臣,只看得一个个图谋不轨的反臣贼子,趁这些人小心观察时,他垂下手悄然抓住佩剑,微微拔剑出鞘,锋利的剑刃割入肉掌,割得很深,血染剑鞘。受疼痛刺激,麻痹的四肢渐渐恢复了机能。
“爱妃,朕给了你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却为何偏要与朕作对,甚至要杀了朕!”天帝咬牙恨声质问。
刺入颈椎的银针是他的皇后赐给他的,当他的心为她而乱、当他以为她的身心已然被擒获时,那张妩媚的笑靥下却包藏祸心,这分明是一个粉色的陷阱!
媚君心深吸一口气,迎着他暴戾的目光,一字字地痛斥:“我要的不是那些!七年前你杀了我的家人,让我失去了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哪怕是金山银山,也无法弥补!”
“不错!”张缜从席间站了出来,面对天帝,大声指责:“你这暴君,挑起战火霸得帝位,不行仁政,不问民生疾苦,不学为君之道,滥杀无辜,失了民心,有何颜面坐这九五至尊的帝座!”
天帝须发怒张,怒目瞪着大殿上的臣子,看到的却是一张张愤慨的脸,而那些个只知阿谀奉承的马屁精们,则醉的醉、呆的呆,右丞相与他的同僚竟然都钻到了桌子底下,抱着脑袋簌簌发抖。
瞧瞧他都养了些什么样的臣子!就连他最信任的、最赏识的大将军兀刺,在这关键时刻竟也不见踪影,所有的人都背弃了他!
“好啊,很好!”天帝不怒反笑,使人心惊胆战地冷笑三声,步步逼向媚君心,话声暴戾慑人:“朕得不到的东西,毁了也罢!”
“天帝!你欠下的债还没还清呢!”
方才在殿上举着歌扇轻舞的少女冷叱一声,猝然从袖中抽出一把匕首刺向天帝。
天帝怒哼,出手迅猛,扣了少女的手腕,抖手一震,将人震飞出去。少女整个身子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飞出一丈远,“叭嗒”摔在地上,不见动弹。
“小丫头!”
媚君心急喊一声,欲奔上前去察看少女伤势,却被天帝阻挡了去路。
“还有什么人要与朕讨债,今日索性一并了结!”
天帝步步逼近,浑身散发着暴戾杀气。
这时,殿内几十名武将挺身而出,将天帝团团围住,拔剑厮杀!霎时间,仪凤殿内剑光霍霍,杀气森森。围上去的武将,忽又暴退回来,一个个剑断腕折,血珠迸溅!他们的剑刃无法刺入天帝护身的软甲;他们的拳头在天帝眼中简直就是豆腐做的,不堪一击!普天之下,能以武力战胜天帝的人,似乎还未出现!
张缜也持刀冲入搏斗圈中,文官们则堵在殿门口,筑起一道肉墙,以防兀刺调遣的京师北军前来救驾。此刻,兀刺若能率兵前来护驾,张缜等人的处境就岌岌可危!可是,他偏偏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