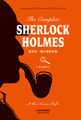跑到汪老大门口,汪老大正在劈柴,一见跑得满头大汗的陈策突然出现在面前,就问:“老庚?你是鬼还是人?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这是怎么回事?”
陈策说:“老庚,今天你要救我一命!”
汪老大说:“遇什么事了?”
陈策说:“抓我的人追上来了!”
汪老大站直身子朝门外田畈上一望,果然是追兵快到了。他灵机一动,放下斧头就喊他堂客:“大珍,你快打盆水提进房去洗澡。把房门闩上,一定要脱了衣服蹲在盆子里真洗。我要把老庚藏在房里!”
陈策说:“老庚,这不行!”
汪老大说:“别的办法才不行!只有这样!——老庚,你赶快躲在床底下去,我用烂棉絮把你封起来。”
汪老大的堂客还有些木讷,汪老大催她说:“救命要紧啊!快!他们追来了!慢一步就来不及了!”
汪老大一把将陈策拉紧就往房里推,又帮着大珍把水倒进澡盆里,让她赶快脱衣服。
陈策说:“老庚啊,这就太为难同年嫂了!”
汪老大说:“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你快啊!”
陈策见大珍已开始脱掉外衣,只好往床下躲了进去。汪老大用柜子里几床烂棉絮把床底下塞满,盖好陈策,然后出门来,拿上斧头继续使劲地在门口劈柴。他显得非常镇静,斧头也变得特准,一斧头劈开一块松树柴,可心里的惊涛骇浪总在翻滚不停!他想,要是团丁今天把他老庚抓走,他就只好用这把斧头和他们拼个死活!砍掉他们一个脑袋,他算是得了本,砍了两个脑袋可就连本带息了!
汪老大刚劈过几块松木柴,团丁就到了。其中一个认识汪老大的人劈头盖脸就问:“你把陈策藏哪儿去了?”
汪老大只顾劈他的松树柴火,那人连问了两句,他才直起腰来说:“你是在问我?”
团丁说:“你是不是想我用枪筒子给你耳朵挖挖耳屎?不问你我问谁?”
汪老大说:“你是要找茅厕?这村里到处都有。”
团丁极不耐烦了,“就是你大伏潭那个老庚,当过县团防局局长,后来跟贺胡子走了的那个陈策!”
汪老大说:“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你是说陈德铨啊,他几年前不是跟贺龙跑了吗?他到处打仗,谁知他把别人打死在哪儿、他自己打死在哪儿了?只怕是骨头都能打鼓了!”
团丁说:“你装什么苕!刚才过了河往你这儿跑来了。”
汪老大往手心里吐了把口水,在斧头柄上搓几下,把斧头捏得更紧,扬得更高了一些劈下去,又直起腰来笑笑说:“你们说这个话要是真的,我今天可要请你们喝酒!他是我老庚!我们从小在一起搬着梆硬的******比谁的尿射得高;六月天,我把他屁股槽里吐些口水、他把我屁股槽里糊些稀泥。你们今天要是真给我带来这么个好消息,我老庚还活着,我现在就捉鸡煮饭,让你撑得像老鸭婆走路!”
另一个团丁说:“别听他云南北京扯龙门阵!我们自己搜!”
汪老大说:“是嘛!你们自己搜!还费那么多口水跟我说什么!”
于是,几个团丁就四处翻找起来,先是搜了堂屋、灶屋和火塘屋,后又搜了猪栏茅厕鸡屏鸭棚,因为动作难免有些过急和粗重,就弄得胆小的鸡鸭到处飞扑,又怕又恨的狗们躲在仓库底板下汪汪乱叫。
忙了一阵,没有结果,认识汪老大的那个团丁见汪老大一脸泰然,就嬉笑着脸说:“汪老大,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你以为我们不会搜你这间房屋是不是?告诉你,我们就是要留下这间房屋最后搜,以便我们集中人员把房屋包围起来!我看,这回陈策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
汪老大心里一紧,他没有想到,这帮人先不搜这间房屋原是这样一个毒计!果然城府不浅!要真是被他们搜出老庚来怎么办?这时候在房里洗澡的大珍把澡盆里的水搅得哗哗响起,还在房里喊道:“谁要来房里搜?我在洗澡!”
大珍这么一配合,汪老大心里又多了几分把握,他平静了一些说:“是啊,我堂客刚从山上背了柴回来,正在洗澡。”
团丁说:“洗澡?骗谁?我得看看是不是真在洗澡。”团丁说着就往窗户逼近。
汪老大也往窗户边走近一步扬了斧头说:“谁要看我女人洗澡,我一斧头下去叫他脑壳变成西瓜瓣!”
大珍也在房内说:“谁敢朝我房里看,我让他挨冷炮子!不得好死!”
当兵的人最怕女人骂他挨冷炮子。团丁更火了,说:“不行!一定要搜!你要这么说,肯定有鬼!真洗澡假洗澡,我们一定要看了才算数!”
汪老大说:“我问你:你娘、你堂客、你女儿、你媳妇洗澡能让一个大男人躲在房里吗?这么简单的事你都弄不懂?”
那个带队的团丁一斜眼,几个人就往窗户扑上去,窗棂上贴的是连色纸,纸上贴有“福禄寿喜”的红色窗花。其中一个眼疾手快地一下捅破了窗纸,大珍趁机拼命地惊叫一声,骂道:“剁脑壳的,悖万年时的!流氓兵痞!冷炮子打的!”
几个团丁果真看见女人脱得精白,颤动一对****坐在盆里洗澡,于是,阴阳怪气地挤眉弄眼小声议论起来,一个说:“真白啊!”一个说:“我还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见女人洗澡呢!”
汪老大本想老庚没事了,他也就息事宁人算了,但一见那几个背枪的阴阳怪气议论自己的女人,又担心不把这几个背枪的赶快撵走,还可能会夜长梦多。他把脸突然黑下来问道:“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团丁们说,看清楚了,的确是在洗澡。
汪老大再次问道:“你娘洗澡,你堂客洗澡,你女儿媳妇洗澡,房里能让这么一个男人藏里面吗?”
领头的团丁说:“那当然是不会,当然不会!我们只是要查清楚你堂客是真洗澡还是假洗澡。是真洗澡,我们就放心了。别见怪,我们也是执行公务!既然人不在你这儿,我们再往别的地方找去。”
汪老大脸上突然飞来一阵乌云,说:“你们想就这么走人?我堂客惹你们了?我惹你们了,我堂客就该你们这么白看了?现在该我找你们了!你们看好了,我斧头吃肉来了!”话没有说完,汪老大手里的斧头就朝着那个捅破窗纸的团丁飞过去,银闪闪的斧口在空中翻飞出一道闪闪烁烁的弧光。那家伙头一偏,帽子就被斧头柄打下来掉在地上。汪老大追过去,捡了斧头还要再砍,几个团丁已跑得远远的,再也不敢回头。汪老大一直追到村外的田畈上骂道:“狗团丁!我****老母亲!我要到县衙门去告你们这些流氓兵痞!”
汪老大骂是这么骂得伤心,心里却一阵轻松。他站在外面一直看着团丁们走远了,才回家叫陈策从床底下出来。
陈策抱紧了汪老大,两人都高兴得流泪。
陈策说:“今天要不是你,我就见阎王了!”
汪老大说:“小时候我们在河里骑牛过河,那牛尾巴刷伤了我的眼睛,我差点溺死在潭里,还不是你拖着我过河,救了我的命啊!”
两人说着,拉了手进屋坐下。汪老大深深地慨叹着:“现在辰溪土匪与土匪打来打去,土匪与国民党打来打去,上头的民国党和共产党说是在搞合作抗日,但在辰溪,只要查出共产党就还是悄悄地杀,辰溪乱哪!整个湘西乱哪!”
陈策也跟汪老大悄悄说起这次回来的任务是贺龙要他回到辰溪来建立党的地下武装,积极支持抗日和为共产党在大湘西最后夺取政权蓄积力量。
汪老大说:“你要在这个地方干这些事,那是要提着脑壳啊!世态这么乱啊!”
陈策说:“不乱我回来干什么?就是因为乱我才回来!我回来就是为了治乱!”
汪老大迫不及待地说:“你回家看过了没有?”
陈策说:“还没有。幸好我今天不回家!”
汪老大说:“那你得赶快回家去看看。你爹、你堂客都是为你而死!”
陈策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汪老大又叹了句:“死得好惨啊!不知他们的生命都能换来些什么!”
6这个军权我们一定想方设法弄到
陈策只得深夜悄悄来到离别了几年的家中。
家已经完全不是当时那个家了,他们父子跟随贺龙走时,家中留下他的老父亲和妻子,可现在父亲和妻子都不在世了。没人照料的木屋,瓦面已满是天洞,椽皮和桁条都长了一圈圈灰白的鸡毛菌子。堂屋神龛上的香炉碗也掉进了瓦片,地上已有一层软软的树叶,阴湿处杂草丛生,荒若野外……陈策知道,自己不能哭,但是,情感的洪流不断冲垮理智的堤防,想起老父亲,想起可怜的妻子,泪水还是忍不住一串一串地流出了眼角。
在一位老人的引领下,他来到了村外的山头上,来到父亲和妻子的荒坟前。几度春秋,坟上都已杂草青青。陈策顺手从附近的灌木丛里折了两把树枝,一把放在父亲坟前,一把放在妻子坟头,然后,他在父亲和妻子的音容中跪了下去,沉浸在深深的夜色里,久久地不肯起来……
老人跟他说:“你带着儿子跟着贺龙走后,县里来了一大帮背枪的,说你是共党,将你妻子抓走。你父亲扬起锄头和背枪的拼死,挖伤了一个背枪的还不罢休,背枪的一气之下扣了扳机……你父亲被村民扶起时已经无法救治……你父亲死后只等着儿媳妇回来料理后事。可第三天,你妻子被一个矿工用板车拖回来时,身上盖了一块稻草毯子。村民揭开稻草毯子一看,她僵硬的尸体遍体鳞伤,看样子已经死了好长时间。家里无人做主,是向瑚姑娘到这个家里来和村民一起料理完你父亲和你妻子后事……”
陈策又听到了向瑚这个名字!
在两座坟前磕完头,他站起来,身体像是高大到顶天立地!他一言不发地从山上下来,直往县城里走去。
天一亮,县城的工人、学生、商人等各界人士纷纷上街庆祝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在学校、机关、厂矿、街头张贴宣传抗日救国的标语。在北门阁的城墙转角处,很多县民围在一起不知在看什么新鲜。陈策也走近去看,原是城墙上张贴了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颁发的《自卫团暂行条例》。围观的县民纷纷议论,根据这一条例,辰溪也要筹备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陈策心里闪过一线亮光,这应该是他建立地下武装的一次绝好机会!
最后一道晚霞从塔湾那边斜斜地照过来,夕阳的余晖让柳树湾的石板街像涂上一层浅浅的蛋黄,被脚板磨溶的石板似乎有了一层薄薄的透亮。陈策和老搭档向石宇走过柳树湾老街沿着陡码头下到辰河港。悬崖下的河滩上横横顺顺地躺着在长河里累病了而等待修理的大小船只,离开了河面的船只躺在沙滩上,像秋季里农民家门口的桐筛里晒着的干鱼。不少船工在那里修船,扎葛渣,涂洪油,绷梆子,下钳子,斧头、刨子和凿子奏出的音响被河对面丹山寺下的悬崖又反回来,整个河谷被这铁木声塞得严严实实。河边还有堆成无数山峰的辰溪煤炭,煤山的下脚有洪水留下的浸泥,看来,是放了很久没有销出去。河港里更是泊满了上洪江下常德的各种船只,桅杆如林,风帆如云。落日余晖在船与船之间的水缝里浮光耀金。在丹山寺与县城之间来往的轮渡总是不知疲劳地来去……为不让别人听见谈话,陈策和向石宇走到河港最外边的船头上坐下。
陈策说:“这次县里要成立抗日自卫团,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这个军权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弄到手!这对于我们将来起码有两大好处:一是有了合法身份开展组织武装活动,一些地方团丁不敢再来加害;二是有了这个本钱,日后才好进一步扩大武装。”
向石宇说:“我也在想这件事情。能拿到这个军权当然好,但绝不那么容易!现在辰溪多少人都盯着,布告刚贴到城墙上,听说就有不少人送金递银在买这个职位。”
陈策说:“就是摘星星,我们也要努把力!当年我们搞团防局时靖匪保民,还在上上下下留有很好的口碑。我们不靠官方,也不送钱,还是可以像当年一样,请当地社会名流来保荐我们。”
向石宇说:“如今已不是当年。当年孙中山先生刚推翻帝制不久,地方官吏都在接受新思想,都在尝试民主;而如今,这些官吏见上面一会儿推翻皇帝,一会儿又出了新皇帝,老皇帝新皇帝也都相差无几;一会儿国共合作,一会儿生死冤仇,说好就好,说坏就坏,也没有什么规矩。他们也都把中国的政治看白了,表面对上面说好听的,暗里都只忙着为自己捞钱。他们以为最实惠的就是自己捞到钱!”
陈策说:“官员捞钱是事实。不过,在钱与乌纱帽之间作一选择,他们还是会选择乌纱帽。钱是毛,乌纱帽才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有一位可以威胁辰溪当地官员乌纱帽的人出面做县长的工作,我想这事还是有成功的可能。”
向石宇说:“那就只有去找向绍轩校长,只有他才有这个分量,也只有他才可能真心帮助我们。”
向石宇与向绍轩同为辰溪向家园人。向校长是孙中山手上的国民党元老,曾留学英国,从事资本主义土地经济和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研究,是全国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向石宇在武汉明德大学求学时,就受到当时的代理校长向绍轩的影响。近因华北被日军侵占,武汉失守,日军进逼湖南,长沙大火,常德桃源濒临沦陷,省立桃源女子中学为避战乱,已迁到离辰溪县城不远的潭湾镇野猫州一带,临时校舍都坐落在辰河岸边。此时,向绍轩正任桃源女子中学校长。
第二天,陈策和向石宇从中南门码头过河到大路口,往潭湾去请向校长出面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