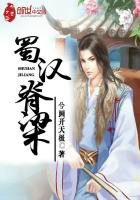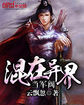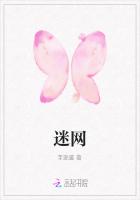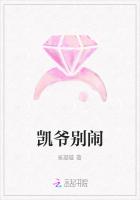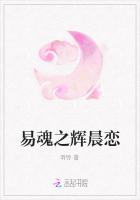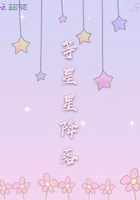林孝忠接信,匆匆忙忙地赶来。但梅春将自己反锁在屋中,不愿相见。
一扇薄薄的木门阻隔开了春梅与林孝忠的情感世界,任凭他在门外如何劝说,门内如死一般的寂静。只有从这房里透出来的那一缕缕印度檀香的薄烟,从窗棂缝中悠悠地飘出来,又沿着板壁向上升,循着屋檐卷入小天井中,随着风慢慢地消灭在天际。
天井中种着一棵腊梅,林孝忠茫然的眼光落在枝干上,在枝杈上已然冒出了点点芽头,全然不顾这天寒地冻的时节。林孝忠猛然间想起这位梅小姐的脾气,也正是这种不顾一切的敢爱敢恨,她今日之举也应当要在预料之中。
无奈之际,林孝忠只好悄悄地回到前院书房中,闷着头在那儿抽雪茄。
午前的阳光很好,山谷之间也给人一些暖意。门外传来轻轻的叩门声,林孝忠咳了一声代替回应,“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容儿进屋来禀报慈音师太来访。孝忠在那堆了半盆烟灰的烟灰缸上灭了雪茄,起身整了整衣裳,走出房门,在一片暖融融的阳光中,精神为之一振,在容儿的引导下来到前厅。
慈音师太正在厅堂前观赏天井里早开的梅花,虽然还是冬天时节,但似乎已不太寒冷了。中午的阳光,让人有一种暖春的感觉,这院子里的梅花似乎也发生了对时节的认知错误,早早的就发出了花骨朵。天井的两棵梅花,已经生长了数十年,粗壮的树枝上紫褐色斑节累累,树冠有二米高,一树是白色腊梅,另一树是胭脂红的,在阳光下显得生机勃勃。
慈音师太年近六旬,白净的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忧念,古板少笑,中等身材,倒还硬朗,脚踏一双饰有云纹的灰色棉鞋,身着一袭灰色僧袍。她在花架前站立着,纹丝不动,只有宽大的衣襟在寒风中微微飘摆,分明是一个世外之人。
慈音师太俗家姓郑,是官宦之后,祖辈是江南的一家织造商人。早年间,靠着到江北贩卖棉花积下了一大笔家产,传到祖父时已开办一家纺纱厂和一家织布厂,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望族,在家乡扩建了祖宅如意坊。如意坊是当地最大的建筑群,内有雕梁画栋的99间大屋,而最值得称道是,在后花园建有一栋罗马式的3层楼房,其中还有一大间西洋舞厅,如意坊的建筑风格堪称中西合璧。当年老爷的三姨太是一位上海女演员,喜欢跳交谊舞,每半个月便在此办一场舞会。
但是,她的祖父却不指望自己的大儿子继承这份家业,而是殷切地希望他能够考取功名。这实在是老人家的奇妙心机,他意在使自己的家族成为一个红顶家族,官商相助,财源亨通。因此,慈音的父亲从小苦读,但是他时运不济,多次考功名而不第,一直蹉跎到年近四旬,依然一事无成,这成了老爷子的一块心病。最后,为了得一个功名光宗耀祖,不得已捐官,谋得了一个西藏边地的七品县官。这个官是无助于家业发达的,而此时郑家也已过了兴盛之时,处于一个守业的阶段。
西藏边地,天高路遥,从江南进藏谈何容易。于是郑县官将家眷留在故乡,赴任时只带了一个书僮阿杰。他一路就走了将近三个月,风尘仆仆,舟车劳顿,刚到任就病倒了。这一病将近两个月,好在官衙的书办精通医术,细心施药调理,但到病愈时人也脱了形,当然这一切他远在江南的家人并不知晓。
慈音俗家姓郑名凤琳,父亲进藏时,她年方3岁,母亲是家乡一户大庄主的女儿,在当地颇有家财。但令她母亲没有想到的是,为了圆老太爷一个做官的梦想,自己丈夫竟然远赴西藏去当了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从此天路远隔,更未曾想到从此之后,夫妻再无团聚之日。
凤琳5岁时,主持梅庵的乡人道圆师太返乡化缘。郑家是当地乡绅首富,乐善好施,多年来总是慷慨地资助梅庵。因此,道圆师太每次返乡,总要到郑家探访拜谢。此次探访郑家,道圆师太发现有一个小姑娘一路跟随着,那笑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师太手中的那一串檀香木制成的佛珠,有机会靠近便会伸出她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一串佛珠。
老师太见状问道:“小妹妹,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小女孩回答说:“这是一串佛珠。”
师太又问:“你知道这一串佛珠有多少粒吗?”
“一百单八粒呀!”
“你喜欢佛珠吗?”
“我很喜欢,我奶奶房里也有一串啊,但是我觉得您的这串更好。”
深喜凤琳小姐知书达礼,老成持重,似乎也与佛主有缘。因此,师太有意引渡小凤琳,但恐郑家不乐意,不敢直言相告。在告辞时,师太牵着凤琳的小手,送了一串的印度檀木数珠作为纪念品。她对凤琳说,今后若有机会欢迎到梅庵做客。小凤琳只道是这位老奶奶邀请她去山上游玩,高兴的乐不可支、手舞足蹈。没想到两年后的秋天,郑县官管辖的地界发生瘟疫,当地缺医少药,连官衙的书办都充当郎中为民施药,郑县官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命丧藏地。阿杰扶灵将郑县官送回江南,一路又走了两个月。
灵柩返乡时正是三九隆冬,这一年江南大雪,郑家里里外外一片飞白,灵堂里遍悬白布幔帐,房外白雪飘飘。郑老太爷痛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时才后悔将儿子送上这不归路,老人家终日郁郁寡欢。在家设置的灵堂上,明烛高香,烟火不断,僧道两班轮流做法事。但就在一个大雪纷飞之夜,守夜的丫环极其困乏,碰到屋角的烛台,刹那时火苗烧着布幔,灵堂顿成一片火海。
江南雪夜,朔风助火,火龙从灵堂窜上屋顶,郑家上下乱成一团。虽然家丁佣人与四邻乡亲纷纷灭火,怎耐火势太大,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自从府中火起,相邻的地保就敲响了急促的锣声,镇上水局的水龙队赶到时,整个郑宅已烧成一片火海,逃生的人们衣裳不整,特别是女眷们披着衣被在雪地里哭成一团。水局的丁勇们拖着水机靠近火场,将院外的水塘砸开冰面,向火场喷水,但是无济于事。郑宅的这一场火直烧了三天三夜,把这一份诺大家产烧的精光。
郑家在城里还有生意与房产,七零八落的—家人进了城去。小凤琳从火海中逃生,四处寻不着母亲,最终从火场的遗骸中发现了母亲的遗物,确认她葬身火海。
几个月之间,小凤琳痛失双亲。跟随祖父母与其它亲眷进城后,幼小的心灵无法从这灾难中解脱出来。她心如死灰,终日以泪洗面。这时,她想到了梅庵老师太对她的关注。因此,凤琳孤身一人进了梅庵,削发为尼,法号慈音。在道圆师太的指导下苦读经书,得悟佛法。老师太圆寂后,慈音继任主持。
近来,慈音发现林府的这位姨太太心事沉重,茶饭不思,隔三差五就到梅庵进香,离开时总有那一种依依不舍、流连忘返的神态,于是和梅春做了一次长谈。
梅春在师傅面前哭诉陈情,慈音也不免落泪,同是落难女人,俩人惺惺相惜。在与师太多次沟通之后,梅春逐渐产生了出家的想法。她一到梅庵,就感到心中压着的大石块消于无形,这里能让她从痛失儿子的梦靥中脱出心来。
慈音师太听说林孝忠来山庄,于是趁天气晴好前来拜访。毕竟林孝忠是一家之主,姨太太想出家能不询问人家夫君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慈音师太心中还是犹豫的。
听到走廊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慈音师太忙转身顺音而望,双手合十,口诵佛号:“阿弥陀佛,林施主,老身打扰了。”
“师太久候了,请进,请进,”林孝忠上前恭身施礼。梅庵是林府的家庙,历代家长均十分礼遇这里的主持。林孝忠诚惶诚恐地将慈音师太迎入客厅,“请上座,师太。容儿看茶。”他向后厅的丫头打了个招呼。
慈音师太在客座那把鸡丝木精制的太师椅上恭身坐下,一脸慈祥地望着林孝忠:“林施主一向可好,老太太身体安康,婉珠太太都好?”
“承师太牵挂,老母身体尚好,只是入冬以来风气又犯了,脚腿不太便利,内人一向很好,在家照顾老母。”林孝忠对慈音师太十分敬重,他小时候就常随父母来寺里烧香,而且在暑夏季节,老太太还会来寺里小住一周,他也经常跟随在侧。但上中学后就来的少了,一晃几十年过去,慈音师太也老了许多。
“来年入夏后,可迎请老太太来此山庄小住几时,她老人家有几年未来这里避夏了,老尼也很念她,平日里常为她老人家上支平安香。”
“谢谢师太菩萨心肠,回城后一定上复老母,转达师太的挂念。”
容儿从后堂送茶进来,她轻轻地将一盖碗杯放在师太左侧的红木茶几上:“师太请用茶,这是老爷带来的武夷岩茶。”接着也给主人上了一杯茶。慈音师太慈祥地看了看容儿,低声致谢。孝忠端起茶杯道:“师太请试茶,不知堪用否?”
慈音师太双手合十道了个谢,轻轻端起盖碗茶杯,先细细端详着茶杯,这是一组景德镇出产的青花薄瓷茶杯,瓷质细致温润,器形雅致,慈音师太十分喜爱。她轻轻将杯盖揭开,只见浅金黄色的茶汤飘着白气,卷起一阵幽香,师太呷了一口茶汤,细细品饮,不住地点头称道:“汤纯味正,应是天心禅寺的茶吧,好茶,好茶。”
“师太知茶,在下钦佩,这正是武夷天心寺的岩茶,自祖父手上经营茶叶后,我家就是天心寺的长年香客,年年茶季都去进香,蒙受师傅馈赠此茶。”林孝忠敬重地望着师太说,他还真是没想到,慈音师太会认出茶的产地。
“知茶之誉,实不敢当。天心禅寺有一位师兄,知老尼好茶,每年都托人捎来一些茶叶,故有所知。”说到这里,慈音师太轻轻地放下茶杯,正襟危坐,望着林孝忠,“林施主,老尼先前给你写过一封信,告知贵梅姨太的近况与她的心思。老尼今天来访就是想倾听林施主之对策。”
“嗨。”林孝忠深深地叹了一声,“非常感谢师太对梅春的关心与爱护。在下对她也是深怀歉意,是我无能,愧对于她,虽爱于她,却无助于她。”
“阿弥陀佛,施主不必自责。大户人家自有十分严厉的家规家法。老尼也是大户之后,深知其中道理,必须循规蹈矩。只是梅姨太对老尼表述倦于家居,盼望能到庵中修行。此事甚大,老尼不敢擅自作主,必要报于施主。老尼大胆告诉施主,梅姨太天资聪慧,这半年来已读多部经文,善与老尼对答。梅姨太确有佛缘,老尼也有意渡她摆脱烦恼,不知施主意下如何。”
在孝忠小住山庄的这几天里,梅春一步也没有离开她的住房,不要说与他相见,甚至连门都没有对他开过一条缝。每日里,只有容儿从内侧的小门给她送食送水。在林府祖传规矩中,这扇小门仅容丫环出入,对男主人也是禁足的。
梅春的每一天都是在卧室旁的佛堂中度过的,她读经书,敲木鱼,烧高香,食素斋,这一切都已表明决意循入空门。而且这不是仅在这几天里发生的,山庄的管家与佣人们也证实了她这几个月间的变化。收到慈音师太的书信之后,林孝忠已有这个思想准备,如果无法劝回梅春,也只好由了她。林孝忠还是不想让梅春剃度落发为尼,他想这么一座山庄还是可以容得下她的。她完全可以在家吃素礼佛,只要我们不下来,这里的管家佣人可以保证她过上清静的生活,至于梅庵,她可以时常走动走动,因此,林孝忠将他的想法告诉了师太。
慈音听罢不住点头称是,心中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原来师太也有一个心结,从林府对梅春的安排上可以看出,林府对她还是有一份照顾的,不然是不会将一个大庄园给她独自使用。虽然梅春想循入空门,但慈音师太也不敢真正的就为她削发。现在林孝忠提出的这个方案应该是眼下一个最好的结果。慈音师太高兴地答应:“阿弥陀佛,施主请放心,老尼定然全力开导梅姨太。告退了。”慈音师太起身告辞,飘然离去。
慈音师太离去良久,孝忠仍坐在厅堂的太师椅上,心中的意念难以平复。
此时,虽然天井中阳光灿烂,山风一阵阵地从敞开的门口吹进厅堂,让他感到冷嗖嗖的。他喝了一口残茶,正要起身离开,忽见管家小张在门厅前探头。
孝忠问道:“小张,有事吗?”
“老爷,上午有船到岸,送来公司的一封函件,刚才老爷有贵客不便打扰。”说着管家双手托着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进了门来。
孝忠接过信封,这是公司陈襄理发来的。小张从厅堂左侧百宝阁的抽屉中取过一把剪刀,帮老爷裁开信封。孝忠从信中得知,年前与商会同仁商定的今年与南洋刘氏金融公司合作举办江南第一银行的事有了眉目,刘氏的副总经理近日将来访,陈襄理请总经理返城主事。
当天傍晚,在管家与容儿的陪伴下,孝忠来到码头,这里停泊着一艘豪华的游船,这是林府人来住古镇庄园的专属交通工具。
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太阳在远山的峰峦间渐渐坠落,山后的天际间一片灿灿红霞,荡荡的河水反射出闪闪白光。孝忠回头望着一片雾霭中炊烟缭绕的山庄,眼中泛出泪花。他顿了一会儿,转身对容儿说:“容儿,你要细心照应好梅姨,她有何需求要尽快交待张管家去办。”
容儿忍住眼泪不流下来,使劲地点点头,她知道老爷这一去不会轻易再回来了,一则是公司里业务繁忙,二则他也是一个伤心之人,真是爱到伤时心已死。
在众人的目送中,游船缓缓地驶离码头,风帆鼓荡,渐渐消失在越来越浓的雾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