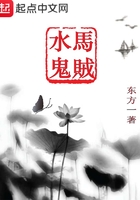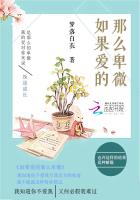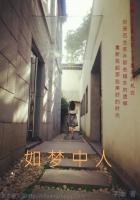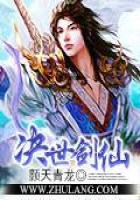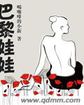林府在罗城历史悠久。90年前,高老太爷林传宗于只身来到此地,至今已传了六代人,而且分支多脉,人丁兴旺,家业兴盛。
林氏原籍在距罗城100里地的崇安县城。林传宗的父亲是秀才出身,在县衙当师爷,守着一份清廉的俸禄,一家五口人倒也生活无忧。清咸丰年间,林传宗15岁时,拳乱四起。当年5月,县城被拳匪包围。一个月的围城让这个只有100名团丁的小山城撑不下去了,人困马乏,人心惶惶。一天凌晨有人开门献城,天明时分县衙被围。而县老爷早已在前一天晚上举家易装悄悄离开了,整个衙门只有林师爷守在签事房中。拳匪没有为难这个老书生,只是将他赶出了县衙。
匪乱持续了半年,农民四散奔逃,地里的庄稼荒废了。那一年秋天,城里开始闹饥荒,米价飞涨。林师爷本来就靠一份薪水养家,现在小山城落入乱民之手,师爷一家的生活难以为继,只能靠往年的一点积蓄度日,一家人每天就喝些粥,吃一些豆腐咸菜。
乱世之时,私塾书坊都停课歇业了,在家的学生们也无心读书。林传宗终日默默无声地守在家里,帮母亲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妹,早晚倒也有心无意地翻看课本,但常常看着书就发呆,悄声地叹气。这一切都被林师爷看在眼里,他知道儿子不安于在乱世中混日子。但林师爷是个读书人,除了写字,一无是处。看到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不少人家的孩子因为无法度日纷纷投了乱匪,他不愿儿子也走这条路,就决定让传宗下山去投奔在罗城做手艺的堂哥。这天晚间,林师爷将这个想法与老婆吴氏做了商议。吴氏不忍尚未成年的儿子离家独行,听着丈夫的话,不禁失声抽泣。
次日早晨,天气阴冷。这一段时间,孩子们无所事事,每天都起床晚。
林师爷要与儿子谈说心中的盘算,便将全家早早地叫起了床。吴氏正将那一小锅可以照人的清汤米粥分进一个个陶碗里,听到丈夫说起这个事,手中的饭勺不禁发抖,一勺的清粥洒落在桌上。她望着只有16岁的传宗,一时语塞,两行眼泪如脱线的珍珠不停地落下。“传宗呵,爹娘对不住你了,你才16岁,却要你离开这个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这个乱世中你读不成书了,这里也没有你谋生的路。我们想让你到罗城去投你的堂叔,他是罗城东街福记皮箱店的老板,你到那里去学徒吧。”林师爷一副可怜巴巴的神情盯着儿子。
林传宗低头喝粥,16岁的他无法表达对这件事的判断,作为师爷的儿子,虽然不是富裕之家,但他倒也没有过什么苦日子,在读书、玩耍中长大。今天要离开这个安稳的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但这半年来世事动荡,家道中落,他有切身体会。他终于放下碗,抬起脸来,冲着爹妈点了个头,“嗯”的一声刚出口,眼睛也红了。这一天里,林传宗啥事也没干,只是一直坐在门口守着弟弟妹妹,看他们在院里玩。
当天晚上,林师爷在煤油灯下给远在罗城的堂兄写了一封信,拜托兄长念在同祖同宗的份上,多多看顾传宗,吴氏在床边默默地给第一次出远门的儿子准备行李。说是行李也只是简单的换洗衣服而已,用一块包袱布打了一个包,当然其中还有一包晚饭时烙的粗面饼与一瓦罐家制的咸菜叶子。母亲备好儿子的行李,悄悄地来到孩子们的床前,三个孩子均已入睡,两个幼儿睡得正香,而大儿子的眼角却挂着一滴泪珠。母亲不禁一阵心酸,依在门框上独自垂泪。
次日早上,林传宗在父母亲的千叮万嘱中,背上包袱。临出门时,母亲又递给他一把半新的油布伞。这一天,小城里有几个青壮年人结伙出行,他们在这个日渐败落的小镇中已看不见生活的希望,还因为他们在城里有远亲近戚,这点燃了他们重新生活的一点点希望。林师爷将儿子托给这些乡亲,请他们带传宗到城里去。
对于林传宗来说,离开家庭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显然是出于一种茫然与无奈的心情,他知道时世艰难,家计维艰,不能再在家无所事事,因此他对进城投亲谋生还是怀有一些希望的。一行人在镇上租了一辆牛车,一路无话,走了两天,这才进了罗城。同行的邻家大哥按林师爷的交待,将林传宗领到东街唐家胡同去找福记皮箱店。
从乡下来的孩子,进城是一件令人眼花缭乱的事。同行的乡人在城门口为林传宗问明了方向,大家相互告别,各行其道,很快就分散到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去。
林传宗抬头看了一眼城门上的大字牌匾,上面是清光绪年间本地一位状元手书的楷字“景福门”。天色渐晚,城门外的江水上泛着落日的红光,一阵江风从城门洞中吹进来,冷飕飕的,林传宗打了一个寒颤。他低头瞧了瞧脚下的青石板路,这条路从城门口向城中延伸,两旁的数十家商铺中已经亮了大大的煤油灯,路灯也点上了。林传宗整了整背上的包袱,腹中感到一阵的饥饿感,他紧了紧腰带,向城里走去。
唐家胡同位于“景福门”内的一条青石板街上。这是当地的一条商业街,从明未开始各行各业聚集在此,已有数百年历史。沿街两侧排开数十家店铺,这里有享誉四方的福祥丝绸店,大同鞋帽铺,建春茶庄,快活林餐馆,多家日杂百货的买卖也十分兴隆。在一段街面上有多家手工艺店,打铁铺,棺材店,响器行,还有就是林传宗此行的目的地-福记皮箱店。他沿着青石板道一路走去,东张西望,希望快点找到福记皮箱店。
天黑以后,各家店铺的灯光照着自家门前的路,加上那些昏暗的路灯,这一路上还是明晃晃的。走过半条街,一堂大门面出现在眼前,门前的货架上叠着从小到大的数个棕色漆皮箱。店面上方的大招牌,红底黑字写着“福记皮箱店”,他心中像揣着一只小兔子蹦蹦跳,终于找到地了。林传宗在门前停下脚步,向店中张望。
福记皮箱店的店面并不大,店堂大木架上整齐地堆着不同尺寸与颜色的牛皮箱,这是城中几家箱柜店中生意最好的一家。牛皮箱是城里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置办家产,娶媳嫁女都少不了皮箱。皮箱店的老账房李先生正在灯下记着当日的台帐,冷不丁抬头见大门外有一个孩子探头探脑,他放下手中的毛笔,盯着这个孩子。
门外天色已黑,路灯微弱,他看不清这个孩子的面容。从他的装束上看,一身黑色的对襟外衣,光脚穿着一双沾着泥的老布鞋,提着一个布包袱,头发乱蓬蓬的,站在门外犹豫不决的样子,像是来自山区的孩子。
李先生咳了两声,清了清嗓,端起黄铜的水烟筒,一边咕噜地吸着烟,一边踱出柜台,来到店门口,他才看清这个孩子的容貌。这是一个清瘦的孩子,虽然衣着简朴,但态度文静,面上挂着一丝拘谨的笑容。
李先生吸了几口烟,问道:“孩子,天色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做啥?”
林传宗找到地方了,心中颇为高兴,但他仍然感到紧张,因为这位老先生的眼光不太友好地盯着自己。传宗定了定神,舔舔一天没有喝水而干裂的嘴唇说:“老先生,我叫林传宗,从崇安县来,我要找这里的林老板,我有一封给他的信。”说着林传宗放下布包,从中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土纸信封,双手托着,恭恭敬敬地递给老先生。
李先生对眼前这个孩子得体的言行有些吃惊,他忙放下黄铜水烟壶,伸手接过这个信封,看了看信封上写着的“福记林老板亲启崇安县林拜托。”
“孩子,你进来说话”李先生说着向店里让。
林传宗进了店铺,随手将包袱放在门口的地板上,盯着这位老先生,“老先生,你是?”
“我是本店的账房,老李。”李先生又从柜台上操起那把黄铜水烟壶,吹燃草纸火引,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在太师椅上坐下,对立在一边的传宗说:“林老板已经回家去了,但他前几天和我谈起住在山上的你们一家,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他很牵挂你们。今晚你先在店里住下,林老板明天一早就会回来。”
林传宗听罢狠狠地点了个头。他感到口干舌燥,下意识地舔舔舌头。
李先生放下水烟壶问道:“孩子,你还没吃晚饭吧?”
“我包里有面饼。”
“不,不,你都来了,还能再吃干面饼。你先等一等,我让人到街对面的饭馆给你叫碗面来。”
“小陈,你出来一下。”老李转身向柜台后的侧门叫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