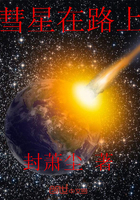推开那扇老旧的木门,蛛丝像一条条手臂,想把那扇尘封已久的门关上。
门外乌云压的很低,天空像是快走进了黑夜。
我打开灯,暗黄的灯光照出了房子内里的轮廓。
顺着木梯爬上阁楼,黑暗的阁楼里看不见任何东西。
我掏出手机,光亮瞬间使阁楼上的布局一览无余。
阁楼左边的角落里,上了灰的油纸布盖着一个漆黑的物件,那就是阿婆让我上来查看的棺木了。
或许是阿爷的意外过世,又或许是病魔使她在床上躺了近半年。阿婆越来越喜欢把死亡挂在嘴上。
自从阿爷意外去世后,阿婆说一个人在曾经待过的老房子里会感到害怕。鉴于我们常年在外,便把阿婆交付伯父赡养。
到后来,阿婆不再对阿爷的意外过世耿耿于怀。便提出了回到我们家来。
父亲在深夜里跟我商量,说出了他的顾忌。当初迫不得已把阿婆交付给了伯父,这几年也算是让阿婆吃穿不愁。要是现在接纳了阿婆回家,我们倒是可以留一个人照顾她。怕就怕这样反复,毁了伯父声誉。招来阿婆被虐待,不得已要和小儿子一起过的闲话。最终闹的兄弟不和。
我理解他的顾虑,于是提出我不再远去他方。就在家乡安定下来,阿婆要有个什么事,也能在短时间里有个照应。既然阿婆喜欢留在老家,那就把家里水电气和米油盐菜都备好。白天她约上那些老朋友听苗歌也不至于打扰到伯父他们。想自己下厨了,也有个下厨的道具,相互也有个照应。晚上回伯父家过夜,既回避了流言碎语,也放下了她夜晚无人照应的担忧。
阿婆不识字,可记性却还是极好的。一部老人机的使用流程说了两遍就记得。所有家人的电话号码我给她存上,全用标点符号作为识别。她能一个个准确的对号入座。
在邻居老太家的牛棚拆了以后,留下了一堆稻草和牛粪混合发酵的有机肥。阿婆一个电话把我叫回家后,整整挑了半天的牛粪,铺出了一个肥沃的菜园子。从此她除草种菜,倒也乐此不疲。
一直到她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堆不干净的东西在那口老水井边上。阿爷也在那里游荡!
我对鬼和神是区分不开的,从小听过的,人死后都会成为鬼。有些鬼是害人的,比如说夭折,比如在家外面死的。比如说非正常死亡,见了血的,喝了药的。上了吊的,或是摔了跟头死的。都属于会害人的鬼。这类鬼,是被唾弃的,不能跟祖先一起享受后人的祭拜,也没有保佑后人的能力。
想要回老家,跟着祖先们一起享受后人的惦念和祭拜,
被后代敬仰,给后代赐予心愿的实现,就必须是自然老死在自家床上,舒舒服服的闭上了眼睛,因果里说的是此人生平善良或是没做过有悖于良心之事。才会有了一条不被折磨的回家之路。
阿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晴天里,赶着那只早已退休的老水牛。点着烟叶卷,背着一把镰刀就上了山。
他每天的流程几十年没改变过,半山休息,点一支烟。到顶休息,点一支烟。把牛赶上山畔,远离土地里种上的庄稼。然后往手心里吐上一口唾沫,提起镰刀在自家的树林里卸下一些树枝绑好。杉木树削了两头尖的胆子插进绑好的树枝捆上。找一处阴凉地,又点上一支烟。对着起伏的山间峡谷唱几曲上五里苗歌。苗歌从一个峡谷穿到另一个峡谷,在山里回荡。没有孤独,没有死寂。鸟儿的应和,树枝刷刷作响。山泉水也跳跃了起来,山里像是开了一场对歌会。
阿爷脾气大,除了那只老水牛和我两个妹妹没被抽过外。家里的男人几乎没有没挨过揍的。有时候吃饭吃的好好的,一记闷梨子就落在了脑袋上。不敢反问,他也不解释。剩你一肚子委屈,哪里安静跑哪里自己哭去。
然后隐隐约约的听到他在外面嘀咕,“吃饭还堵不上嘴”
那一天,阿婆把晚饭做好了等着阿爷打完柴赶牛回家吃饭。一直没等到,便拜托隔壁邻居帮忙去找找。后来消息传回来了,阿爷坐在田坎下。浑身已经僵硬。
伯父赶到的时候,一帮人围着没有一个人敢去碰触。在野外死亡在族人概念里是件犯忌讳的事。没有人是愿意主动去惹上不干净的东西,一直到伯父找来了木梯子。才七手八脚的帮忙把人抬回了家。
梯子架着人回到了院坝上,阿婆死活不让抬进家门。
父亲赶回了老家哀求,说怎么说都是我爸,认祖归宗,做上几堂法事是作为子女应该尽的孝的。
不管怎么请求,阿婆就是不松口。她说,阿爷没在自己房子里过世,是天意对他良心丑的惩罚。这一辈子没对你们好过脸色,还非打即骂。让他进家门,会祸延子孙,多灾多病的。最后拗不过阿婆的执着,阿爷被草草掩埋。以至于长辈只跟我提过大致的方向,具体地点却是一无所知的。
父亲基于对阿爷的愧疚和追思,每逢清明或者过年。都会让我拿上香火烛纸在天黑后找个路口,点燃纸烛,背过身给阿爷烧过去。
好些次我想回头看看,阿爷是否会在黑夜里出现。落寞的蹲在那里捡起这难得的供奉。想起这些,不由得热泪盈眶。却始终没有勇气回那个转身。在传说里,做了坏鬼的阿爷已经没有识别亲人的能力,你若回头,他会骑上你的肩背,跟着你一起回家。轻则大病,重则殒命。无论多少祖先都佑你不得!
阿婆说,这几日下大雨。你去看看我的老房子有没有被淋湿。木材腐烂后,我回老家后就要住在烂房子里了。
我扯了扯那块油纸布,一口漆黑的棺木安静的躺在那里。漏了雨的瓦片处似乎有意的避开棺木上方。没有一滴雨水落在棺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