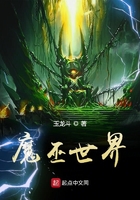永遇七年,八月流火,萧县已是整整三个月未曾下过雨了,炎炎烈日下遍地焦金流石,田地干涸龟裂出了歪七扭八的纵横沟壑。
张二麻子站在田埂间。
他戴着一顶斗笠帽,豆大的汗珠顺着脖颈流下,在灰汗交杂的深铜色的肌肤上冲刷出道道黑褐色的印痕。
粗布的对襟布衫已经破了好几个洞,补丁撂补丁,束进洗得看不出颜色了的大裆宽腿裤间。
裤腿挽到小腿处,正露出的结实小腿肚上有横七竖八的疤痕,耪地或是锄地都免不了被劈被砸的伤口。
脚上没穿鞋,常年光脚做活的脚底皮肤硬得令人心惊,厚厚的角质层一道道裂开。
张二麻子目及之处是张家的十几亩地,地里种的禾穗早已枯黄倒垂,羸弱的像在匍匐呻吟着,残余的黄色枝干已是极脆,人走过就能带起一阵细碎的粉尘。
从前村里的人都羡慕他家踩了狗屎运,田地就离村口大井几步路远,浇水是件极其省心省力的事情。
现在井水干涸得能见底部的黄山土不说,就连村旁的那条飞流疾驰的大河也在灼热的炙烤中日渐蒸发了,河滩上干渴而死的鱼都早就被捡光了。
张二麻子前些日子也带着小大子去捡鱼了,记忆中往日奔腾的水流那天连大鱼的脊背都没不过了,那今日呢?他不敢再往下想。
眼前的禾穗已能看出雏形,张二麻子心里绞痛不已,这是一家五口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他和张家的春天就商量好了,多少留下来作过冬的粮食,多少背到镇上去卖钱。
卖了钱,要给老母亲纳一双新鞋,她现在脚上的那双鞋底子都磨破了,前脚处的布也磨得稀稀疏疏的,隐约都能看见脚指头。
再给小大子扯半匹布做件新衣裳,换下来的旧衣补一补就能给小二子穿了,小二子长得可太快了,现在穿的衣服还是前年裁的,上衣紧紧绷在身子上,裤长只能将将盖到腿肚子,再不换一件大的,就怕哪一天给炸线绷开了。
而今这一切计划都成了泡影。
村里有老人说是神明降罪,也有人说是鬼怪作祟。开始也没人把这些当真,后来日子久了,族里和尚、道长、师太都各请了好几个,再后来不论什么名头,只要自称能求雨的,村里都盛情相邀了。
更有甚者,听说隔一座山头的刘家塘,趁没人的夜里祭了两个童男童女,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吓得张家的举着锄头,守着小大子和小二子一步不离,几宿几宿不敢睡觉。
也不知是作法的心不够诚,还是真是上天震怒要惩罚谁,怪力乱神的事情各村各寨都做了不少,雨愣是一滴也没下来。
“啪!”什么东西掉在了张二麻子右侧的肩头。
张二麻子只觉得大脑嗡的一声,耳朵里除了一阵刺耳的嗡鸣再也听不见别的声音。
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庄稼人,有时候直觉比什么探测工具都灵敏,他的本能当即为他带来了极为强烈的不详预感,心猛地一沉,咚的一声巨响在脑海中炸开,嗡鸣声越来越响。
张二麻子后知后觉地感知到喉咙干得快要冒烟,他伸出舌头,不安地舔了舔干裂的下嘴唇。
两个呼吸后,他自觉终于做足了心理准备,伸出左手将肩膀上的东西扫了下来,那是一只黄绿色的虫子,身约一寸长短,身上带着缕缕褐色斑纹,足胫节呈绛红色。
张二麻子腿弯一打颤,几乎要站不住了,他死死抓住手中插地的锄头,将全身的力量都压在一个支点上。
耳朵里的嗡鸣声渐渐消失了,整个世界的嘈杂一瞬间被拉回了意识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剧烈的嗡鸣,是真正震耳欲聋的巨响,响遏行云,穿云裂石。
伴随着震天的嗡鸣声,远处天地交接的边际线上,掀起了一股股黑压压的浪潮。
飞蝗来了。
黑色浪潮滚滚而来,张二麻子只觉蔽空如云翳日。
不知怎的竟有了须臾间的错觉,到底是太阳逐渐被遮了个完全,还是他骤然眼盲看不见日空了。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论田里是不是颗粒无收,秋季收税的日子确是到了。
“张二哥!张二哥!方才县丞带了好多人来,把你家小大子小二子抓走了!”远处传来隔壁王大张皇失措的呼喊。
王大跌跌撞撞闯进屋里的时候,张二麻子和张家的正和刘家塘的村长商量对策,如何除蝗,如何安置村民,如何将仅有的水分发到各家各户。
冷不丁听到王大的叫喊,张二麻子“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登时头脑发晕,辨不清四周的方向了。
后头只听“嘭”的一声,张家的饿了好几天早已是头晕眼花,猛然血气上涌一时压不住,直直栽倒在地。
刘家村长急忙跨上前一步扶住了张二麻子:“张二哥,你要挺住,我们这百户人家都要靠兄弟你了啊!”
张二麻子是这几片山头的里长,下头有一百户人家。
以前张老父还在世是远近一片有口皆碑的老里长,张老父去了以后,很多人对年纪轻轻的张二麻子接任里长很是不服气。
但张二麻子倒是不矜不伐,十里八乡有什么困难都乐意帮扶一把,进县城里和县丞、主簿交涉也是不畏不惧,渐渐赢得了乡民们的好感。
张二麻子回过神来,一边架起了张家的,一把抓住王大的领口,手握得紧紧的,骨节甚分明,几根青筋爆出:“王家老大,你说清楚,县丞为什么要抓小大子小二子?”
王大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地叙述了方才的情形,原来还是为了秋税的事情。
今年大旱后又遇蝗灾,赤地千里,天下大屈,很多乡民们都收拾细软逃难去了,有亲朋能投奔的早就拖家带口投奔去了,没有的也是能逃则逃了。
剩下一些家中有老孺的不便于长途跋涉,张二麻子把这些乡民都聚集起来,统一分配剩余的水,组织腿脚灵便的人去捕捉蝗虫回来充饥,暂且饿不死,但水真是喝了上次没下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