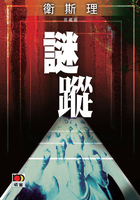将你自己局限于观察,你肯定会失去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目标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尽你所能去活得更好。生活就是场游戏,如果你投入进去,玩得尽兴,就能明白其中的规则。否则,你将无法保持平衡,不断地被变换的玩法所惊吓。非玩家们总是哀怨他们得不到运气的垂青。他们拒绝承认,其实他们自己可以创造运气。
——达尔维·欧德雷翟
“你看过艾达荷近期的摄像眼记录吗?”贝隆达问道。
“等一下!等一下!”欧德雷翟心中有些不快,她必须用这种方式来回应贝尔合理的询问,好让自己发泄一下。
这些天,压力将大圣母裹得越来越严。她一直让自己对必须面对的任务打起兴趣。任务越多,她的兴趣就越多,她的视野也就越广泛,因此也注定能产生更多有用的数据。感官用得越多就越灵敏。本质,这就是她的兴趣所追求的东西;本质,像是寻找食物来安抚空虚的胃。
不知从何时起,她的日子变成了今天早晨的重复。众所周知,她有接触他人的兴趣,但工作室的墙壁困住了她。她必须去那些别人能接近的地方。不光能接近,而且可以实时地与她交流。
该死!我会留出时间。我必须!
时间,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也能产生压力。
什阿娜说过:“我们走在借来的时间里。”
非常有诗意!但是,在实际的需求面前没什么作用。在斧子落下之前,她必须将尽可能多的贝尼·杰瑟里特细胞分散到各处。没有任何其他任务能排在它的前面。贝尼·杰瑟里特的织布正在被扯碎,送往圣殿居民无从知晓的目的地。有时,欧德雷翟将这种流动看成是碎布头。它们翩跹着在无舰里远去,带着一批沙鲑。一同带去的还有贝尼·杰瑟里特的传统、知识和记忆,它们可以用来辨别方向。但是,姐妹会早在第一次大离散就这么做过,没人回来,也没人发出过信息。没人。没人。只有尊母回来了。如果她们曾经是贝尼·杰瑟里特,那么现在她们已扭曲得可怕,自寻死路。
我们还能再次团聚吗?
欧德雷翟低头看着案头上的工作:更多的待选表格。谁要离去,谁要留下?没有时间停下来做个深呼吸。来自她前任塔拉扎的其他记忆摆出了一副“早就跟你说了”的姿态。“明白我当初都经历过什么了?”
我还曾经渴望过顶层的位置呢。
顶层可能有位置(她乐于这么跟侍祭们说),但是,不怎么有时间。
有时,想到“外面”那些被动的、非贝尼·杰瑟里特的普通人时,欧德雷翟会嫉妒他们。他们可以生活在幻想里。多么欣慰。你可以假装你的生活会无限地持续下去,明天会变得更好,天上的神们都在给你关照。
她以对自己的鄙视结束了这次走神。未被遮蔽的眼睛更好,不管它看到了什么。
“我研究了艾达荷最新的记录。”她说道,看着桌子对面耐心的贝隆达。
“他具备有趣的本能。”贝隆达说道。
欧德雷翟琢磨了一阵。无舰上遍布摄像眼,几乎没有死角。委员会关于死灵艾达荷的理论正一天天地变成现实。这个死灵到底掌握了艾达荷系列生命中多少的记忆?
“塔玛对他们的孩子有疑虑,”贝隆达说道,“他们有什么危险的天赋吗?”
这是意料之中的。默贝拉在无舰中为艾达荷生的三个孩子在刚出生时就被带走了。他们的成长都处于密切的观察之下。他们具备了尊母展现的那种可怕的反应速度吗?现在还太早,无法下结论。据默贝拉所言,这是在青春期才会表现出的能力。
他们的尊母俘虏在愤怒的顺从中接受了孩子被带走。然而,艾达荷显得无动于衷。奇怪。难道有什么东西给了他更宽广的生殖观?几乎和贝尼·杰瑟里特的观念一样?
“另一项贝尼·杰瑟里特的生殖计划。”他讥笑道。
欧德雷翟延展着自己的思路。她们在艾达荷身上看到的真的是贝尼·杰瑟里特的态度吗?姐妹会说情感牵挂是古代的遗物——对于人类在那个时期的生存至关重要,但在贝尼·杰瑟里特的计划里无关紧要。
本能。
从卵子和精子里带来的东西。通常响亮而又关键:“这是整个物种在对你说话,笨蛋。”
爱……后代……饥饿……所有这些潜意识下的动机触发了特定的行为。胡搞这些东西是危险的。交配圣母在这么做的时候清楚这一点。委员会会定期对此进行检讨,并下令对后果予以密切关注。
“你研究了记录。这就是你的全部答案?”对贝隆达来说,这已经接近于哀怨了。
在贝尔感兴趣的摄像眼记录中,艾达荷向默贝拉询问了尊母的性瘾技术。为什么?他与之媲美的能力来自伊纳什洛罐往他细胞中加入的特莱拉特性。艾达荷的能力与潜意识模式同源,类似于本能,然而在效果上与尊母的无法区分:不断放大兴奋,直到它驱逐了所有的理智,将它的受害者困在回馈的源头。
默贝拉只是口头表达了她的能力。她显然仍余怒未消,因为艾达荷在她身上使用了她学过的相同的技术。
“当艾达荷问到动机时,默贝拉拒绝回答。”贝隆达说道。
是的,我注意到了。
“我能杀了你,你知道吧!”默贝拉说。
摄像眼记录显示了他们躺在无舰内默贝拉舱房里的床上,刚刚结束了互相满足。裸露的肉体上有点点汗珠。默贝拉的前额盖着块蓝色的毛巾,绿色的双眼盯着摄像眼。她似乎是在直接盯着观察者。她的眼里有橙色的斑点。那是愤怒的斑点,来自她体内残余的、尊母服用的香料替代品。她现在服用的是美琅脂——而且没有副作用。
艾达荷躺在她身边,黑发散落在脸旁,与他脑袋下的白色枕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双眼紧闭,但是眼睑在颤动。消瘦。尽管欧德雷翟的私人厨师亲自为他准备了可口的餐食,他吃得还是不够。他高耸的颧骨轮廓清晰得夸张。在被困了这么多年后,他的脸已是皮包着骨头。
默贝拉的身体能力足够支持她发出威胁,欧德雷翟知道,但在心理上说不通。杀了她的爱人?不太可能!
贝隆达也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她展现自己身体的速度时,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以前看到过这种现象。”
“她知道我们在观察。”
摄像眼显示了默贝拉的身体挑衅式地从床上跃起,以一种看不清的速度(比贝尼·杰瑟里特能达到的速度快多了)踢出了右脚,在离艾达荷头部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时才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她一开始动作,艾达荷就睁开了眼睛。他看着她,没有恐惧,也没有眨眼。
那一脚,如果踢中了就是致命的!这种事情,你只须看一次就足以让你心生恐惧了。默贝拉动作时并不需要大脑皮层。就像是昆虫,肌肉里的神经自主触发了攻击。
“看到啦!”默贝拉放下了脚,低头盯着他。
艾达荷笑了。
看着记录,欧德雷翟想起了姐妹会掌握了默贝拉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孩。交配圣母都很激动。一段时间之后,这条线上出生的圣母也会拥有尊母的能力。
恐怕我们没有时间。
但是,欧德雷翟还是分享了交配圣母的激动。那个速度!再加上肌肉神经训练,姐妹会伟大的普拉纳—宾度资源!对这样的创造物,她难以找到语言来形容。
“她是做给我们看的,而不是给他。”贝隆达说道。
欧德雷翟不是很确定。默贝拉厌恶一直处于被人观察之下,但她已经习惯了。她的很多行为显然已经无视了摄像眼背后的人。在这条记录上,她又回到了床上原来的位置,躺在艾达荷的身边。
“我已经给这条记录的读取加上了限制,”贝隆达说道,“有些侍祭看了觉得不舒服。”
欧德雷翟点了点头。性瘾。尊母这个方面的能力在贝尼·杰瑟里特内部搅起了波澜,尤其在祭侍中间。非常有挑唆性。而且,大多数圣殿的姐妹都知道什阿娜圣母是她们中唯一练习过这些技巧的人,而她练习的目的是挑战一个普遍的误解,即性瘾会弱化姐妹的能力。
“我们不能变成尊母!”贝尔总是这么说。但是,什阿娜代表了重要的变量。她教会了我们关于默贝拉的一些东西。
某天下午,看到默贝拉独自在她无舰上的舱房内待着,一副放松的样子,欧德雷翟尝试了直接的询问:“在遇到艾达荷之前,你们中有人试过,怎么说呢,‘投入进去’吗?”
默贝拉又回到了愤怒的神态:“他是趁我不备!”
她对艾达荷的问题展示过同样的愤怒。想到这里,欧德雷翟朝工作台俯过身去,调出了原始记录。
“看她变得有多愤怒,”贝隆达说道,“这是针对这种问题的催眠植入。我敢以我的名誉担保。”
“香料之痛能解除这种催眠。”欧德雷翟说道。
“如果她能进入这种状态!”
“催眠术本该是属于我们的秘密。”
贝隆达琢磨着话中的引申:在最初的离散中,派出去的姐妹一个都没回来。
这想法在她们的意识里始终挥之不去:真的是贝尼·杰瑟里特的叛徒创造了尊母?很多线索证明了这种观念。那她们为什么要培养男性奴隶?默贝拉的闲扯并没有揭示真相。所有的这些都与贝尼·杰瑟里特的教育相悖。
“我们必须了解清楚,”贝隆达坚持道,“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让人不安。”
欧德雷翟认同她的担忧。这种能力到底有多大的诱惑力?非常大,她觉得。侍祭们抱怨说梦到自己变成了尊母。贝隆达的担忧是合理的。
你一旦创造或触发如此野性的力量,就能建立异常复杂的肉欲幻境。你能控制整个人类,只须通过支配他们的欲望,触发他们的幻想。
尊母竟敢使用如此可怕的力量。显然,如果她们掌握了关闭幻境的钥匙,她们就赢得了一半的战争。要是能找到简单的线索,指向钥匙的存在,那就是胜利的开始。尊母组织中像默贝拉这个级别的人可能不清楚,但是那些在高层的人……可能她们只是运用了这种力量,却不关心甚至不了解它深层的能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最初那些离散的姐妹究竟受到了什么诱惑,走上了这条死路?
之前,贝隆达曾提出过她的猜测:
在首次大离散时期,尊母抓住了圣母并把她们关押起来。“欢迎,圣母。我们邀请你们欣赏一下我们能力的小小展示会。”一幕幕的交媾场面,接着又展示了尊母身体的速度。然后——停止服用美琅脂,注射基于肾上腺素的替代品,里面还掺杂了催眠药物。在药物的作用下,圣母被打上了性印记。
这一切,加上香料之痛的退却(贝尔暗示的),可能会让受害者拒绝原本的身份。
天啊!最初的尊母难道都是圣母?我们敢在自己身上检验一下这个猜测吗?我们又能从无舰里的那一对身上学到些什么?
两种来源的信息摊在了姐妹会敏锐的眼睛前,但钥匙还没找到。
女人和男人不再仅是繁殖上的伙伴,也不再仅是互相的慰藉和依靠。关系里加了点新东西。关系又被提升了。
在工作台上播放着的摄像眼记录里,默贝拉说了些什么,吸引了大圣母的全部注意力。
“我们尊母自找的!怪不了其他人。”
“你听到了?”贝隆达问道。
欧德雷翟猛力地摇了摇头,想要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在这段对话上。
“我跟你不一样。”艾达荷反对道。
“空洞的借口,”默贝拉指责道,“你想说你是被特莱拉人设置了,去诱惑你碰到的第一个铭者?”
“并杀了她,”艾达荷补充道,“那是他们的期望。”
“但是,你甚至都没试过要杀我。我并不是说你能杀得了我。”
“那是因为……”艾达荷没接着往下说。他下意识地朝摄像眼瞥了一眼。
“他想说什么?”贝隆达跳了起来,“我们必须搞清楚。”
欧德雷翟继续默默地观察着这对囚徒。默贝拉表现出了惊人的洞察力:“你觉得你是在跟你无关的场合下碰巧撞上我了?”
“是的。”
“但是,我看到你体内有东西接受了这一切!你不仅是在设置下逆来顺受,你把它展现到了极致。”
艾达荷的眼睛仿佛在审视自己。他仰起头,舒展了胸肌。
“那是门泰特的表情!”贝隆达叫道。
欧德雷翟所有的分析都指向这个结论,但仍未得到艾达荷的承认。如果他是个门泰特,为什么要隐瞒呢?
因为这个能力喻示的其他东西。他害怕我们,而且,他的确该害怕。
默贝拉轻蔑地说道:“你按照自己的需求,改善了特莱拉人在你身上做的事情。你内心其实并没有任何怨恨!”
“那就是她处理负罪感的方式,”贝隆达说道,“她必须让自己相信自己说的,否则艾达荷没办法困住她。”
欧德雷翟抿紧了嘴唇。投影中的艾达荷笑了:“或许我们两个都一样。”
“你不能怪罪特莱拉人,我不能怪罪尊母。”
塔玛拉尼走进了工作室,坐在了贝隆达身旁的犬椅中。“看来,你也对这段感兴趣。”她示意了一下投影。
欧德雷翟关上了投影。
“我一直在检查我们的伊纳什洛罐,”塔玛拉尼说道,“那个该死的斯凯特尔隐瞒了关键信息。”
“我们的第一个死灵没问题吧,是吗?”贝隆达问道。
“我们的苏克没发现什么问题。”
欧德雷翟语气柔和地说道:“斯凯特尔必须留下些讨价还价的余地。”
双方都抱有幻想:贝尼·杰瑟里特将斯凯特尔从尊母手下救出,并收留在圣殿避难,而他则向姐妹会支付一定的代价。但是,每个研究他的圣母都知道,这位最后的特莱拉尊主还有别的企图。
聪明,聪明,特莱拉人。比我们怀疑的更聪明。他们用伊纳什洛罐玷污了我们。“罐”这个字——又是他们的一个欺骗。我们想象它是羊膜般的容器,里面装着温暖的液体,每个罐子都是复杂机器,用以复制(以精确、步骤清晰和可控的方式)子宫的功能。罐子倒是罐子的样子,可看看它实际上是什么!
特莱拉的方案很直接:使用原生器官。经过无数的世代,大自然已经做出了优化。贝尼·特莱拉所做的只是加上了他们的控制系统,他们独有的复现细胞内所存信息的方式。
斯凯特尔称之为“上帝的语言”。更准确地说,是撒旦的语言。
反馈。细胞指导着自己的子宫。受精卵或多或少可能都会这么做。特莱拉人只是优化了它。
欧德雷翟发出了一声叹息,引得她的同伴投来了锐利的目光。大圣母遇到了什么新麻烦?
斯凯特尔的秘密让我担忧。那些秘密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唉,我们怎么这么容易就“降格”了呢?然后,再找借口。而我们知道是借口!“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这能制造我们急需的死灵。或许可以找到志愿者。”找到了!志愿者!
“你走神了!”塔玛拉尼不满地哼了一声。她瞥了眼贝隆达,开始对她说话,觉得她可能会听进去。
贝隆达的表情变得有些麻木,通常这意味着她情绪低落。她的声音比耳语响不了多少:“我强烈要求抹消艾达荷。至于那位特莱拉的怪物……”
“你为什么建议得这么委婉呢?”塔玛拉尼问道。
“那就杀了他!还要让那个特莱拉人尝尝我们所有的——”
“住嘴,你们两个!”欧德雷翟命令道。
她用两个手掌扶住了前额,盯着拱形窗,看到了外面的冰雨。气象人犯下了更多的错误。你不能责怪她们,但是,人类最恨的就是不可预测。“我们要自然!”不管它是什么意思。
想到这里时,她开始渴望回到那个让她愉悦的秩序里去:偶尔在果园中的散步。她喜爱各个季节下的果园。与朋友们一起度过安静的傍晚,和那些让她温暖的人进行有来有往的交谈。温情?是的。大圣母敢于尝试——甚至对同伴的爱。她也想要美味的食物与能增加风味的精选美酒。它们对味觉的刺激真是绝妙。然后……是的,然后……温暖的床,温柔的同伴,他懂得她的需要,她也懂得他的。
当然,多数的这些都无法实现。责任!多么重要的一个词!它在熠熠发光。
“我饿了,”欧德雷翟说道,“要不然叫人把午饭送来吧?”
贝隆达和塔玛拉尼盯着她。“才刚十一点半。”塔玛拉尼表示。
“好还是不好?”欧德雷翟坚持着。
贝隆达和塔玛拉尼偷偷交换了下眼神。“好吧。”贝隆达说道。
贝尼·杰瑟里特有一种说法(欧德雷翟知道),大圣母的胃满意了,姐妹会能运作得更流畅。这句话让天平发生了倾斜。
欧德雷翟接通了她私人厨房的通话器:“三个人的午餐,杜纳。来点特别的,你决定吧。”
午饭端来了,主菜是欧德雷翟的最爱,小牛肉砂锅。杜纳对香草的感觉很灵敏,砂锅里放了少许迷迭香,蔬菜也没有煮过头。完美。
欧德雷翟回味着每一口。另两个人只是在进食,一口一勺,一口一勺。
这就是我成了大圣母,而她们当不上的原因?
等侍祭打扫完餐桌后,欧德雷翟问了一个她最爱的问题:“最近在侍祭中有什么闲话吗?”
她想起了自己曾经是侍祭的日子,成天竖着耳朵倾听老妇们的谈话,希望能听到什么伟大的真理,但多数情况下听到的只是些有关姐妹们的闲话,或是某个监理又出了什么问题。不过,偶尔她们也会放下戒备,泄露些重要的信息。
“太多的侍祭都在说想要参与大离散。”塔玛拉尼粗着嗓子说道。
“最近她们对档案的兴趣也增加了许多,”贝隆达说道,“那些心有所感的姐妹都来寻求确认——自己是否携带了很深的赛欧娜基因印记。”
欧德雷翟觉得这挺有趣。她们那共同的、生活在暴君时代的厄崔迪祖先,赛欧娜·伊本·福阿德·赛伊法·厄崔迪,将这种能躲避预知搜索者的能力遗传给了后代。每个公开行走在圣殿的人都分享了这种来自祖先的保护。
“明显的印记?”欧德雷翟问道,“她们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受到了保护?”
“她们需要确认,”贝隆达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声,“现在能回到艾达荷的话题上吗?他可以说有基因印记,也可以说没有。这让我觉得不安。为什么他的部分细胞没有赛欧娜的印记?特莱拉人到底干了什么?”
“邓肯知道风险,他也没想自寻死路。”欧德雷翟说道。
“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贝隆达抗议道。
“可能是个门泰特,我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塔玛拉尼说道。
“我能理解我们为什么留着默贝拉,”贝隆达说道,“宝贵的信息。但是,艾达荷和斯凯特尔……”
“够了!”欧德雷翟喝止道,“看门狗不要一直叫个不停!”
贝隆达勉强接受了。看门狗。贝尼·杰瑟里特的一种说法,意为不断监视姐妹、判断你是否陷入了歧途。侍祭们觉得这难以忍受,然而对圣母来说,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某个下午,和默贝拉单独待在无舰上灰色墙面的面谈室内时,欧德雷翟解释过。她们面对面站着,隔得很近。眼睛相互平视。十分随意、亲密。前提是假装看不到四周的那些摄像眼。
“看门狗,”欧德雷翟回答着默贝拉提出的一个问题,“意味着我们互为牛虻。没必要做太多解释。我们很少说废话。一个简单的词就够了。”
默贝拉椭圆形的脸上露出了专注的表情,分得很开的绿色双眼炯炯有神。她显然认为欧德雷翟提到了某种常见的信号,用一个词或是一种说法来描绘眼下的这种情况。
“什么词?”
“任何词,该死!只要合适就行。它就像是某种相互作用。我们分享一个不会烦扰我们的‘叮咬’。我们欢迎它,因为它让我们保持清醒。”
“如果我成了圣母,你也会当我的看门狗?”
“我们需要自己的看门狗。没有她们,我们会变得虚弱。”
“听上去有点强迫的意味。”
“我们并不觉得。”
“我觉得它是防蚊剂,”她看着天花板上闪烁的镜头,“像这些该死的摄像眼。”
“我们照顾自己人,默贝拉。一旦你成了贝尼·杰瑟里特,你会得到一生的照顾。”
“舒适的小窝。”不屑。
欧德雷翟语气柔和:“完全相反。你的一生都在接受挑战。你用能力的极限来回报姐妹会。”
“看门狗!”
“我们总是在相互关注。我们中的有些人在执掌权柄之后可能会时不时地表现得独裁,甚至专横,但都是在形势的要求下点到为止。”
“从来不会热情或温柔,嗯?”
“这是规矩。”
“或许有感情,但是没有爱?”
“我跟你说了规矩。”欧德雷翟能从默贝拉的脸上清楚地看出她的反应。“终于说漏了!她们会要求我放弃邓肯!”
“也就是说贝尼·杰瑟里特中没有爱。”她的语气是多么悲伤。默贝拉仍有希望。
“爱也会发生,”欧德雷翟说道,“但我的姐妹们把它当作心理偏差。”
“我对邓肯的感觉是心理偏差?”
“姐妹们会尝试治疗它。”
“治疗!治疗是用来解除痛苦的!”
“姐妹会认为爱就是一种腐烂。”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腐烂!”
贝隆达仿佛一直在跟着欧德雷翟的思绪,此刻她将欧德雷翟从空想中拽了出来。“那个尊母绝不会加入我们!”贝隆达抹去了嘴角的一点午餐残渍。“教授她我们的方法,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至少,贝尔不再称呼默贝拉为“妓女”了,欧德雷翟想着。这就是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