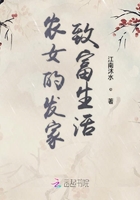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
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逝世于香港。
一
林语堂和鲁迅都是文豪,他们在同一个时代放射各自的光芒,以自己的方式行走在那段岁月。他们曾经相得,也曾经相离。1936年鲁迅逝世后,林语堂在美国纽约写的悼念文章《鲁迅之死》,其中这样刻画他和鲁迅的相交:“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言语中,对鲁迅的敬意在字里行间一一闪现。
1923年,林语堂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林语堂留学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是他和鲁迅相识的开始。
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尽管当年胡适对林语堂关照颇多,在林语堂留学海外经济窘困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用私人钱以学校的名义资助林语堂,却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直到林语堂回国后才知道事情的具体真相。这是很深的个人情谊,但没有影响到林语堂的选择,林语堂站到鲁迅旗下,和鲁迅成为盟友。
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两天,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的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信和约稿,然后是林语堂复信和交稿,这是两人“相得”的开始。后来,林语堂和鲁迅并肩战斗,写了许多文章,大谈政治。他还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这段经历让林语堂在年老的时候还时常得意地和女儿提起,成为过往岁月闪耀的亮点。
1926年,林语堂和鲁迅都上了当时军阀政府的黑名单。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然后他邀请鲁迅到厦大任教,这段四个月的相处,让他们的友谊加深了。
在厦门大学,林语堂极力想照顾鲁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屡屡提及林语堂的这种努力,包括林语堂夫人廖翠凤对鲁迅生活的照顾。当鲁迅在厦门大学不如意萌生去意的时候,鲁迅担心的也是对林语堂的影响,他们不仅仅是惺惺相惜,而是风雨同程。
当鲁迅离开厦门去广州然后到上海,而林语堂也离开厦门去武汉最后也到了上海,这两个曾经有过密切友谊的人又在一起,但相聚并没有太多友谊的加深,恰恰是他们之间裂痕的开始。
二
在上海,林语堂和鲁迅都以文为生,不过走的却是不同的路子。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他认为:“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
这是不同的选择,不一定是背道而驰,但分道扬镳是肯定的事情。愈走愈远,既是无奈也是现实。
仔细观察鲁迅和林语堂等几个人在厦门后山上的那张合影,都是在爬山,林语堂是西装革履文明棍,而鲁迅则是长袍布鞋。也许这仅仅是生活细节,但细节有时候折射的是一种走向,林语堂和鲁迅的差异可见一斑。他们为文的风格和人生道路的不同从这样的细节也可以看出端倪。毕竟,林语堂是出生在乡村牧师的家庭,他从平和坂仔这偏僻乡村走向厦门、走向上海、走向外国留学,然后回国到北京,到厦门,到上海,生活有不顺心甚至有危险,但总体是向上发展的。在他的内心,欢乐多于忧愁,他坚持的是“人生要快乐”。而鲁迅出生在没落的地方望族,家道的衰败使鲁迅过早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与世态炎凉。这深刻影响到他性格的形成,他秉持的是“一生都不宽恕”。
文学立场的不同,让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友谊也磕磕碰碰。开始,他们围绕“痛打落水狗”等有了论争,尤其是林语堂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而鲁迅却认为在生死斗争之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鲁迅认为,对林语堂“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而林语堂则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字里行间的锋芒颇有江湖间的刀光剑影。
不过,“南云楼风波”是他们之间的正面冲突,使他们从文字走到现实的争执。
在鲁迅的日记里,对此曾有记叙:“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而四十年后林语堂在《忆鲁迅》也回忆此事:“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此的风波是过去了,但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裂痕却无法消除。尽管他们后来有次和解,但这样的和解并没有坚持多久,决裂却是紧随而来。鲁迅还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认为林语堂是在暗讽他已经老了。这也许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也许平常人不以为意的一句寻常话,在心有芥蒂之人的心目中却能滋生出许多遐想。
从1934年起,左翼作家群体增强了对林语堂的批评,主要是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斥责幽默刊物为“麻醉文学”。从这以后,两人再无来往,林语堂的名字,也从鲁迅日记里完全消失了。这两个曾经是盟友的人,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这样的方向不仅仅是各走各的阳关道,而且颇有对阵江湖的架势。
三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总体的美学特征是沉重而悲怆的。这当然和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有关。只要想一想20世纪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是多么艰难曲折、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奋争和磨难,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严肃的思想面貌和浓重的悲剧色彩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因此,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对林语堂以提倡幽默掩盖社会矛盾,“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的批评就更容易让人理解了。
鲁迅公开申明过:“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他还说过:“‘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针对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以幽默小品为统治者“帮闲”的倾向,鲁迅曾在一封信中说:“专读《论语》或《人间世》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也。”
这些看起来像是否定和排斥幽默的痛乎言之的话,连同当时中国“炸弹满空,河水漫野”的现状一起,在一代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撼。无怪乎当时的青年作家吴组缃在接到日本人增田涉[34]因为编选《中国幽默文学选》而征求意见的信时,觉得很不以为然,作出了偏激而失礼的反应。
在近半个世纪后,吴组缃在北大的课堂上曾对这件往事有过回顾和反思,坦然承认自己当年一律抹杀幽默是片面的,没有准确理解鲁迅关于幽默的全部看法。他还在文章里公开作自我批评,指出:“其实幽默与讽刺,往往很难区分;我对鲁迅那个警句的理解也不免简单化,随着岁月和阅历的增长,我知道看事不能从概念出发:幽默也有不同的内容,讽刺也有不同的观点,情况变化无定,笼统地看是不对的。”
到底鲁迅对幽默的全面的看法是什么呢?
早在1924年5、6月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撰文《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第一次将英语的humour译成“幽默”并加以提倡。humour一词的含义是令人觉得有趣或可笑且又意味深长的言谈或举动。原来有人译为“酉靺”。林语堂在文章中指出:“素来中国人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不胫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体。”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或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无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枯燥无聊。”
在这里,林语堂是把幽默作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或文章中欠缺的一种美学要素来提倡的,这是颇有积极意义的,很快就得到了鲁迅的呼应。《论幽默》一文中有些观点,是被鲁迅接受并予以发挥的。其中主要观点有二:
第一,幽默应与人类的同情心相联系。日本学者鹤见祐辅[35]曾提出,“使幽默不堕于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在纯真的同情罢……幽默不怕多,只怕同情少。以人生为儿戏,笑着过日子的,是冷嘲。深味着人生的尊贵,不失却深的人类爱的心情,而笑着的,是幽默罢。”
鲁迅对这一见解是肯定的。1933年10月,他指出:“……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即为此。”鲁迅早就有“无情的冷嘲与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之说,“有情的讽刺”,其实即是幽默倾向于揭示社会实际情状中的可笑与荒谬的产物。这正是鲁迅希望幽默发展所趋的正路,而有别于林语堂关于“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的主张的。
第二,幽默的运用要有一个严格的度。鹤见祐辅提出,“幽默是如文,如水,用得适当,可以使人生丰饶,使世界幸福,但倘一过度,便要焚屋,灭身,妨害社会的前进的。”鲁迅对这一见解实际上也是接受的。他不反对幽默在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但反对幽默的泛滥。
他在《“滑稽”例解》中写道:“慨自语堂大师振兴‘幽默’以来,这名词是很通行了,但一普遍,也就伏着危机,正如军人自称佛子,高官忽挂念珠,而佛法就要涅槃一样。倘若油滑、轻薄,猥亵,都蒙‘幽默’之号,则恰如‘新戏’之入‘×世界’,必已成为‘文明戏’也无疑。”这就是说,幽默一旦泛滥逾度,势必变质为庸俗无聊。从幽默的度,鲁迅进一步阐发了讽刺艺术的度的重要性。他一则指出:“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36]
二则指出:“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讽刺文学是不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对幽默的理论主张并无反感,反而颇多同情。他不但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友人林语堂同声相应,而且通过翻译鹤见祐辅的《说“幽默”》,学习、研究了幽默作为文学的美学要素所具有的某些关于其自身生存的根本特征,如幽默的根柢在同情,幽默的运用有其度等等,并颇多发挥。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并主编的《论语》出版。林语堂和其他一些作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提倡、阐释“幽默”的文章,逐渐推衍为一股幽默文学思潮,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产生不小的影响。鲁迅的幽默观,便在30年代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有了新的发展变化,从一开始的与林语堂倡导的幽默文学思潮有某些契合之点,发展到与之渐成对峙,最后竟至完全仳离。这个时期,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幽默存在和流行的前提。
林语堂认为幽默之风,存乎一心,欲求幽默,诉诸心境。他说:“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的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但鲁迅却认为幽默存在和风行的前提是社会环境。
鲁迅认为,中国没有幽默的传统,中国过去流传较多的是历史上文人的笑话轶事,还有像金圣叹临死时说的那种以自我解嘲的方式来掩盖刽子手凶残的话语,而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更何况,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使人们无意去讲什么幽默。针对有人攻击鲁迅坐着有版税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闻其骚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鲁迅反击说:“有版税的尚且如此,还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么?恐怕连‘骚音怨音’也不会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谈不到。”
鲁迅从社会环境去分析幽默之存亡的见解,体现了他一贯的直面现实的战斗精神,从根本上触及了林语堂的幽默论的玄虚之处。求幽默于心境,而欲求心境的平和冲淡,便只好闭目塞听,从哀鸿遍野、饿殍陈路的悲惨现实中逃出,“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来”。在鲁迅看来,这样的闲话幽默,只能成为替反动统治者“帮闲”的一种手段。
第二,关于幽默的泛滥的结果。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化界由于《论语》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的杂志,如《谈风》《中庸》《聊斋》等,当时的情形真成了“东也是幽默,西也是幽默,大有风行之概”。文坛上刮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林氏“幽默风”,鲁迅在杂文集《花边文学·一思而行》中说,“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漫骂。油腔滑调,幽默也;‘天朗气清’,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结果只能是,“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幽默这个名目,自也难逃此厄运。
第三,关于幽默与讽刺的联系、界限与转化。
林语堂虽然承认幽默与讽刺在审美功用上有联系,却严幽默与讽刺之辨,竭力排除讽刺于幽默之外,不愿看到幽默向讽刺转化。他说:“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后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又说:“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在林语堂看来,虽然幽默可能具有讽刺社会和人生的作用,但为葆其纯粹,却不能以讽刺为目的,即万万不能倾向于讽刺;而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则只有避开切实具体的讽刺对象,趋于空泛笼统,使其情调深远,才有望近于幽默。总之,林语堂既不乐意看到幽默倾向于讽刺,又希望讽刺空泛化并复归于幽默。其对讽刺的憎嫌之态,跃然纸上。
而鲁迅与林语堂的看法正相反,他是乐于见到幽默倾向于讽刺的。在鲁迅看来,幽默通常是对可笑事物某种特点的诙谐的揭示,往往含有讽刺的成分。在难以幽默的社会环境中,幽默不可能有恒定的形态,一定会发生变迁、分化。“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歧看,鲁迅反对林语堂的幽默观,是切中要害的。他的声音一出,林氏幽默风顿时减色失势,幽默泛滥的局面也很快得到澄清。一时间批评和反对幽默又成潮流。
不过,当时鲁迅虽反对幽默的泛滥,但并不反对作为美学风格的幽默本身,而且,他对借骂幽默以名世的做法和简单化倾向,也非常反感。他说:“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又无不骂幽默和小品。其实,则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他还幽默地写道:“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竟好像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人。”
弄清楚了鲁迅对于幽默问题的全面而具体的见解之后,对于他在30年代帮助日本增田涉选编《世界幽默全集》中的中国部分一事,就很好理解了。从这件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中,很可以见出鲁迅幽默见解的宽阔和精当。
总之,鲁迅心目中的幽默作家或幽默作品,大抵是含了讽刺的锋芒和滑稽的风格,能聊博一笑,但又“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幽默作品所引发的笑,不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也正因为这样,鲁迅所推崇的幽默作品,在艺术上要求是较高的。他对增田涉说:“迄今为日本所介绍的中国文章,大抵是较轻松易懂的东西;坚实而有趣的作品,如陶潜的《闲情赋》之类,一点也没有译。”这里,鲁迅对幽默作品提出了“坚实而有趣”的要求,这也可以视为对幽默文学作品中的精品的一个具体而适当的要求吧。
四
1936年,林语堂到美国从事写作,就在这一年,鲁迅因肺结核去世。四天后,林语堂写下了名为《鲁迅之死》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鲁迅逝世使二人阴阳相隔,但是他们论争的影响并没有就此消失。林语堂在美国写的这篇文章中盛赞鲁迅的伟大。林语堂有旧文人浪漫优雅的一面,对社会底层人民有同情心。与此相比,鲁迅始终关注现实,对社会底层人民有更直接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对所谓上层社会是持批判态度的。林语堂把鲁迅比做战士,对鲁迅私心终以长辈事之,通篇对鲁迅持肯定态度,不过,文中也有不少刻薄而有趣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