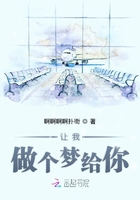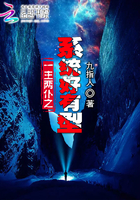张堂文默默地搓着手,看着一脸肃穆的杨鹤汀。
这样的话,先前在杨鹤汀的住处,也聆听过多次了。但那时的张堂文,只有亢奋和崇敬,而如今,他的心底却滋生出了一声胆怯。
他在怕什么?
哪怕是身在水牢中,他都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冰冷的胆怯。
他到底在怕什么?
杨鹤汀靠在教桌边上,静静地看向张堂文,先前发生的那么多事,让他完全相信眼前的张堂文,不仅仅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普通西商。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从京师法政学堂开始,总有人会走入杨鹤汀所在的这条道路,有人一路相随,也有人半途掉队,要想成就藏在他心中的大志,达成藏在千千万与他一样的同盟会成员心中的理想,非热血和恒愿不能铸就!
所以,在杨鹤汀的心中,虽然会争取每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也不会惋惜任何一个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
但他的直觉告诉自己,眼前这个张堂文,并不是贪生怕死畏首畏尾,也不是坐井观天不知不问,他的困惑,必然来自于千百年来中华传统思想的束缚,他还没有达到破除这个礼法的真正境界:无私和奉献。
杨鹤汀缓缓站直身子,轻声说道:“堂文兄,鹤汀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唔?”张堂文抬起头,“杨先生但讲无妨!”
“方才在操场,春福见到你的一刹那,眼神中的变化,想必堂文兄心中也明白!”
“唔?”
“那是一种惶恐,一种担忧,那不该是一个孩子看到自己父亲的表现!”
“唔!”
“人,不该是这样啊!堂文兄!”
张堂文心头一颤,这熟悉的话语,像一记鸣锣敲响在张堂文的耳边,这话,他也曾经说过。
“一辈子诚惶诚恐,一辈子按照父辈的规划走完碌碌无为的一生,或许,这一生不愁锦衣玉食,或许这一生无忧无虑,但,这就是人生来的意义么?那些投胎在穷苦人家的,生就应该备受欺压,一生颠沛流离么?”
杨鹤汀抬头看了看屋顶,按捺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如今,外敌欺凌,内忧不断,清廷除了一味求和,割地赔款,又做了些什么?加赋,征丁!我公学一期认缴粮米不过三五斗,可又有多少人家肚子都吃不饱?何谈求学?穷苦人家不得入学堂,目不识丁沦为流民,不是上山作匪,便是沦为畜力,如果我们这些饱学之士不能为民族为国家做点什么,我们耻为国人,羞对国家,千百年后国将不国,人皆为奴为寇的时候,九泉之下,我们有何面目见先人后辈?”
张堂文一刹那间,便想起了夏老三,我送他的那把左轮手枪,会给他指向何处呢?
“堂文兄!”杨鹤汀满面激昂地看向张堂文,“清廷就像一株从根部腐朽的苍天大树,表面看上去风平浪静,实则不堪一击,一旦我中华觉醒之势并起,它必将摧枯拉朽一般席卷江河!想一想那一天,再看看今日堂文兄尚不敢明谈的心中顾虑,堂文兄,春福会作何感想?你又会作何感想?”
张堂文的眉头渐渐皱在了一起,他的心在犹豫。
杨鹤汀描绘的美好画面,张堂文也希冀已久,但这条路,必然不会似杨鹤汀口中那般风雨不惊。遍观二十四史,变革之路无不血雨腥风,生灵涂炭。
若是不牵连其他,张堂文宁可自己孤身投入,但,他毕竟是一家之主,是百十号人的老爷,是两个幼子的父亲。
杨鹤汀从张堂文紧皱的眉头中看出了端倪,他缓缓坐在张堂文对面的椅子上,轻声说道:“鹤汀,家道中落,早已以身许国,堂文兄肩负张家宏业,心之顾虑,人皆体谅,便是春福,鹤汀也可保证,仅以毕生所学指点迷津,不涉党事!”
“杨先生!”张堂文缓缓地抬起头,看着杨鹤汀的双眼,“是在下偏私了!”张堂文庄重地抬起手,深深地躬下了身子,“可叹思源堂堂七尺之躯,不与报国,却困于私情,今日在壮士面前,做了小人了,还请杨先生见谅!”
“堂文兄哪里话!这....”
“杨先生!”张堂文摆了摆手,“春福虽是年少,却也是我张家儿郎,若我依旧如来时念想,把控其言行,约束其未来,就像杨先生前头所说,思源亦无颜见九泉之下的先人了!”
张堂文深吸了一口气,坚定地说道:“春福能跟随杨先生,修身向学,是张家百年积下的福分,无论日后作何发展,都是他秉从内心的选择,我这个做父亲的,不该横加阻拦,以一己之私落一世遗憾!杨先生请放手教导,何去何从,听凭春福自己决断吧!”
杨鹤汀赞许地看着张堂文,庄重地还了一礼,两人相视无言。
推开房门,却见门外不远处,罗飞声与张春福正在低声攀谈着什么,张春福见父亲出来了,连忙快步上前侍奉着。
张堂文满眼怜爱地看着张春福,伸手按在张春福的肩膀上,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紧紧地捏了捏张春福的肩头,仿佛下了重重地决心一般,扭头便向校外走去。
“父亲!”张春福连声唤着,便要上前。
张堂文猛然回身,眼眶却已是湿润了,“福儿!放手向学,秉从内心!杨先生和罗先生是不世英才,你好生侍奉,尊师重教!不必担心你爹娘,张家儿郎,胸怀忠贞,心系天下,切勿辱没了张家先人!”
张堂文说罢,双手抱拳,深深地躬了下身子,便头也不回的走了。
张春福尚有三分迷瞪,却也被张堂文的深情所感染,泪流满面。
杨鹤汀轻叹了一声,朝着张堂文远去的方向躬身回礼,罗飞声虽然不曾进屋,却从杨鹤汀的反应中猜到了大概,一同躬身相送。
张堂文大步流星地走出校门,在门口处回望着南阳公学的匾额,杨鹤汀手写的四个大字依旧是那般苍劲有力,张堂文不由深深地提了一口气,冲着等在门口的马车车头说道:“走吧!去武庙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