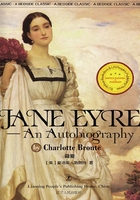道童带二人穿过迷宫一般的走廊往东楼的一层走去。楼下是一条宽阔的走廊,竖着一排高大的朱漆柱子,柱子上雕刻着飞龙腾云的图案,工艺繁杂,巧夺天工。人们穿着毡鞋从这里进进出出,把地板磨得发亮,发出幽暗的光泽。他们来到迎宾厅前,狄公对陶干说,“我去见住持,你且去找监院,希望他今晚之前就能找人换好损坏的车轴。”继而又压低声音,说道:“看看能否从监院或其他什么人那里找到这座阴森森的道观的平面图。”
迎宾厅位于大殿入口处。道童把狄公请进厅内,屋内暖烘烘的,铜炉里堆满了烧红的炭火,狄公心下十分满意。墙上挂着上好的帷幕,有很好的保暖作用。
见狄公进门,一位身材修长、略显消瘦的老道从鎏金卧榻上连忙起身,踩着厚厚的地毯,迎了上来。他神色庄严,身着明黄色锦缎长袍,头戴上清冠,一条长长的红色缎带一直垂到背部,越发显得他身形颀长,气质飘逸。住持上前施礼,狄公发现他眼睛呈古怪的蓝灰色,和他严峻的面容一般,冷冰冰的;上唇留着两撇小胡子,颔下蓄着一绺稀稀疏疏的胡须。
二人在卧榻旁的太师椅上落座,道童正在拐角的朱漆茶几旁准备茶水。
“下官此行唐突,”狄公先开口道,“恰逢仙观庆典之大日,宾客众多。我等叨扰一晚,还望仙长海涵。”
住持淡然地望着狄公,但狄公却有种异样的感觉,总觉住持目光闪烁,眼神回避。住持眼眉一挑,声音低沉沙哑,道:“大人此番前来,实属敝观之幸。东楼二、三两层有客房四十余间,但条件简陋。招待不周之处,县令大人莫要责怪才好。”
“厢房温暖舒适,我等甚是满意。”狄公忙道,伸手接过道童奉上的香茗。此刻,他的头阵阵作痛,无意再寒暄客套,便开门见山地说道:“刚接任汉源县令时便有意来贵观,一则聆听仙长教诲,欣赏观内风光,二则还有些事情想当面请教,怎奈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如愿。”
“但说无妨。不知大人所谓何事?”
“去年在贵观有三人不幸殒命,下官想了解些相关细节,”狄公道,“以作增补卷宗之用。”
住持挥手示意道童退下。待大门关上后,住持虽面露不悦,但脸上仍挂着笑意问道:“大人,敝观有道众不下百余人,这还不算杂役、道童和往来的香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修行之人亦和天下苍生一般,也会生老病死。不知大人指的是哪三人?”
“是这样的,”狄公答道,“下官在公堂翻看卷宗时发现,贵观转呈至我汉源县的死亡文书副本中,居然有三名从外面来的女子在此殒命。她们可是来贵观修行准备出家的?”只见住持眉头微蹙,狄公旋即赔笑道:“我也记不起她们的名讳和具体细节了。本应查阅妥当后再来宝观,但今日凑巧到访……”狄公欲言又止,侧目瞧向住持。
住持微微点了点头。
“贫道知道大人所言何事。的确,去年从京城来了一位姑娘,说是姓刘。刚到这里就病倒了。孙天师亲自为她把脉调理,但……”
他突然缄口不言,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狄公转身,正待细看是何人进入厅内,却仅看到门又被人合上了。
“看看这些粗俗无礼的戏子!”住持怒吼,“门都不敲就往里面闯。”看到狄公一脸惊愕,他又道:“依惯例,我们雇了个小戏班协助观里的道士在庆典之日表演神仙道化戏文。此外,这些伶人还穿插着表演些杂耍等小把戏助兴。他们对本观庆典虽有助益,但是对道门规矩一无所知。”他生气地将拐杖敲了敲地面,道:“下次再也不能请他们来了!”
“嗯,”狄公道,“我想起来了,这位刘姓姑娘说是死于顽疾。敢问住持,当时是何人验尸的?”
“是敝观的监院,大人。他精通岐黄之术,医术高明。”
“原来如此。是否还有个姑娘是自杀身亡的?”
“实属不幸啊!”住持叹了口气。“她本是个聪慧过人的姑娘,但人有些癫狂,饱受幻象折磨。贫道本不愿收她为女弟子的,但她本人十分渴慕修仙求道,家人也十分坚持……一天晚上,高小姐惴惴不安,竟服毒自尽了,尸身运回家中后便下葬了。”
“那这第三位女子呢?下官依稀记得她也是自杀身亡的?”
“大人所言差矣。黄小姐是意外身亡的。她才华横溢,对敝观历史典故十分感兴趣,常常独自一人游览楼台殿宇。一日她倚着东南塔楼楼顶的栏杆欣赏风景,不想栏杆朽坏倒塌,她便失足跌落在道观东边的山涧之中,不幸殒命。”
“难怪在黄小姐的卷宗中未发现尸格。”狄公道。
住持遗憾地摇了摇头。
“是的,大人。”他缓缓道,“尸身至今尚未找到。山涧底有个深沟,约有三十多米,还没有人能探入谷底。”
狄公若有所思,继而又问道:“她可是从库房顶的塔楼坠下的?若是如此,便正对着我所居住的东楼。”
“正是。”住持呷了口茶,显然想结束今天的会谈。但狄公并没有起身离开的意思。他捻了捻一侧胡须,又问道:“不知是否有道姑久居仙观?”
“幸亏没有!”住持淡淡地笑道。“观内事务十分繁杂。承蒙道众抬爱,小观空得虚名,在州府颇有威望。家中有女子愿意入我门者,都坚持要在敝观出家。她们在观中先修行一段时日,待颁布牒文后,便离开本观,遣于各处宫观继续修行。”
狄公打了个喷嚏,掏出丝帕擦拭胡须,谦恭地说道:“多谢仙长不吝赐教!贵观秩序井然,观规严明。只是下官职责所在,多有得罪,还望老仙长海涵。”
住持黯然地点了点头。狄公将杯中香茗饮尽,又问道:“适才仙长提到的这位孙天师,莫非就是曾在御前侍奉的孙太傅,我朝赫赫有名的高道名士,孙明孙大人?”
“正是!孙天师能长留敝观,实乃敝观之无上荣耀!天师官居要职,曾任雍州长史。两位夫人病逝后,他便请辞告老还乡,此后又被拜为太子太傅。当他离开宫廷时,三个儿子也已长大成人,各自拜了官职。因此,他便决心余生潜心于玄学之术,并把敝观作为居所,在此修行。孙大人在此已有两年之久。”他微微点头,洋洋得意地说:“孙太傅大驾光临,实属本观一大幸事!天师从不恃才傲物,反而时常与弟子讲经论道,参与各种法事。观中大小事宜,天师事必躬亲,不吝赐教。”
狄公无奈地想,看来自己必须去拜会拜会这位大名鼎鼎的孙大人了,便开口问道:“不知孙太傅身居何处?”
“天师栖身于观内西楼。不过大人此刻前往大厅便能见到天师,他正在那儿看戏。一同观戏的还有位包夫人,是个一心向道的孀妇。几日前和她打算出家的女儿白玫由京城来到本观。还有位公子,名叫曾黎,尤其擅长吟诗作赋,也在观中待了数日了。他们是敝观仅有的宾客,因这雷雨天,观内宾客不多。此外还有关赖戏班的几个戏子也在观内——大人怕是对这些身份卑微之人没什么兴趣。”
狄公冷笑一声。世人皆以卖艺谋生为“小道”,难登大雅之堂,优伶更是身份低贱。他素来觉得这种观点有失公允。本以为住持乃得道高人,悲天悯人,会有不同的论断。便道:“依下官浅见,优伶于世还是大有裨益的。寻常百姓闲暇时听听戏文,不仅能消愁解闷,打发时日,那些历史戏文还能让世人更加尊崇历代先贤,了解他们的丰功伟绩。这点也是贵教的神仙道化戏文所匮乏的。”
住持生硬地辩解道:“我教的神仙道化戏文是为了教化度人,宣扬真道,其他戏文怎可与之相提并论?”为了缓和气氛,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大人莫要误以为他们不敬重先贤。这些面具和戏服已有百余年了,十分贵重。容贫道带大人前往大厅。今日晌午就开始演了,现在估计已经是最后几出了。稍后斋堂还将略备薄酒,望大人能一同前往。”
狄公平素最不喜欢这种应酬,但身为县令,且这朝云观又在治内,故不好推辞。于是强颜欢笑道:“承蒙邀请,下官自当前往。”言毕,他们相继起身,住持引他走向大门。
刚推开厅门,住持迅速环看四周,确定昏暗的走廊空无一人,他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他恭敬地带狄公走到大厅门外,两扇朱漆大门映入眼帘,气派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