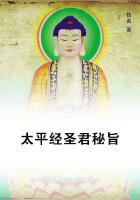1
现在是2004年7月22日晚9点15分,在北方城市太原,我坐在六楼窗口的灯下,开始写海。
窗外是层层叠叠的窗户,亮着灯或者没有,我知道越过它们,就是这座北方城市明亮的夜空。在强大的明亮面前,黑暗似乎只是点缀。这样的情景,人们习惯上会称它:灯火的海洋。
以前我是半个农民,有一年端午节后的一天,我拄着锄把伸直腰杆,嘴角因为腰的酸痛向耳根咧了一下,我把右手握成拳头捶捶腰,然后腾出左手,抹一把额头的汗水。这时候,我感觉一阵风从我的背后升起,掩过我的头顶进入邻村的麦田,接着麦田里腾起一阵剧烈的金色起伏,将风传出很远。如果语文老师在场,他会激情迸发地大喊:“啊!金色的麦浪!”麦浪起伏的场所应该是麦海了,但我没有听他这么喊过。
如果我还是一个农民,也许我这一辈子也不会离开我们的村庄,像村里很多人那样。也就不会看到海和描写到海,我是指真的海。但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像你们都知道的那样。所以下边我要写到真的海。
2
那是北方夏日的一个午后,我站在渤海的海边,我背后的这座城市叫秦皇岛,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北戴河。太阳好像刚刚还很烈,但似乎很快就黯淡了。和我站在一起的还有我的一个校友。他毕业分配在了这个城市,以后他将在这个城市里工作、生活、结婚、生子,而我还要回到遥远的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我只是做短暂停留,停留是为了看海。
他终于办完了事,于是我们急不可耐地跑到了这个城市所毗邻的海边,因为我们都生长于内陆。这儿其实是个游泳场,不远处拦着网,竖着的牌子上写着:小心鲨鱼!偶尔有很小的风,因而浪很细。实际上被网着的这块水面没有给我海的感觉,我觉得网的外面才是海,那里有鲨鱼,鲨鱼会一口咬断你的脚脖子!像电影里放过的那样。海应该是危险的和令人恐惧的。
人很多,游泳场像个露天的澡堂,本地人口头上都把它称作:海滨浴场。
我们下到水里。水很浑,被人们的臭脚踏得四碎的海草碎片升起又沉下。脚下频繁地碰到内陆人称为贝壳的东西,但是形状没有早些年内陆市场上用来装雪花膏的那种优美,想来想去,就用歪瓜裂枣来形容眼下的它们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校友会游泳,狗刨式,在北方小泥潭或者水库里自学成才的大都是这种姿势:头努力地向上仰着,两手和两脚在水下急速地向后划水,缓慢地行进,样子就像刚学会爬行的婴儿。我没有自学成才,所以只好在海水里走来走去,当然只能是缓缓的。我跟在校友的后边,他游不多远,就慌忙站起来,呼哧呼哧地喘气,我就哈哈大笑,笑他的狗刨和滑稽,他就谦虚地笑,腼腆地笑。他的笑充实了我的自信,我于是憋着一口气,放平了身体,试图展示一种完美的泳姿,但结果是很快地没在了水下。我手脚并用地划水,以为过了很长时间,并以为游出了很远,但站起来才发现,与原地不过咫尺之遥。
憋着气,闭着眼睛,水下不辨方向,我和校友之间渐渐就有了距离,而且我离开岸边越来越远。
阳光变得黯淡,但海水依然温暖,我一会儿站起,一会儿潜下;一会儿潜下,一会儿站起。
当我又一次想要站起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海水淹过了我的头顶,而我并没有向着海的深处游(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涨潮了)。现在我是在很深的海里了,我急速地想。海水淹没了我的头顶,恐惧一下子攫住了我,慌乱中已经灌了几口海水下去,海水又咸又苦又涩,而且肮脏。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想到了死,平生第一次想到了死,我想我真够倒霉的,大学毕业第一天就被淹死在这秦皇岛外的海里,我可真够冤枉的!我没有想到同样淹死在海里的还有著名的聂耳。我想活,我想喊,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游泳的人已经变得稀少而且遥远,我估计我的喊声只有被自己听到,他们的嬉笑变得虚幻。我再次能够浮出水面的时候,短暂地看到了我的校友,也很遥远,但我还是看清了他,认出了他,他还在刨一阵,歇一阵;歇一阵,刨一阵。我想大笑,但我的笑很快就被淹在了水下。我想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了,于是我不再慌乱。我发现在水下憋不住的时候,喝下一口水可以缓解肺部的压力,于是我就喝下水;我又发现,在水下用力蹬地,可以使我暂时地浮出水面,于是利用浮出水面的机会,我大口吸气,而当再次沉下的时候,我努力向岸的方向前进。我不断地鼓励自己:今天你能到达岸边!不知道这样挣扎的过程到底有多久,也许只是短短的十分钟、半个小时,但我的感觉像是过了千年。终于,再次站在海底沙地上的时候,不需要蹬地头就可以露出水面。我没有欣喜,只是如释重负,像完成了一件异常艰难的工作,长长地吐了口气,疲惫地向岸上走去。头很晕,很恶心,想要呕吐,但终于没有吐出来。招呼校友上岸,没有跟他说今天我差点送命。
3
我曾在另一个夏初再次来到渤海的海边,但这次背后的这座城市叫大连。
我在这个城市里转悠了一天之后,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我暂时寄居的同学家里,我决定就在这个城市的某处,露天地等到天亮,天亮之后去看海。
海边的初夏仍然冷,而我却错误地以为白天晒得我脱皮的阳光起码可以使夜晚温暖。
当夜幕缓缓降临的时候,我像这个城市中一个无事可做的闲人,在临近海边的一个小区开始闲逛。我凑在人群中看当地人赤着脚摇着扇下象棋,听他们用方言争论每一步棋的对错和香臭;或者看他们在树阴下使劲地甩扑克,互相用粗话骂骂咧咧开着玩笑。时间在一点一点地过去,下棋的人终于打了哈欠,甩牌的人也伸了伸懒腰,提起棋袋子收拾扑克陆续散去。夜幕渐深,楼房窗户的灯光一个接一个熄灭,终于一个不剩。
现在,我似乎看到了当时的我。凉亭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除了路灯,一片黑暗。楼房挨着楼房,窗户邻着窗户,表情木讷,像人睡着之后的酣态。我感到了困倦和寒冷,于是竖起衣服的领子,想以此减少热量的散失,然后在凉亭的长凳上躺下来,努力地想睡着……但寒冷还是把我叫醒,我只得站起来,走向草地,开始练武,低声地呼喝,猛烈地挥拳或者出脚,身体因为运动而暖和起来,于是停下。冷很快又袭上来,我又练武,终于实在是累了,但又不敢不动,所以只好四处地走动。四下里没有一个人,只有昏暗不明的路灯和浑浑噩噩的植物。冷,还是冷,越来越冷,我紧了紧衣服,继续行走,不敢停下。海上的风吹来,带着潮湿而尖刻的寒冷,刺骨!我现在开始恨海,开始恨自己这个愚蠢的决定。在经过一个停车场的时候,脚步惊醒了守护者的警惕和不真实的咳嗽,我走过他,没有想要停下来,甚至没有想到取暖。我越来越不敢想到海,包括恨。海现在是黑暗的和阴冷的意象。我不敢想到海……
夜色在一点一点艰难地退去,天空变得灰黑,星星稀少,闪闪烁烁。我无意中已经走到了一个叫作“星海公园”的门口,走进公园的大门,没有人向我收票。在海边,我坐下来,面对黑暗中的大海,近处和远处没有分别。海上没有一丝灯光,只听到风卷海水的声音:“哗——哗——哗——”
身后有人吭哧吭哧地走近,路过我的时候,我感觉到沉重。在不远的地方,他们将肩上的东西重重地卸在海里,“嘭!”沉闷但没有惊起什么,因为四周一片黑暗。仔细看,大概是用木板和橡皮轮胎扎成的筏子,他们坐上去,向海的深处划去,背后是这座晦暗的城市和昏睡的人们。他们是去捕鱼的。白天吃到的本地人叫作“牛舌头”的鱼,就是他们这个时候打上来的吧,我想。对他们来讲,海就是他们的麦田了,我又想。
暗终于完全退去,天空终于亮起来,海边巨石的轮廓开始清晰,终于细节分明。我站起来沿着海走动,看海从晦暗中显现。远处一老妪向我走来,走一段就停下来,捡起什么,又捡起什么。走近了才看清是海带,长度超过我的身高,内地是没有见过的。一定是昨夜涨起的潮水送上来的,我想。
在堤坝下,我看到粗大的管子,城市的污水正从那里源源不断地进入海,发出剧烈的声响。刚才天黑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我还以为那是海特有的美妙声音!望一眼不断溅起的污浊泡沫,我一阵恶心,匆忙逃开,向公园的大门走去,路过公园里晨练的人们,没有人注意到我的表情。
2004年7月22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