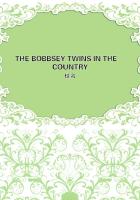第二日一早,顾青梧需到县上青岩书院去,答谢老师和院长。临行前,老学究硬逼着顾大郎同去,更是不住的嘱咐顾青梧道:“大郎这孩子病了一场,肚子里那几滴墨水吐了个干净,你此去书院,定要求得田师和山长应允大郎入院之事,让他与你同行,这孩子精明得紧,或许能得长辈赏识,唉,若是你们父子都能有出息,老夫我这一辈子也就无欲无求了。”
顾青梧不敢不应,只得把顾大郎带在身边,但路上却又是另一番话,“你这孩子自小就老实,爹爹不长待在你身边,因此要问你一句,你可真的是爱读书?愿意进书院?”
顾大郎愣了愣,试探着答道:“儿子,儿子不,不是那么喜欢吧……”
“你既不喜欢,爹爹自不会勉强你,书院在外人看来或许高不可攀,但在我看来,也算不得什么好地方,反正都随你意,爹爹是不会参和的。”顾青梧一口打断他话,似乎很明道理的样子。
这模样叫顾大郎颇感意外,但转念一想,老爹或许在书院里吃了不少苦头,也就不愿意自己重蹈覆辙,当下不禁生出一股有父如此,夫复何求之慨。
二人乘着牛车,一路缓行,及至巳时初刻才到县城,买了些见面礼又耽搁不少功夫,修整一番,这才上门。到了书院门口,门房识得顾青梧,但见他换了秀才的装束,忙诧异道:“顾、顾……可是今次过了院试?”
顾青梧昂了昂头,冷哼一声答是。那门房当即换了面色,露出一股难以言表的谄媚,“恭喜顾相公得偿所愿,小人在这里有礼了。顾相公这是回书院见先生和院长的吧?”
顾青梧应了一声,从怀中掏出几个铜子儿递了过去,敷衍的答了声谢,便进了门,他是书院弟子,这进门一道不需通传。
领着顾大郎入了二门,即见一个宽阔的广场,放眼望去除了四周设有几方石凳外,并无它物,广场上倒是有十来个书生抱着书绕着四方长廊摇头晃脑、吟诵不断,显是极用功的样子。
顾大郎不曾进来过,自是有一股新鲜感,一路走过不停左右环顾,见得里间七八个学堂里正有先生授课,顾青梧立在一处学堂外好半响,这才舒了口气,叹道:“为父在这间屋子里待得够久了,现下却有些不舍,真是滑稽。”
里间几个贪耍的学子见顾青梧父子在外候立,顿时发出一阵唏嘘声,上方先生闻声当即呵斥一声,偏过头望出来见到顾氏二人,脸色一喜,随即吩咐底下学生道:“尔等温习适才所学一章,稍后老夫挨个考校。”言罢,起身出门向二人走来。
顾青梧不待老先生到得跟前,已先躬身拜倒,“青梧见过老师。”顾大郎自也跟着拜了下去。
老先生口中连忙道:“勿须如此,青梧且起。头两日听院长说起,你已过了院试,老夫心下大慰,也总算不负你十二年苦读之功。”老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将二人带到檐下石凳旁依礼而坐。
顾青梧脸上一红,只道:“弟子资质愚钝,让老师操心了。”
当年与他同进书院者,要么已考进上院,身具秀才甚至举人、进士功名,要么早已收拾书卷,经商务农而去,唯有他一人苦苦坚持,如今总算天不负人。老先生十余年来看在眼里,也知他不易,故而素日对他多有照看,是以今日甫进书院,顾青梧便领着儿子前来拜谢。
这时老先生终于看向顾大郎来,见他面容与顾青梧有七八分相似,心下自是了然,客套地赞道:“这位可是令郎?眉目清秀,颇具风仪,真是个好少年。”
顾青梧闻言,自也欢喜,忙令顾大郎见礼。顾大郎原本立在父亲身后,这时见老先生问起,当下站了出来,又是躬身拜倒,“晚辈顾双木见过师公。”
他声音清朗,举止从容,瞧在眼里只教人舒畅,老先生捋了捋胡须,笑着赞道:“青梧生了个好儿子,将来必有作为。”
虽是客套之言,但顾青梧听了,心下却一万个赞同,自己的儿子哪有不好的?登时便道:“今日弟子前来,除了看望先生外,便是为了这孩子的事情,这孩子原是跟在家父身边蒙学,资质远在弟子之上,不料今夏为救人落水,招致恶疾,得了失魂之症,从前所学忘得干净。家父的意思乃是让这孩子进书院来请诸位先生教导。家父年纪大了,弟子需得回家接替他老人家的差事,村中私塾可不能停的。”
老先生闻言,点了点头。心里想到,以顾青梧的资质,这辈子秀才功名应是到头了,再耗在书院中也属无益,让他儿子进来补了老父的位置正好合适。只是这等大事他一小小教学先生哪能做得了主?故而只好道:“院长和田师今日正好有暇,你不妨去他二人处求求情,想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
拜别老先生,顾青梧又领着儿子往书院后院而去,后院乃是先生、学子宿舍,寻常时候便是院长也住在此间。这时院长澜沧先生正与训导田尚奇谈论院中教学之事,忽听厅外童子传话来,‘新进秀才顾青梧领着幼子拜见两位老师’。
澜沧先生愣了愣,随即指着田尚奇脸面笑道:“头二日还说起顾家那个精怪的小子,如今便要见面了么?顾青梧可还有其他的儿子?”
“顾氏三代单传,可不就是那小子么?当年他出生时,在下还派人送过贺礼,一转眼十多年,这小子都已长大成人了,不曾想竟是个精灵古怪,异于父祖之辈。”田尚奇亦笑着答了,又令童子带二人进来。
这田尚奇少时与老学究有同窗之谊,乃是三十年的老举人,曾在外县做过几年县教谕,后受澜沧先生相邀,辞官归乡,协助他创办青岩书院。可说如今青岩书院闻名川渝,田尚奇堪居半功。
顾青梧二人随着童子进了三省堂,但见里间两个头发灰白的老者正谈笑着,当即引着儿子往前快走几步,躬身拜倒,“青梧携幼子大郎,见过院长、田师。”
田尚奇面色慈祥,挥挥手笑着道:“你这孩子事事都好,就这执拗劲跟你父亲别无二致,快快坐下,别多礼了。”言罢,又吩咐小童上茶。
当下顾青梧寻了个凳子,半边屁股坐下。顾大郎辈分更低,自然只有候立父亲身后的,虽是老大的不愿意,但也不敢表露出半分,只是低着头轻轻呼哧两声。
上方澜沧先生却似有意观察他一般,一双眼将他看了个通透,直叫顾青梧一身的不自在,怎么,难道院长识得大郎不成?
田尚奇见状,连忙咳嗽两声,打趣道:“老先生初见小童子,忆起当年风发乎?”
澜沧先生自知失礼,当下端起茶杯小抿一口,只道:“少年人朝气磅礴,真是叫人羡慕,老兄弟,咱们二人日薄西山,还能饮几回?”
顾青梧原本便是内敛之人,听得两个老头儿互打哑谜,一时间倒不知该如何插话,脸上不免一红。所幸田尚奇将话题又转回到他身上,“青梧,今次秀才中试,我等还没恭喜你呢?”
顾青梧闻言,立时又要站起,却见田尚奇摆了摆手,复又续道,“坐下坐下,今日你正好来了,我且问你,日后有何打算?可是还要进上院深造的?”
顾青梧忙答道:“弟子资质愚钝,自知人力有穷时,此生举业已到尽头,故而今日前来,是想向二位师长辞学。家中老父年迈,身为人子的,自当在他老人家膝下尽孝,还望二位师长体谅。”
澜沧先生与田尚奇互望了一眼,轻轻点了点头,这才答道:“你这孩子也忒妄自菲薄,也罢,你既已下定决心,老朽也不便为难你。只是学习一事,不拘于学堂,只要有心哪里都能读圣贤书,你可不能就此松懈,须知学问一事,当终身不缀。”
顾青梧正色答了,便又说道:“今日弟子前来,除了辞学一事,还有一事想求两位师长应允。”
“你且说来。”
顾青梧便又将顾大郎入书院求学一事说了。他话音一毕,却只见两个老头儿对望一眼,当即哈哈大笑,他不明就里,不自禁便将头往后偏去,这些时日他渐渐形成习惯,但有困顿,就想着儿子,儿子定有法子解决!
顾大郎也自惊疑不定,他并不清楚这两个老头儿心里打了什么主意,但总觉不踏实,似乎一股阴谋正悄然布局。
田尚奇瞧着父子二人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模样,当即忍住笑声,道:“青梧啊,你这孩子在书院也待了有十来年了,难道还不知书院的规矩么?若真是腹有诗书,便再是清贫,书院也是收的,但若胸无点墨,那便是天王老子来求情亦无用矣。”
顾青梧听到这里,心下一急,急忙解释道:“田师,大郎这孩子您老是知道的,向来最是聪慧,天资甚高远胜父祖,只因今夏救人而失了记忆,否则明年开春招生试,不需弟子相求,他也尽可进得书院。”虽说他并不强求儿子入书院求学,可若试也不试,便又太过不像话了。
澜沧先生点了点头,只道:“嗯,这事还是头次听说,你父亲治家有方,这孩子品行倒是不错。只是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我等虽是先生,却也不可不遵规矩。”他话中似乎一片为难,但听口气又留有余地。
顾青梧闻言,当下急得差点哭了出来,这便要站起、下跪相求,他身后顾大郎却按住他身子,温声道:“爹爹莫急,既是院长和田师有疑,不妨当场一试,若是孩儿真没这福分,那也不能叫两位前辈为难才是。”
顾大郎虽不曾与澜沧先生有过交集,但听他适才之言,总觉得有一股幸灾乐祸的味道,自不免暗生好胜之心,故而当场求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