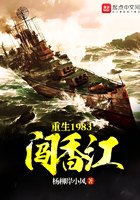帕萨特车上,吴子玥反复叮嘱钟海说:“虽然我和你约定等你搞掉了王一鸣咱们再确定关系,但我要警告你,你和那个黄一一在一起时,千万别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如果被我发现,我绝不轻饶。”
“你放心,我就是用手也不会失去了我的操守。”钟海一激动,冒了一句。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太粗俗,想掩饰过去,可已经来不及了,吴子玥接着钟海的话就好奇地问道:“什么叫用手。”
钟海脸一红,说:“用手就是——这是男人们的事,不能告诉你。”
“我就要知道,不然我就把你撂在这儿。”
吴子玥话音未落,帕萨特已经溜到路边停下。钟海了解吴子玥的脾气,就把嘴巴附在吴子玥的耳边,如此这般解释一番,吴子玥听了一把推开钟海,羞涩地说:“去你的,流氓,你们男人都是流氓,什么流氓话都说的出口,什么流氓事都做得出来。”
“世界上本无流氓,只是因为有了女人,男人才变成了流氓。”钟海自豪地说。
对于男女之事,钟海真的没做过,说他不想做那是假的,可吴子玥根本不给他机会,他也不能死乞白赖地霸王硬上弓。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表现的太过分,他担心吴子玥会看不起他。
男人最怕的就是被女人看不起,尤其是被自己心爱的女人看不起。
钟海躺在外间的沙发上,听着里面传出的电视声,想象着吴子玥看电视的模样,慢慢地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一缕灿烂的朝霞透过玻璃窗照进来,洒在了钟海的脸上。钟海睁开眼睛,看看墙上的挂钟,时针直到了八点多。他一骨碌从沙发床上爬起来,连鞋子也顾不上穿,一边叫着子玥的名字,一边冲向卧室。
卧室的门开着,吴子玥不在床上。这丫头,上班也不喊我一声,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钟海嘟囔着,从卧室出来穿了鞋子,到卫生间洗漱后跑进了厨房。
碗里放着稀饭了,两根油条被纸裹着放在案板上,钟海抓起油条就塞进嘴里,三下五除二油条就被他消灭干净,正要再喝稀饭时,外间的手机响起,钟海走出了厨房。
电话一定是王一鸣打来的。学校里,除了王一鸣能给他下命令,一般人没这个资格。
可是,钟海这次又错了,电话是陌生的座机打来的。钟海摁下接听键,把手机放在耳边,一边询问对方是谁,一边走向厨房。只吃干的不喝稀饭,钟海一个中午都会很难过。
电话里很久都没传出声音。
钟海也不说话,把碗沿挨到了嘴边,还没喝一口,对方就冷漠地问道:“请问你是钟先生么?”
“嗯,请问是哪位。”
“我是分校的黄素芬。”
“哦,黄董,你你好,有事么?”
钟海叫了声黄董,不禁想起自己曾经把黄董想成了“晃动”,不由一笑。
“别笑。”黄素芬严肃地说。
“黄董哪天制定了法律,说打电话时不能笑。”
“我和你说正经的,别嘻嘻哈哈的。”
“我没和你嘻嘻哈哈,我一个晚辈,怎么敢和你嘻嘻哈哈。”
“请你马上到这里分校来一趟,我有事要和你谈。”
“你和我谈事就该到一高来,我没工夫到分校,对不起,我还没吃饭,我得挂了。”
钟海挂断了电话,把手机放在了案板上,心想,一个外地人,来到安州市揩我们的油,还如此霸道,真的把自己当做一棵大葱了。
刚喝了一口,电话又响起,钟海看看,还是那个号码,接听后没好气地说:“你到底有完没完。”
“我的女儿黄一一出事了,我要你马上到分校来一趟,不然我就决定改变咱们见面的地点,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希望你慎重考虑。”
这次该黄董耍大了,她说完后不等钟海回话,就挂断了电话。
钟海本来没打算把黄董当一棵大葱,可一听说黄一一出事了,不由把心提到了嗓子眼,自己昨晚就和黄一一在一起,如果黄一一遇到麻烦,自己肯定逃不了干系,于是咣当一声把碗放下,抹了一把嘴拿起手机就奔了出来。
一路上钟海都在想,黄一一到底怎么了。他昨晚亲眼看着黄一一开着奔驰进了校园,总不会又开车跑出来出了车祸,或者发生了其他不测。钟海越想越害怕,不由吩咐司机加了油门,快速赶到了学校。
钟海在校门口下了车,直奔校园。门卫看到钟海闯进去,就在后面追赶着喊道:“喂,你找谁呀,请你登记——你站住,我然不吃不了兜着走。”
“我找你们董事长,是她叫我来的。”
离办公楼还有二十来米,钟海就看到黄董端着茶杯站在一个阳台上。他朝上招招手,把手做喇叭状朝上面喊道:“黄董,一一到底怎么了。”
黄素芬朝钟海扬扬手,把手放在嘴边做了个“嘘”状,然后端着茶杯走了下来。
楼道门口,黄素芬朝钟海笑笑,脸上的微笑就像春潮般朝着钟海涌过来,钟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问了句:“一一到底怎么了。”
“年轻人别急,你先我和到办公室待一会儿,咱们先聊聊,然后再说一一的事。”
钟海跟在黄素芬进了办公室。
黄素芬的办公室比王一鸣的办公室豪华多了。原木色的办公室油光滑亮,黑色的老板转椅看上去就想给人舒适的感觉,墙上挂着七十二的背投,办公桌上放着崭新的电脑,一台立式空调放在门后,吹风口的塑料过滤板上拴着五颜六色的绸布条。尤其令钟海心动的是,一排枣红色的组合柜把宽敞的办公室分为两半,而中间的一个柜子上挂着一副蒙娜丽莎的微笑。钟海估计,外边是办公室,里间可能是黄董的卧室。
“请坐。”黄素芬殷勤地说。钟海惴惴不安地坐在了沙发上,黄董也跟着坐在了钟海的对面。她跷起二郎腿,一手按着沙发,一副很随意的样子,任何人都不会把这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女人和电话里蛮不讲理的声音联系起来。
“你喝点茶么?”黄董慢条斯理地问道。
钟海摇摇头,他本能地拒绝这个女人。钟海忘不了她在电话里咄咄逼人的声音,而他最讨厌这种声音。
“到分校来千万别客气,如果你愿意,尽管把这儿当做你的家。说到家,请问一下,你家就在安州市么?”
这个女人果然不简单,随便几句话就开始盘问钟海的家底。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我家不在安州市,不过离安州市也不远,就在城乡结合部。”
“没关系,毛主席说过,出身不由己,但道路可以自由选择。城乡结合部也不错,最起码民风淳朴,空气清新,其实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在地球上,跑不到月亮去。”
“黄董不愧是从北京来的教授,语出惊人,一语中的,令人佩服。”钟海敷衍着说。他不明白黄素芬今天一大早把他喊过来到底所谓何事,黄素芬不说,他也不提,他倒要看看这个女人葫芦里到底买的什么药。
黄董受到钟海的夸奖,好像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就越发亲昵地问道:“钟秘书家里都还有什么人呀。”
“母亲早亡,现在只有父亲和我相依为命。”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不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还是那句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自由选择,你不必为卑微的出身而感到自卑。”
两个人就这样相互恭维着,奉承着对方,听起来是那么的真诚,但细想起来却感到异常的虚伪。不知不觉中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钟海终于失去了耐心,就主动开门口问道:“黄董,你在电话里说一一出事了,她到底怎么了。”
黄董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把椅子拉开,重新坐了下来,说:“我听说你昨晚和一一在一起,有这回事么?”
钟海从黄素芬稳健的谈吐中发现,黄一一根本没事,他悬着的心早已沉到了肚里,现在黄素芬终于扑到了正题,钟海的心不免又突突起来。他昨晚和黄一一单独在河岸上漫步,虽然没主动做出什么有违天理的举动,但黄一一毕竟趁他不注意吻了他一下,他担心患有精神分配抑郁症口部遮拦的黄一一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她的母亲,所以才惴惴不安。
为了以防不测,面对黄素芬的盘问,他不能不据实以告,于是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是的。”
“你们是怎么约会的,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和一一走到一起的。”
“我没和她约会,只是碰巧。”钟海觉得黄素芬的表述有失偏颇,就纠正道。
“碰巧?你以为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妙龄女郎晚上在河边披着月光漫步谈情说爱是碰巧?”
钟海不明便黄素芬为什么要问这些,但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黄素芬已经知道钟海“约会”了她的女儿黄一一,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不能让黄素芬对他产生误会和偏见,于是就解释道:“这事还得从白天发生的事说起,我拿了支票出了校门后刚要坐出租车,碰巧黄一一开着车到市里办事,就把我捎带到了市里,路上我们说了几句话,下车时她索要了我的手机号码,我当时也不想给,但她非要我给,所以我就号码给了她,这不,到了晚上,她就给我打电话,说有事要和我谈,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就如约前来,在河岸上和她散了一会儿步,说了一会儿话,事实就这样,不信你把黄一一叫来,咱们可以当面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