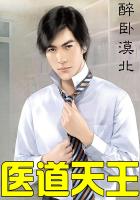“宋公子。”一名老朽来到石桌前。
“商先生。”宋时琰站起身来作揖,摆手,“请往这边走。”
他推开房门,迎面涌来一阵药味掺杂着一些血腥味,“请。”
宋时琰推开窗户通通风,冲淡血腥味。
老先生在榻前站定,观察司木面色,看眼瞳,再切脉。诊了许久的脉,老先生一言不发。
“姑娘服用还魂丹,性命无大碍,不过高烧会反复两日。主要是灵海受创,棘手一点。老朽主要用温养的方式治疗,这样留下的病根会少一些。”老先生抬头对宋时琰陈述着诊脉结果。
公子点着头,“敢问先生,姑娘何时会醒?”
“大概这两日,且服两个方子再看。公子不必担心,老朽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有信心的。”
“商先生的医术在下怎会质疑。”宋时琰为老先生铺好纸笔。
老先生执笔写下两个方子,递给他,“姑娘的伤势尚不能服丹药。第一张为内服方子,药材熬成汤,五碗水熬成一碗,一日三服;第二张为外敷方子。麻烦公子准备药材送至老朽房中便可。”
商先生若是开的不常见的药疗方子都会跟患者家属讲解。
“好,先生慢走。”
商先生走到门口就跟顾培轼夫妇打了个照面。
顾培轼拱手,“商先生,有劳了。”商先生回礼,道先行离去。
顾夫人快步到床榻边,手轻抚着司木苍白的脸,“可怜的孩子哟,怎会伤的如此之重。”话间,眼中有泪,顾夫人越看司木越发心疼。
顾培轼看着孩子,呼吸慢了下来,服用了还魂丹还如此憔悴,那伤的是多重呀?转身问宋时琰,“可查到是那方势力?”
宋时琰轻声说,“南越太子。”
顾培轼也是知道南越的朝政局势---太子和宣王争位。啊木惹上南越太子,那岂不是跟宣王有交易?
又问,“如何处理?”
“陈墨废了两个武尊玄力,红叶团不是吃素的。小侄已经查到南越太子贪污,强抢民女,开地下赌坊的证据,现在坊间应该在声讨他。”宋时琰如是应答。
虽说他身份敏感,但是东鲁皇上不介意看南越乱上一乱,南越最近是有些猖狂了。
顾培轼赞同地点点头,“阿木受伤的消息我会处理的,司倔驴那边有我。你回去好好休息,再处理这事,别给自己惹上麻烦。”
十日后是东鲁皇帝的生辰,北齐南越使者进京贺寿,宋时琰的商行承办着使臣的衣食住,处理不当,可是会招来一堆麻烦事。又身为当朝宰相之子,谣言猛如虎呀。
“知晓,姑父也好生休养。我下午再过来探看姑娘。”
“去吧,去吧。”顾培轼看着宋时琰的背影,两人合作多年,这小子怎么不对木丫头动感情呢?这肥水不流外人田,要是在皇帝生辰宴上被赐婚就不好了。
宋时琰回到宋府,向父母请过安,回到房间睡上一觉。昨晚和陈墨顾知喝多了,又一夜未睡,头晕晕涨涨的。
另一头,陈墨布置完报仇计划,一清早收到宋时琰的信儿,知道司木无大碍便赶往司将军府。
陈墨见到心心念念的人,嘴里却说着谎话---司木接到个任务去了北齐,会赶上皇帝生辰宴。
打春节后司媛就没见过妹妹了,听闻妹妹又出远门做着危险的任务,低头垂眸。
司媛眸中的落寞落在陈墨心上,不禁揪了揪。十八受伤了,是他没保护好她,辜负了司媛对他的托付。
他上前揽司媛入怀,下巴轻抵在她头上,“对不起。”
司媛以为他说的是公事忙,陪她时间不多,抱住他的腰,“你们平安就好。”
“嗯~伯父,又喝醉酒了?”陈墨沉声问,嗓音低低沉沉的。
“没有,屋里睡觉呢。”
“咳咳咳。”中气十足的咳嗽声吓得司媛挣脱陈墨的怀抱,脸红红的。
陈墨握住她的手,“伯父,早上好。”
“陈墨,你这臭小子,把我小女儿弄丢了,又来我司府勾引我大女儿。”司彦一拳打在陈墨肩上。
“爹!”司媛怪自家爹爹手下没个轻重。
司彦讪讪地拍了拍拳头的灰,“哎,女大不中留咯。陈墨你是男人的话,过几日就上奏请皇帝给你们赐婚。”
“遵命,岳父大人。”陈墨弯腰深鞠躬,拱手作揖。
司媛愣住了,他是认真的?
司彦点点头,他就喜欢直爽干脆的。
“起来吧,我的兔崽子是回房睡觉了么?”
司媛抢着说,生怕由陈墨说出来爹爹又埋怨他。“爹爹,妹妹去北齐执行任务了,能赶得上皇上大寿。”
“两个女儿都比爹忙,都是大忙人。老咯,不中用咯。”司彦转身回房。
一对小情人手拉拉了许久的家常,眨眼便正午。
“媛媛,我先走了。明日再来看你。”
“好,那我不留你吃午膳了。忙去吧。”
陈墨回府躺在床上,下午要去看司木情况,现在睡下能补上一两个时辰的眠。
顾府--------
一天下来司木发着低烧,顾元宛,顾夫人轮流照顾司木。
未时,服了第两次药汤的司木悠悠转醒,可乐坏了顾夫人,没多久司木又陷入昏迷。夫人急忙叫元宛过来看看,这是怎么了。
顾元宛把着脉,“药起效了,伤势重又晕过去了。”
“元宛啊,这样一直发烧,不会留下病根吧?啊?”顾夫人抹着泪。
顾元宛也无能为力,商先生的法子已经是最好的了。
陈墨和宋时琰到了院子,听见顾夫人的哭声,急忙冲进来,“怎么了,十八怎么了?”
顾元宛安抚着母亲,“司木体温降下来了,但还是发着烧。商先生说这两天阿木会反反复复发烧,母亲担心落下病根。”
陈墨走到床榻前,看着司木,默念着:十八,对不起,是哥哥没保护好你。
宋时琰问,“至今未醒么?”
“刚刚醒过,又晕过去了。”顾元宛帮司木抹了抹汗,把毛巾洗了洗又敷在她额头上。
陈墨扯着宋时琰出了房间,“十八,情况到底怎么样?”
“不仅受伤,灵海受创,还中了毒,极其霸道的一种毒。在元宛行针时才毒发,毒拔除后,一身玄力废了。”
陈墨踉跄了几步,玄力没了对司木来说是要了她的命呀!怎会如此严重!
“性命无大碍,商先生会治好她的。”宋时琰扶住陈墨。
“知道她鲁莽,我没留心注意她。是我没保护好她,我应该早些赶到的。”陈墨一屁股坐在地上哽咽,懊悔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我不应该喝酒,应该看住她的,应该看住她的…呜呜…”一个大男人坐在地上抱头痛哭。
宋时琰静静地坐在他身旁,等他冷静下来,“她不希望你这样责怪自己的。一切都会好的。”
陈墨忽地站了起来,发了个信号,冷着脸离开。
陈墨召集红叶团的长老们商议,如何搞死南越太子。让这孙子深刻地明白司木不是他惹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