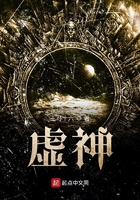今日很不愉快。
老艾瑞克回到罗盘街的住宅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本来他还想着到卫戍城去看看正在制造的连发蝎子弩,但他真的太疲惫了,甚至不想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门。
要不是城里有宵禁,不允许酒馆在十点半之后营业,他一定还会继续狂喝到天亮才肯罢休。
这时,老艾瑞克正准备要开门,却发现自家的房门竟然开着。
尽管自己喝得烂醉,但他知道,这绝不可能是房门为了照顾他喝醉酒而自己打开的。
老艾瑞克当即按住了腰间的剑,有人闯进了他的房子里来。
会是谁呢?
常年游走于宫廷乱象之间的他,对战场之外的危险向来有着敏锐的直觉。
他也不打算点灯,摸着黑,小心翼翼观察周遭。
看来不速之客并没有打算物归原样——柜子被翻倒在地,桌椅板凳像刚遭受了台风洗礼一样东倒西歪。
最令老艾瑞克心疼的是放在展柜里的高档苏维妮翁,竟然全部都被摔在了地上,漏得一滴也不剩!
老艾瑞克气得浑身发抖,假如有机会,他非得把打碎酒瓶的人按在地上,把玻璃碴子统统舔干净不可!
老艾瑞克强压怒火,屏住呼吸走上二楼的台阶,摇晃的吊灯铁链嘎吱嘎吱响,一扇打开的门挡在了走廊前。
老艾瑞克一拉开木门,眼前立刻出现了一个高大的人影!
老艾瑞克一惊,条件反射半刃出鞘顶上人影的脖子!
然而接下来却让老艾瑞克哑然失笑。
待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哪是什么不速之客,原来只是自己的盔甲架罢了。
不过话说回来,盔甲架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被搬到了走廊里来?
不对!
忽然,老艾瑞克感到寒芒在后,一阵汗毛倒起。
猛然间听到身后传来的脚步和呼吸声,紧接着冰冷刺骨的气息直逼向身后!
不好!
老艾瑞克当即以左脚为轴,颈椎如大龙盘旋,全力回身,余下的剑刃完全绽放,自左往右划出一轮半月,顺势斩破身前头盔,带着荡然剑风,狠狠地朝袭击者砍去。
敌人实力不弱,但是从接触力度来看,似乎不是成年男子的力道。
老艾瑞克手腕翻转,变横扫为斜劈,剑尖破开墙壁,压缩来袭黑影的腾挪空间。
然而袭击者脚步连退,避开老艾瑞克势大力沉的一剑,转身踏向墙壁,借力起跃。
与此同时,老艾瑞克剑尖的指向陡然一转,双手上挑,直逼对手的脖颈。
“说吧,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永远不会知道。”
刹那间,对方如雨燕般在空中舒展身姿,利剑贴脸而过——咣啷!
敌人向后腾跃空翻,前脚回旋踢中盔甲架的一侧,上面的钢铁部件立刻噼里啪啦地散落向老艾瑞克的方向。
敌人动作很灵活,看起来像个女人,戴着惨白的狂欢节假面,一身修身的皮衣反倒显得她格外迷人。
但老艾瑞克不敢掉以轻心,只见她趁着老艾瑞克躲避盔甲部件之余借力踏上墙面。
像黑猫一样横越过走廊,化作一道黑影翻过老艾瑞克的头顶,落地的时候又丢下一颗小小的铁球。
——“嘭”!
一声炸响,老艾瑞克眼前顿时烟雾弥漫。
“咳咳,你是……什么人?”不待他追问,那个女子便已消失在烟雾之中。
她逃走了。
老艾瑞克追上去的时候,剩下的只有敞开的窗户和飘动的纱帘。
那个女人早就顺着房檐,以异常惊人的平衡性飞快走过连接两栋房屋的绳索,眨眼间站在了教堂的塔尖上。
如同白色月光下凝视一切的夜莺。
她最后望了老艾瑞克一眼,便彻底变成了远方夜幕中的黑点。
老艾瑞克狠狠一拳砸向窗台。
见鬼了,她的目的是什么?
也没时间思考神秘女子的来历,他立刻就开始在房屋里四处检查被翻动过的每一个地方,他想知道对方想要找的东西是什么。
就在这时,老艾瑞克走进了伊纹的房间,他注意到床头柜上快被破坏的抽屉。
开锁的工具还落在地上。
应该是他之前突然归来,导致神秘女子来不及打开上锁的抽屉。
想到这里,老艾瑞克指尖一颤,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猜测。
他用剑柄的配重奋力砸坏铁锁,拉开抽屉。
难道说,对方的目标……会是伊纹吗?
不对……不对,她的目标,是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
此时此刻,伊纹被眼前恐怖的一幕震慑,他想起故乡老人们常常说的故事。
旧时杀人的僧侣会将尸体埋进修道院的墙壁之中,每一面巨大厚实的墙体之内可能都隐藏着一个被囚禁的亡魂。
倘若长期处于这样的墙体之下,那么活人必会被恶鬼缠身,霉运不断。
没想到,这样的场景真实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随着刽子手将墙砖一块一块封死,光明逐渐消逝,伊纹感觉自己似乎也跟着停止了呼吸。
那个染着血的白布头颅还不愿意放弃生的希望。
他看不见,却仍然看着光明消失的地方,一块一块砖,裹在蚕茧里的男人一遍一遍诅咒……
堵死、封锁,永久的黑暗降临。
伊纹浑身上下都感到了寒意,他似乎看到白布上的血迹凝结成了一个血红的眼睛。
它睁大着好像要看清这世间乱像,血块构成的眼瞳还在继续扩大,像是在转动一般。
冥冥之中,他听到有人在低声重复一个名字:“伊凡。”
伊纹头痛欲裂,觉得自己不能眼睁睁地见死不救,但又想到老艾瑞克的嘱咐,皇宫里不该管的不要管。到底该怎么办呢?
正在犹豫间,伊纹听到了身后嘈杂的脚步声。
有人来了!
幻听也在一瞬间消失,他似乎清醒了过来,恍然意识到这种情况下去救一个陌生人根本就不现实,情急之下他赶紧冲进了拐角的树墙后。
他隐隐约约感到要是再继续在这迷宫花园呆下去便会有巨大的危险,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伊纹不敢久留,朝着远方高耸的宫门小跑,好不容易找到离开花园的路。
那个被裹成蚕蛹的男人绝望的闷哼仍然阴魂不散地在伊纹耳边回响。
伊纹一刻也没有眨眼,那个被砌进围墙里的人究竟是谁?
他为什么会被人以如此残忍的手段抹杀?
伊纹边走边思考,没几步,他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伊纹阁下,你怎么在这里?”
那声音无比熟悉,伊纹手心出了汗,他缓缓回头。
果不其然。
他如同触了电一般,因为说话的人正是“章鱼爵士”庞克拉。
“我迷路了,我第一次来到皇宫。”伊纹故作镇定地说,但他的内心几乎是在呐喊——为什么他会在这?!
伊纹时刻防备着,在这夜晚人迹罕至的花园里,遇到任何人都得警惕,更何况是那个令人忌惮的庞克拉爵士呢?
“哦,我来这里散散步。”
庞克拉似乎没有敌意,只是很自然地抬头看着头顶的夜空。
“我不太喜欢人群聚集的地方。现在挺晚了,阁下,夜空下即便最熟悉之物也会变得陌生……尤其是不熟悉皇宫的人,在夜间可是真的会迷路的。”
啧啧啧,好一个“散散步”,伊纹点点头,也不知道庞克拉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对,我确实迷路了,庞克拉先生。”
“没关系,我带你离开这里。”庞克拉和蔼地笑了笑。
他背着手,在夜色中像是游方的诗人一般,碎碎念着什么,仿佛在揣测天空星座的运行轨迹,欲走未走。
然而这时,他又转头问了伊纹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啊,对了,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奇怪的声音?”伊纹心中一凛,他问这个干什么?
庞克拉像是在苦苦思索着什么一般,“嗯,对对……啊,好像是谁在用铁器敲东西?”
他一打响指,那双碧色的眼睛如同灵魂的注视,“所以,你有听到吗?”
铁器敲东西?!
伊纹的耳边霎时间回响起一个男人痛苦的闷哼。
毛骨悚然。
这似乎是在试探着什么。
伊纹不免感觉心跳加速,尽管他对自己的剑术十分自信,但他最担心的还是花园深处那些戴着刽子手面具的人。
庞克拉会跟他们是一伙的吗?
“我……”犹豫许久,伊纹最终还是回答道,“是,我听到了。也许是园丁们还在值夜班吧,我现在更需要早点回家,并不想搭理这些事情。”
“啊……对,来吧,请跟我走。”说罢,庞克拉便在前面带路,“嗯,有时候收敛住好奇心也不是不好的事情。”
起初伊纹有些担心这个家伙会故意把自己带到什么偏僻的地方去,但转念一想,皇宫还有哪里比迷宫花园更偏僻的呢?
“对了,伊纹,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参与帝国竞技呢?”
“帝国竞技?”
“对。”伊纹不知道庞克拉为何莫名提起了这个话题,“你的身手不错,也许……你会成为我的新同僚也说不定。”
伊纹没有回答,暗暗记下了庞克拉的话。
帝国竞技,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就是路德维希那家伙在宴会提到的竞赛。
最终的获胜者会成为新的“首席骑士”,掌管帝国最强大的殿军兵团。
想想的确令人心动。
眼前的道路渐渐熟悉了起来,视野变得愈发开阔,燃烧的火盆映亮了一个又一个全副武装的殿军侍卫,伊纹记得自己就是在这里看到斯坦因少爷被殿军给吼到腿软的。
路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被仆人搀扶的贵族,他们的马车都统一停在了皇宫外的街道上。
可能是因为宴会的缘故,房屋之间的绳索都挂上了风玫瑰王室的彩旗。
庞克拉说:“差不多开始了吧?”
一声尖啸划破夜空,伊纹身后的皇宫塔楼上升起了一束火焰,噼啪,噼啪,化作五彩斑斓的夜之花。
不由自主,伊纹停下了脚步,他怔怔地看着远方,它们一簇接着一簇,照亮星空,它们盛开、凋零,像无数散落的天雨,留下彩色的轨迹。
“看啊,是烟花,是烟花!”孩子们拉着他们的父母,各种各样的颜色在他们童稚的脸上交相辉映。
“是啊……有的时候,一辈子都不能看到几次。”
即便是热衷于金钱的贵族们此刻也沉醉于梦幻般的时空下,女人依靠着男人的肩膀,一向严肃的殿军侍卫们也好像在烟花里看到了人生经历过的美好。
忘掉了武器,忘掉了厮杀,至少在这短暂的一刻,世间没有杀戮,没有权谋,天下何处不太平?
灯火阑珊的街道,贵族们在星辰下翩跹起舞,宛如一幅幅典雅的画卷。
斑斓的花火将月光渲染,透过冰冷的空,一次又一次照亮画中人的面庞。
赤色闪过,那是落日的回廊,白色闪过,那是冬日的过道。
在人群之中,伊纹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女孩,她牵着父亲的手,秋风吹起她奶茶色的长发。
画前人不语,唯闻花火声,画前人不探,唯见故人影。
“爸爸……您不去看烟花吗?大家都去了。”
露娜安静地站在皇帝陛下的身边,黑色的舞裙,盛装的伊人,莫不是画中剪影,莫不是故人来寻?
皇帝惘然地仰起脸,他心中那幅画中的伊人渐渐在他的双眸中化作涟漪,映出夜空花色。
赤红的酒滴顺着酒杯滑落,在地上碎成盛开的玫瑰,如同夜空的那朵火花。
“露娜,你知道我不再看了……我已经很多年不愿再看到焰火。”皇帝哀声轻叹,眼眶微微泛红,“但……那些花火真的很美。”
“哥哥呢?妈妈呢?为什么他们不来呢?他们不喜欢这些花儿吗?”
皇帝像是没听到一样,喝尽杯中美酒,淡淡地说:“没人不喜欢焰火,人们只是哀叹她们的逝去罢了。”
露娜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她踮起高跟鞋,摸摸皇帝的头顶。
“爸爸,你要打起精神哦。”
慢慢地,伊纹越走越近。
然而她却微笑着,带着优雅的舞步,黑色长裙像涟漪散开,身影渐渐模糊在了闪烁的光影中,笑声融进花火与众人的喧嚣中……
伊纹想起了小的时候,他总是羡慕邻居家的孩子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然后默默地坐在一旁看着,因为那些不属于他。
他常常会在修道院的祈祷日,偷偷看着制皮匠的小女儿,他知道那依然不属于他。
他心里永远渴望着父亲答应过会带他去看的焰火,他只能在脑海里幻想,因为醒来才知道,从来没有任何美好的事物属于他……
他多想好好看看那些稍纵即逝的花火。
真的很美。他想用双手小心翼翼捧起它们,想要永远留住那些美丽的花儿,对着夜空轻轻一握,它们却消散了。
不免有些失望。
看到了吗?爸爸,妈妈。是焰火。
伊纹想起了鹰河城的事情,他在等他的父亲,等啊等,转眼间就是十几年。
小时候多希望自己也能像其他家的孩子那样,能够在狂欢节的时候,和爸爸妈妈坐在小木船的船头,仰望头顶绚烂的烟花。
伊纹笑着,不知不觉,一行眼泪悄然落下,被耀眼的光揉碎成五彩斑斓。
“你很喜欢烟花?”
“对。”
庞克拉长叹一声:“可惜,这种东方运来的漂亮花朵一生也就只能看到那么几次。”
“但对我来说,是永远。”伊纹不经意间回道。
“海天万顷荡漾波光浮,不见天边人影漫殊途……”
庞克拉斜靠在街灯下,竟然像是动了情地吟唱着,他想象自己在弹奏竖琴,声音虽然有些沙哑甚至可以说是难听。
但是令伊纹惊讶的是,他真真切切地饱含深情。
“一片波光里,别让歌儿愁。人事本无秋,奈何天要留。”
声音渐小,庞克拉懒洋洋地把手垂了下去,像是思索着什么。
“见笑了,这是我故乡的歌谣,我的父亲在世时常常在嘴边哼唱它……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像是漂泊海上的行者,不是吗?相比于尘世大海,我们太过渺小了,除了波涛,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大家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瞬间的绽放,我也一样。”
“嗯。”
“伊纹?”正当伊纹沉思之时,他感觉有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回首一看,那是一张少女天真的面容,在烟花下,她也变成了真正十六七岁女孩本该有的样子,她把折扇藏在自己的身后,一侧的街灯在脸上映上一层红晕,伊纹不禁怔住了。
“你是……露娜吗?”
他这才回想起来,她是路德维希皇子的妹妹,皇帝的女儿。
伸出一半的手又默默收了回去。他只不过是无父无母的孤儿罢了。
伊纹莫名感觉到胸前的白神项链在振动,他的目光渐渐从迟疑转为惊诧。
不知为何,他感觉周围的建筑在扭曲,皇宫塔楼好像变成了一棵漆黑的枯树,耳畔回响起男人垂死的闷哼,天空渗出殷红的血,焰火化成了巨大得如同月球般悬空的红眼。
“伊凡,复仇。”
猛然惊醒!露娜触碰了他的手。
她略带责备地说:“才刚见面就不记得我了吗?”
刚刚的一切仍然是幻觉。可是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过了。难道是因为今晚看到的那一幕留下了太大的阴影了吗?
伊纹低着头说:“不会。”
“怎么你一直都怪怪的?”露娜说,“爸爸喝醉了。本来哥哥说要陪我去看烟花,可是他一直一直没有出现……”
伊纹嗫嚅着双唇,很想开口告诉她之前在皇宫走廊里看到的一幕——你的父亲当时正在殴打你的哥哥和母亲。
但他不忍心伤害到这样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她会相信吗?她不能接受。
想到这里,伊纹其实也暗自叹息,她不应该看到真相。
“那,我能暂时代替你哥哥,陪你去看烟花吗?”他试探着说。
露娜微微低下头,把耳边的散发别到耳后,两汪清眸可以避开了伊纹的面庞,“你觉得呢?”
“我……我不知道,也许不行……”伊纹几乎要上气不接下气,即便是面对疾驰而来的刀锋,自己都从未像今天这样惶恐。
露娜笑笑,就好像夜风摇动银铃,她重新仰起脸,伊纹几乎能在她那碧色秋波的双瞳中看清拘谨的自己。
“现在当然不会同意。”风托起她的裙摆与万千秀发,她说,“因为,在你问我之前,我就先决定邀请你了。”
“可是……我……”伊纹扭过头,想问问身后的庞克拉,可不知怎的,身后除了其它依偎的情侣,便再无庞克拉的身影。
伊纹再回过神来,露娜白皙的左手背已经伸到了自己面前。
“你是要拒绝我吗?”她俏皮地一笑,又用左手擦着伊纹的脸,“难道是哪个粗心的女孩,把腮红都抹到你脸上去了吗?”
伊纹一惊,猛地一个后退,“我!我……怎么会!”
说着,他又缓缓挪上前,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烈火在灼烧这喉咙,蔓延到脸颊,又好像有一只沾着蜂蜜的蜜蜂狠狠地蛰了自己的心头。
那一刻,他忽然有了一个愿望,如果能成为捍卫皇家的殿军骑士,一生一世留在高廷守护她该有多好……
也许,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使君若是平家客,此夕承恩永不羞”吧?
他不记得旁人的眼光,也不记得自己的想法,他只是将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托着她的手心,伴在她身侧,走过长长的步道。
他不记得斑斓的花火,却只记住了那个同样醉人的笑靥。
如果你喜欢,我希望永远能守护你的笑,就像我想要守住曾经那些没能守住的一样,我发誓。
花火肆意燃烧,点亮夜色,在最后一丝光亮隐遁进夜幕,余响循着天边回荡。
留下的不过是人们的赞叹,和一个男孩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