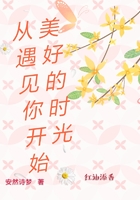那天刚放晴的天气有阴了上来,母亲就突然出现到了杨拾的宿舍门外。母亲头发都没有梳,外套应该也是随便裹得一件,北方的天冷的不成样子,她就那么瑟缩的站在门外。满脸蜡黄配上黑眼圈吓得杨拾缓了好久才分辨出来。
她的声音有点颤抖:“妈?你怎么来了。”
妈妈眼神涣散却牵强的挤出一堆笑来:“今天周六,我表妹的儿子结婚了,妈妈想着你没什么事情,就打算带你去看看。”
杨拾还没来得及说,妈妈就拉着她的手臂向外走去。
“妈,你等我收拾一下。”杨拾回头打算换件衣服,可是妈妈的手臂死死的握住她,将哭不哭的“一百,咱们走吧,快到时间了!”妈妈从出现到现在都很奇怪。杨拾张了张嘴巴又把将说的话都咽了回去。
从母亲慌张的出现她就感觉不对劲,时间越长心里就越难受,惴惴不安又无法启齿。她感觉到了胃部的一阵瑟缩,是异于不吃早饭的感觉。
慌慌张张的坐上了车,母亲就将自己围成了一团靠在车门旁,透过模糊的车窗看着外面。杨拾看着衣衫单薄的妈妈,伸手将她的手包裹起来,母亲的手很凉。当她刚触碰上去的时候,母亲下意识的甩开了她,杨拾惊愕的看着母亲,她的躲闪的眼睛。
“妈,你同我说,怎么了?”她说出来的时候,声音不自知的带了一点哭腔。
母亲似乎是含着泪的,车里开了暖气杨拾又是刚走进车子里一会儿,难免也感觉到了眼睛湿润。不,她快骗不了自己了。
母亲不说话,抱着自己来回的摇头。车子急速的驶向江城国际机场,因为是市郊在杨拾建议走高速,但是被司机否决了。
你有没有被针或者微小的刺扎到过?杨拾感觉自己被一根刺扎到了某个地方,是那种轻微的、无关紧要的、也无可奈何地疼。
母亲回绝了这个问题后还是一直在看窗外,尽管窗上蒙了一层厚厚的水雾,根本看不清外面。
杨拾低头看着手指,因为缺钙指甲并不是那么圆润光滑。
这是她听到母亲喃喃道:“你爸爸......他......有事情......我们现在要去国外住一段时间。”
可能是昨晚睡得太迟了。母亲细小的声音、今天早上的闹剧,和梦一样。不切实际甚至无聊至极。可是那个声音朦胧又真实的砸来时,杨拾感觉有什么碎了。过了好久杨拾才能明白,命运的筹码她已经输的丝毫不剩。
“爸爸到底怎么了?”
“一些小事,你知道的爸爸总是很忙又不爱说......”
“妈!我不是小孩子了。”
妈妈的眼圈红的不像样子,杨拾看来又急“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妈妈实在忍不住了,抱着杨拾嚎啕大哭起来。一个书香门第的贵气小姐,像一个粗鄙的老妇人一样,不分场合身份的哭闹。
终于了解了事情原委,杨拾像是被雷击了一样。她不敢相信以前的父亲,现在的父亲,事实的杀伤力极其惊人,把她伤的片甲不留。
父亲犯了事情,正在接受调查。
最后杨拾叫停了车,下车后就是逆向的一路狂奔,边跑边擦眼泪,她非要去问出个所以然来。
母亲也下车来追她“囡囡是要妈妈死的伐,回来吧!”说罢就缓缓的躺了下去。
多少次杨拾真希望这就是那天晚上的一场梦,这么戏剧化的事情怎么能发生?上天又怎么凭的机缘巧合轮到她的头上,但是事实就是这么无情的发生了。荒唐的闹剧就仓促的上演了,无法停止的荒唐让她疲惫的无法挣扎。
姜瀚启还在病房里躺着等待杨拾回来,病床上的粥凉了但是姜瀚启并没有喝。姜瀚启看着病房内护士来来回回、进进出出便问了她:“有没有见过一个长头发,穿着一件白色棉服的女孩走了?”
护士摇了摇头,姜瀚启便麻烦注意着一点:“那个女孩方向感不好,我怕她找不到过来的路,你看见了就把她带过来。”
但是一直到了晚上,杨拾还是没回来。姜瀚启什么都没吃躺在床上,等了杨拾整整一晚上。小护士看不下去了,就帮他在食堂买了点东西。
姜瀚启冷着脸,什么都没说把那碗放了一天的粥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