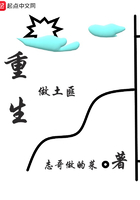傍晚,兰延陵与任清尘送蹇修离开。
蹇修的伤势仍然严重,不能握剑,武林盟便派了人护送他。
师兄弟三人牵着马在运河边散步,蹇修将湛卢剑还给兰延陵。
“大师兄,还是你拿着防身!”
蹇修叹了口气,“我现在的伤势,也不能使剑,你让我拿着它,徒增祸事?”
兰延陵吓了一跳,连忙将湛卢剑收起,“那我替大师兄保管。”
这是兰庭玉留下的剑,虽说传给了蹇修,但兰家的剑,是留给兰延陵的,自家这小师弟根本没有继承湛卢的自觉,更没有把重振父亲的盛名放在心上。
年纪还是太小。
蹇修语重心长道,“我走后,你要多听清尘的话,不要惹麻烦,知道吗?”
兰延陵点头。
三人正说话间,兰延陵注意到隔岸似乎有两个人,站在树下,也在说话。
蹇修和任清尘随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一绝代佳人立于河畔,面向一白衣男子,两人言笑晏晏,似乎很融洽的交谈着什么。
男子容姿秀美,风度翩然,温文尔雅,两人立在河畔如同入画之人。
“桃慕苏。”任清尘望着东方镜和桃慕苏,他心道这两人气质极为相似,正是大家公子哥和小姐的那等气质,此外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迷离雾气,令人难以言说。
蹇修问,“她是何人?”
任清尘努了努嘴,“小师弟的未婚妻。”
“原来就是她?”蹇修微微蹙眉,任清尘道,“正是,她就是东方家二小姐,东方镜。”
蹇修说,“她怎么跟桃慕苏在一起?”
“她是去请桃公子的。”任清尘说,“我们的小师弟对桃公子万分向往,有心结识。”他说到这里,突然问,“你这几日与桃慕苏可有交流?觉得他为人如何?”
“桃公子气度卓然,言谈举止无不博学,进退行事无不有礼,确实令人心向往之。”蹇修道,“而且此人武功修为决不在师夷风之下。”
他此言一出,兰延陵与任清尘皆面露惊骇之色,任清尘失声道,“师夷风不是号称武林第一高手吗?桃慕苏比他还厉害?”
“师夷风酷爱武学,桃慕苏身为陈金阁阁主,被花院主与岚先生赏识,住进南风院,何需摆下擂台,师夷风早已拜访过了。”蹇修负手而立,淡声道。
任清尘于是问,“师夷风挑战了桃慕苏?谁胜谁负?”
“桃慕苏没有跟他比拼武技,他说自己不长于此,却要跟师夷风下棋。”蹇修说起此事,有些揶揄,“我们这位桃公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擅于琴技。”兰延陵道,“他果然很厉害。”任清尘看了兰延陵一眼,后者眼中敬服之意更甚,任清尘问,“那大师兄怎么知道他武功修为不在师夷风之下?”
“师夷风与我提过,有一回他对桃慕苏出掌,两人一掌接实,桃慕苏身上的内功浩瀚浑厚,至少有一甲子的功力。”蹇修说。
任清尘大惊道,“一甲子?他年纪轻轻不过二十多岁,怎会有如此浩瀚的内功修为?”
“师夷风也深感奇怪,然此事无从解释。桃慕苏似乎不欲与他缠斗,一掌过后第二掌显然力道不如从前,被师夷风震伤吐血,是略逊于师夷风了。”蹇修道,“但按师夷风所言,他以为桃慕苏并未尽全力,至少应还保有三分力才是。”
“桃慕苏是故意示弱?”任清尘觉得不可理喻,在北风院见龙庭之时,他与龙庭的对话,此人并无意隐藏实力,言谈之中似有若无的自负,令人闻之惊惧。
任清尘咧嘴,坏笑起来,“既如此,师夷风那一掌使出了几成力?”
“五成。”
兰延陵瞪大眼睛,他未曾料想师夷风也隐藏了实力,高手过招果真除了实力更拼心机,若是他,定然老老实实出十成十的功力,实际上他在江州也是这么做的。
任清尘听得却是心惊,桃慕苏身上有一甲子的内功,与师夷风的五成功力接实尚且略逊一筹,那师夷风的内功修为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实在令人不敢想象。
人言师夷风专注剑术,与内力修为上稍显逊色,如今来看,这‘逊色’,也是其他人想也不想,望尘莫及的。
河畔那一男一女这会儿已经没有在说话了,东方镜缓缓来到河边,望着滔滔河水,目光沉静悠然。
一直立在桃慕苏身旁的红衣女子走到他的面前,桃慕苏似乎交代了两句话,那女子点了点头。
“那红衣女子是什么身份?”任清尘指了指,他记得这个女子叫南烛,在江州曾救过云殊,这女子也是倾国倾城之色,只是阴郁而少去笑容,终日跟在桃慕苏身后,少言寡语,只有桃慕苏跟她说话她才会回应。
“桃慕苏的随侍。”蹇修说,“叫南烛,常日跟在桃慕苏身边,这几日跟随云殊多些。”
“这女子武功修为也高于常人,我们在江州见过她。”任清尘道。
蹇修点点头。南烛常年随侍在桃慕苏身边,两人同食同寝,其中关系只怕并非只是随侍如此简单,只是这等房中之事,众侠士便是心有好奇也不好多做盘问。
东方镜远远望见了任清尘三人,冲三人招手,便要乘船往这边来,桃慕苏没有做挽留。
他将东方镜送上渡船,与少女告别。
身边的红衣女子道,“三爷,兰棠来信了。”
桃慕苏的目光随着东方镜的身影渐渐移去河边,淡声道,“什么事?”南烛望了一眼东方镜,转头道,“兰棠姐姐说,府里的事不顺遂,许多事要三爷抽空回去一趟再做决断。”桃慕苏道,“扬州的事吃紧,我如何有空回府?兰棠素来多谋善断,我不在府里时,她领着办事已有多年了,这回也依着她的意思办就是。”
南烛犹豫了片刻,桃慕苏道,“可是有掣肘之人从中作梗?”
南烛道,“他们疑心病又犯了,疑那案子是三爷从中搬弄是非……”
桃慕苏微微一笑,“原来是那件事……兰棠温柔和顺,在府中素得人心,能让她如此掣肘的……是父亲疑心我吧。”南烛没有作声,问,“三爷可要回府?”桃慕苏指尖一抬,右手食指与中指之间不知何时夹了一粒蓝田玉棋子,那棋子色泽润丽,暖玉生烟,只看成色便知是难得的宝物。
他将那粒棋子击在水面上,棋子没有马上落水,反而在水上跳跃了好几下,南烛说,“三爷……这蓝田玉棋是宝物……”
这是桃慕苏极喜欢的一副棋子,平日爱不释手,如今抛入水中,过会儿不知能不能捞的回来。
“是他送我的礼物。”桃慕苏温声说。
“他……?”南烛疑惑。
“我的朋友。”桃慕苏抚了抚额角,小声说,“他知道我喜欢这些小玩意,特意去蓝田山采来的玉石,每一颗都是他亲手打磨……三百六十一颗棋子,他磨了整整一年。”
南烛道,“……三爷从没有跟南烛提过从前的事。”
“我们……”桃慕苏顿了顿,柔声说,“相依为命,是兄弟。”桃慕苏指尖一动,又不知从哪里取出另一颗黑色的蓝田玉棋,他将那颗蓝田玉棋子捏在指尖把玩,慢慢的说,“他第一次磨得不好,我把棋子全打碎,让他重新给我磨,于是他又磨了一年,我让他反反复复磨了三次。”
南烛见他一颗一颗往河里扔棋子,问,“三爷想让朋友……再为你磨一次?”
“他永远不会再为我磨棋子了。”
“三爷……”
桃慕苏将那一幅蓝田玉棋尽数扔进河里,深吸了口气,从袖中取出一把纸扇。
“将这把扇子呈给父亲。”
南烛展开纸扇,那扇骨十分廉价,像是街上十文钱一把的普通纸扇,但扇面上墨迹未干,赫然题着一行诗。
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
桃慕苏的字,南烛已看了四五年,这扇上决然是桃慕苏的字没错,但自家三爷是何等人物……一幅字价值千金,为何要在这样一把廉价的纸扇上题字?
这上头的诗,又是什么意思?
她自然没想到这把扇子和上头的字是另外一个小姑娘送给桃慕苏的,南烛并不明白桃慕苏的意思,只是桃慕苏话已至此,显然也已不会多说,他道,“告知兰棠,不要顶撞违逆父亲的意思,他老人家年纪大了,爱折腾什么就让他折腾去,兰棠只管照顾好老祖宗,其他事不必忧心了。”
南烛道,“老爷心中怨怪三爷,却不会对三爷不利,只是若让宵小之辈翻了天去,惹了麻烦总是不好处置。”桃慕苏闻言微微一笑,“缩减府里开支,下月之前,公子小姐的月钱扣除五成,多出来的那些,尽数奖励全府上下公子小姐姨娘尽数抄写金刚经,每抄一遍,奖一两黄金。”
南烛哑口无言,“这……”桃慕苏这一招果真是够狠,公子小姐月钱被扣,花销成问题,却也不到饿死的地步,只得认真抄写经书,自是少了许多时间去寻衅滋事。
“那抄写好的经书,做什么用?”
桃慕苏略微想了想,道,“选个良辰吉日烧了,为姐姐祈福吧。”
这招数虽然阴损,却的确是解决眼下燃眉之急的好办法,她点了点头,道,“还有一事,环儿缠着兰棠姐姐,要来照顾主人。”
“不许她过来。”桃慕苏道,“我不需任何人照顾,她以为江湖是芳桃园由着她胡闹,她随便前来便是拖累我。”南烛道,“是,我这就给兰棠传信,只是环儿虽是丫鬟,你却宠她,在房里过的是千金小姐的生活,兰棠若是拗不过她……”
“兰棠若是连个环儿都看不住,这芳桃园的大丫鬟便不必做了。”桃慕苏声音柔和,语调却有些冷漠,“若是连这点事都办不好,就让她收拾东西回去继续伺候姐姐,那里事少清闲。”
南烛连忙点头,这就传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