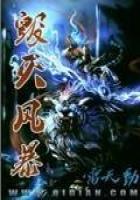魏纪一时看罢,确是难掩好奇:“你既有此信,为何不一开始就拿出来。也省得受这许多折磨。”
微澜因看着他狡黠道:“这毕竟是我最后的护身符,不到万不得已,怎么可以随便拿出?再说彼时,我根本没有可信之人。万一所有人都想谋夺我姨母家产呢。那时只怕我一旦拿出此信,反而会死的更快吧。”
微澜说着便将黑匣递给他,却将书信收进自己袖中。
看着她小心翼翼的模样,魏纪终于微笑起来。
他想了想,又不由得笑意更深。
微澜收好信,因问他说:“宗正,你预备怎么处置魏康泰与铃兰?”
他忍不住摸了摸微澜的头,却说出了一句她根本意想不到的话:“先不管他们,我们吃饭要紧。”
一时众人到齐,魏纪却不言其他,只叫左右传膳上来。大家辛苦了一日,午时也不过用了些茶点充饥,如今也的确是饥肠辘辘。魏家规矩历来是男女不同席,因此两边便各具一案默默食着。
张氏因等了一夜不见菱花,正是疑惑不解。不想此时突然叫传,她方晓得族老们今日竟全来了临园,一并连苏锦姝等人也全在宗祠处。眼瞅着举家知晓,却只单瞒了她一个,心中顿时疑窦丛生。
一想到此处,她顿时食不下咽,只恨不能立时摔了筷箸发作了才好。可偏偏族长在场,她又不能不有所顾忌,只好转过头去看苏锦姝。
不想这一看又是气不打一处来。
苏锦姝向来养尊处优,又极善日常调理。因此虽年近四旬,肌肤却仍如少女一般。再配上这一身织锦描金的正红裙衫和发上飞凤吐珠金步摇,当真是宝气氤氲,富贵清华至极。
如此看来,这做寡妇也没什么大不了。
想她这二十年来,一直忙于打理临园的日常琐事和清除魏康泰身边的莺莺燕燕,也不知道因此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一叶叶,一声声,空阶听到明。”这就是她孤枕难眠时的全部写照。
正巧此时微澜换了干净衣裙出来,王氏一见,便立时从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苏锦姝也不理会,只暗暗将自己面前的一盅桂圆红枣羹推到了她左手边。微澜心中一暖,忙努力将盏中银勺执起,慢慢食起来。
这碗热食下肚,她总算缓了口气。只是胳膊仍旧疼的厉害,初时还能勉强举起,如今已是半分都动弹不得。想到只得罪一个铃兰尚且如此,若是因此开罪于整个魏氏宗族,即使最终取胜,那也是得不偿失。
一时心中难免拿捏不定。
谁想正巧被她瞟见那香案下尚有一个青绸蒲团,她便趁势端端正正地跪下祈愿:“魏氏先祖在上,今有肖氏女微澜,幼从名师,长于深闺。然金人铁蹄之下,不得已辗转流落,其间几度生死。若非魏氏庇荫,恐早成冢中枯骨矣。今为揭露奸人,以证清白,或有迫不得已揭露过往阴私之事。先祖若在天有灵,万望宽恕。”
说完便三次叩首,并以额触地,可谓虔敬至极。
不想却有人忽在她身后轻声提醒:“过犹不及,言多必失。”
她耳上一热,立时回头看去。不想魏纪却早已走远,身后只有几位族老满含深意地审视着她。她忙深深一福道:“各位叔伯,我一介孤女,孑然一身。侥天之幸,方得托庇于魏府。可说从此魏氏荣辱,就是我之荣辱;魏氏前途,就是我之前途。因此今日在这堂中所言,我绝不会再向外透露一字。所以我也斗胆恳请,若我所言为实,请务必恕我僭越不敬之罪。”
魏纪因走过来正色道:“你但说来,是否有罪,我等自有公论。”
她欣然点头,随即便转向魏康泰:“大伯,还是烦劳您把铃兰请进来。毕竟是对质,又怎可少她一人?”
魏康泰虽然已经叮嘱过铃兰,可到底还是不放心,生怕一不小心,再把自己拖进水里。但微澜此请合情合理,他也无法公然拒绝。
铃兰最终还是被重新带了进来。
不想她性烈如火,即使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也仍旧拧着眉毛不肯服输。
微澜却不由得心生好奇,也不知当年她母亲究竟是何等风采,以至于竟然在一夕间搅动了两府风云。
一时不由轻叹:“铃兰,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其实你很像一个人。比方说你的母亲——小沈氏?”
她自然是没有答话,甚至还将脸转向了另一边。可张大娘子却忽然站了起来。她仔细打量着铃兰上下,终于有一刻,这个女子和记忆中某个花一般的面庞重合了:“你是,你莫非是沈红云的女儿?”
这的确是她母亲的名字。
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地点了点头。
这屋子里倒有一大半是认识她母亲的。因此只听得“嗡”一声,堂中便陡然热闹起来。
似乎一瞬间,所有人都开始窃窃私语,就连那些最下等的仆妇们都在偷笑着指指点点。
张氏也忽然涨红了脸。好似终于被人扒光了最后一层遮羞布,所有的骄傲与坚持顿时荡然无存。这一刻,她只恨不得杀了这里所有的人:杀了他们充满窥探的、幸灾乐祸的眼神,杀了他们对她二十多年独守空闺的肆意嘲弄。
岁月太长,她已经独自饮痛了半生。
当年,她本是定远大将军府上的四娘子。本朝重文轻武,武官地位远远不及同级的文官。可她却家学渊源,自小便爱舞刀弄剑,骑马蹴鞠更是一等一的好手。
如此勇武的女子,杭城不少人家难免望而却步。好在父亲于她儿时,就已经为她定下了一门亲事。正是她母亲的闺中好友——六安侯王氏的长子魏伯健。
魏氏家境殷实,且又有侯府庇佑,因此虽然后来提亲意外提前了一年,但她还是遵照父命,欢欢喜喜地嫁过去了。
过门后,她发现丈夫虽然生的文弱,但也白白净净地很像个读书人,心里便悄悄的有些欢喜。只是他一直都很冷淡,张四娘子起初还以为是不是自己不通文墨,所以惹人厌烦。可后来她才渐渐发现,似乎只要沈家的那个表妹一回门,他的脸上便有了笑意。
她起初也不是没有妒忌过。可这个表妹待人却极和气,说话也是轻声细语,连她谈起刀枪剑戟时也是一贯的耐心与容忍。再加上她又有孕在身,张氏便慢慢放下了戒备之心。两人因时常相约着一道绣花、踏青,关系也因此日渐亲密深厚起来。
直到一个夏日午后,她闲极无聊,便顺道拐去寒碧山庄游玩。彼时的山庄不过一座别院,只有少数洒扫的仆役。山间宁静,她便干脆以绿柳为剑,行进间随意舞弄为戏。不想刚绕过一处水湾,便远远看见前面亭瓦上有株紫藤盛放,垂坠的花枝几乎将整个亭台密密笼住,不由深以为奇。因特意止住从人脚步,自己却分花拂柳,一路行去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