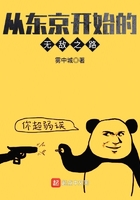第二天刚出电梯口,就看见时肆站在门外边的绿化带旁边。红色卫衣,黑色裤子,衬得气色都好了很多。
孟迁瑜拉了拉书包带子跑过去:“你好点没有,还发烧吗?”
刚准备伸手去探他额头的温度,又觉得不合适,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
时肆挑挑眉,昨天晚上不是摸得很起劲吗,怎么他就这么见不得光?
“没事。”他摇头,一开口,孟迁瑜才发现他嗓子嘶哑的厉害。
“药都吃了吗?”她问。
时肆点点头,等她跟上来之后往小区门口走。
气氛微妙。
也许是昨天晚上,夜里人的心境总是不同的吧,不然怎么一大早上就弥漫着驱散不开的尴尬。
孟迁瑜乖乖跟在他后面,时不时抬头看看两人之间的距离是否适中。其实昨天晚上从他那里回来的时候,她就有点后悔,不该那么冲动,明明前一天还当着他的面故意说了那样的话。
但是要让她任他一个人在空荡的房子里烧的晕晕乎乎不省人事,好像她也做不到。
那就当做是她出于对普通邻居和同学的善意吧,以后再有什么事,还是应该慎重。
她只希望自己昨天晚上没有露出什么马脚,让他看出她所谓的不可启齿的少女心思才好。
当然她其实是多虑了。
时肆一点没看出来,只是觉得她像个小怪物,可能脑回路跟别人不太一样。
回头看看她怎么没跟上来,四目相对,她先移开了视线。
哦懂了。
人家不是腿短跟不上来,就是单纯不想跟他隔这么近。
但是他还是不死心问了一句:“孟迁瑜?”
“啊?”她被吓了一跳。
“是不是昨天晚上换了别人你也会那样做啊。”他问。
孟迁瑜缓了一下,点点头。当然换了别人她也会这样啦,如果是姥姥生病了,或者钟棂,或者是其他很重要的人,她都会去照顾的。
时肆彻底死心了,他感觉一颗烧的通红滚烫的心被一盆冰水刺啦一声浇透了。
拔凉拔凉的。
还以为自己会有什么不同。
“要是你们班那个班长生病了呢?”他问,怎么说不能输给那个小白脸书呆子。
孟迁瑜很奇怪:“班长不住我们小区啊,而且他身体很好的,没见过他生病的。”
时肆疯了。怎么她这个意思,要是班长住那个小区她还就送了?还不生病,身体好?什么鬼几把玩意儿,他身体不好吗?
他看那个什么劳什子班长,就是小时候龙牡壮骨颗粒喝多了,还不生病,她当他是谁啊,金刚不败之躯百毒不侵之体???
迷。
人哪有不生病的,他不生病,说明他不是个人。
这么想着,果然心里平衡了许多。
孟迁瑜是搞不懂他怎么一会儿浪得不行一会儿愁的要死,哦对了,钟棂说了,时肆拿过物理竞赛一等奖的。
物理那种东西都能看懂,那他估计跟普通人不一样吧,反正高一分科的时候要不是物理只考了六十分她也不至于一意孤行选文科。来了文科才知道,还有个比物理更不好收拾的地理历史。
一想到第一节课就是历史,而且昨天晚上的卷子历史选择题错了好几个,她就愁的不行。
时肆听到后面刷刷的声音,回头看了一眼,这孩子真拿了张卷子边走边看。
他算是懂了,孟迁瑜是真的属于对学习很认真的那种,拿出了忧国忧民的心境来看卷子。
但是认真归认真,过马路还是要稍微看一下路吧。
他一把拉住了差点一脚踏出去就闯了红灯跟送外卖的小哥来个亲密接触的孟迁瑜,凶着一张脸教训她:“看路!”
孟迁瑜蒙了一会,才抬头看他,说“好”。
真是要被她气死,怎么就不能让他省点心呢这死孩子。
撇过头去看了一眼,发现是文综卷子。
孟迁瑜刚看的应该是历史题,反正那一片错的最多。
仔细看了看题目,他自己都要笑死了,这么明显的材料分析题,他一个理科的都看懂了。
她是怎么想的,还能选个最离谱的,这么些年文科白读了真的是。
算了,看在她昨天晚上给他送药端粥的份上,就让他这位大仙勉强屈尊,略施仙力,给这颗榆木疙瘩脑袋开个光吧。
所以那天一中的学生就看到了罕见的一幕,一中门口,门卫室旁边的小花坛旁边,时肆拿着一张卷子在给一个女生讲题目。
所有从前门走进学校,并且有幸看见了这帧名场面的人都在试图找一个科学且可靠的说法解释这种实在是见了鬼的现象。
磁场错乱?基因突变?还有什么前沿性的科学研究成果都拿出来试试,能对上一个是一个啊。
并且,时肆那个鬼语气,竟然出奇的像极了在讲台上讲的唾沫子直飞恨不能当场给她们每人头上安个定时炸弹,那个再说听不懂就直接让他炸了。
“你看材料啊,那个A和B明显跟材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都不知道AB是对的还是错的你也敢选?你为什么不选D 啊?”这是大佬逼近抓狂边缘的声音。
“AB是对的”回答的是个很小而且很笃定的声音,然后声音更小了,“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是对的。”
时肆差点让她给气笑了:“你这是考什么呢,考历史还是考历史书呢?”
孟迁瑜还在反驳,并且觉得自己是有理的那一方:“但是D就算跟材料有关,那如果材料有问题呢,它本来也就不是主流观点啊。”
时肆想了一会说:“人家在题目里给了你材料,就是要你提取信息的,D不是主流观点,但是它不是错到违背具体事实可以被直接排除的选项。即便只有一小部分人坚持这种观点,但是它有材料论证,那么起码在这则材料下,它是对的。”
孟迁瑜又看了两遍题目,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时肆观察着她的反应:“懂了吗?”
孟迁瑜点点头:“懂了。”
不得了不得了,理科竞赛大佬在给文科前三十讲历史题,还让人家听懂了。
孟迁瑜有点失落,他好像总是能接受一些新的观点,也敢于去质疑一些成为了权威的东西。明明自己才是正儿八经的文科生,但是他刚刚那句话,她完全找不到反驳的点。
时肆又把卷子翻了个面:“剩下的两题也都是类似的问题,你是对教材依赖性太严重了。”
孟迁瑜点点头。
他对她笑了一下:“回教室吧,早自习快开始了。”
孟迁瑜看呆了,但是马上反应过来,不能太痴汉,他会发现的。
当然她这副表情,在时肆眼里,那就是学渣对学霸单纯的崇拜。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聪明,看来以后要多多施展,不然太过隐藏实力也不太好。
历史地理也不难吗,他准备去找两本教材看看,方便在这个傻子面前树立他高大威猛睿智过人的形象。
至于为什么要树立这种形象,他自己也没太搞懂,但是管他的呢。
好不容易有能再孟迁瑜面前显摆自己的机会,这个逼,他是装定了。
时肆在楼梯口目送着孟迁瑜回了教室,那个心情啊,就像含泪把孩子送进监狱的老父亲——
不好意思说错了——
像是含泪把孩子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老父亲。
是的,你没有看错。
对于时肆来讲,整个高三十二班的生存环境哦不,学习,学习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你想啊,有个神里神经的班主任,一天天那个嘴跟机关枪似的,稍微不注意就要被他那个眼神凌迟八百遍。还有他们班那个班长,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也不知道觊觎他们家闺女多久了,反正他看着就像是个天天盘算着些阴谋诡计的小人,而且长得太白了,这个,嗯,反光,刺到他们家闺女学习就不好了。还有杜衡,一天天跟个二五八万似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玩意儿,追个妹子磨磨唧唧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动静,哦对还有那个钟棂,嗓门有点大,把他们家孟迁瑜带坏了就不好了。
总之呢,现在他整个人都散发着慈父的光芒,每天都得提防着,,告诫自己,这么好的孩子千万不能给带偏了。
回了教室时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范毅泽从他身上扒拉开:“你有病是吧你,有病抓紧治。”
范毅泽腆着个狗鼻子在他身上嗅了嗅,翘起兰花指,语气及其做作:“哦,天哪,女人的味道~”。
得,这是戏精上身了。怎么就没有人来发现这颗好苗子早点圆了人家的银屏电影梦呢。
时肆揉了揉鼻梁,在心里一遍遍告诉自己——
杀人犯法。
杀人犯法。
杀人犯法。
范毅泽一脸欠抽的表情:“昨天晚上,怎么样?”
时肆挑挑眉:昨天晚上?孟迁瑜?他怎么知道的?
不对,转念一想,他想问的应该是舒心瞳。
不提这事儿也就罢了,他还能晚点要他的狗命,既然这一大早上就自己收拾的油光水凉的往枪口上撞,那他也不介意送他一程。
管他妈什么杀人犯法,直接给他判刑吧。
范毅泽几乎是在时肆捏住他下巴的时候就怂了,下一秒就被干净利落的来了个过肩摔。那一声反应有点迟钝的“大侠饶命”愣是堵在了嗓子里。
背部着地的时候还在想,虽然这是他先招惹的人家吧——
但是尼玛能换个地儿吗!讲台上过肩摔!他不要面子的吗!
重点是他现在还起不来了。
真的是丢人丢到家了。
楼下班班主任听到平底一声闷雷,皱了皱眉:“来不要管楼上啊,我们把主观题抓紧时间讲一下……”
第二节课课间,范毅泽拖着两节课过去仍然不太灵便的左腿挪到了时肆的课桌旁。
怎么今天转型了?认真学习不睡觉了?
他凑过去看了一眼摊开的书本:“第六章,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
兢兢战战的开口:“大哥,咱们这,专业不对口吧……”
时肆看了一眼他的腿,还有点骄傲:“你他妈懂个屁,天才都是跨界的。”
说完特意安慰了一下他的腿。
范毅泽被他那个笑吓到了:“是是是,您说的对。”
跨界?扯蛋吗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