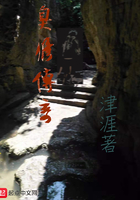风吹走了最后一片阻挡阳光的云。太阳渗出的血丝,汇聚成细流,倾倒在了这一片土地上。
龙韬——这位有着二百六十三年历史的帝国的最后一位国君——茫然地站在都城的城楼上。夕阳把他的脸庞映成金黄,上面有一丝不常见的惶惑与悲凉。他的发丝被吹起,在斜阳的余晖中,闪着黯淡的金光,像他布满尘土的龙袍一样。充溢血丝的眼中,曾经也闪耀着希望与复仇的火光,但,这都已是过往。
过去的岁月?龙韬想起了自己的一生。他仿佛就是为政治而生。最可悲的是,他有他先祖的雄才大略,也有他先祖的宏伟梦想,却没有他先祖那个时代的文臣和武将。他有什么?一个烂摊子。一个由一个个供奉在太庙里,他不敢言甚至也不敢怒的人给他留下的烂摊子。他也曾是一代英君,曾幻想过能够英雄造时势,可毕竟还是时势造英雄。独木难支。他本清澈的跳动着火花的眸子,见证了这一伟大帝国从最后一个落败走向最后一个辉煌。他的亲力亲为也曾让他心爱的国家摇摇晃晃地从垂死的卧榻上站起,以满头的青丝到夹杂着白发为代价。但,这苦心经营的一切,这虚幻的大梦,已被无情而又强大的现实所彻底击毁。一切都过去了。顺着他孤独的目光,已不再有人烟阜盛的市镇,不再有盔明甲亮的行伍,只是残破不堪的城墙,漫山遍野的敌军,还有血,和尸体。
鼓衰。力尽。矢竭。弦绝。
大漠。荒草。碧血。残阳。
山河依旧。生民破落。
风有点大起来了。
他摇了摇头,轻轻叹了口气,对周围最后的近卫士兵和侍从,也仿佛对自己说:“若有来生,必不生在帝王家。”
“破城之时,我允许你们任何人投降。
“你们为祖国付出了一切,祖国不怪你们。”
龙韬喃喃道:“至于我——我,血不流干……死不休战。”
最后的时刻——还是到了。
南城门徐徐打开,城中华盖节钺突出,敌军正欲上前,但见一将金盔金甲,龙驹长枪,从众军阵中过,如入无人之境。
望风而靡。
残阳,凝血。
《胤史》载:悼烈帝十八年,敌军围都甚急,帝自奋威突固,所乘马为流矢所中。帝下马掣剑,杀十数人,被伤数处,力竭,乃大呼自刎于军中。敌将陆章怜其勇,命以帝王礼葬,划千户之地以尽其祀。胤及于此,传二百四十七年,历九世,亡。
龙韬太老了。他已经老到熬不到他的对手死去,老到看不到他的祖国振兴。一个迟暮的老者,凭一己之力,拖着一个国家蹒跚前行。现在他累了,他所能做的,不过是亲手杀掉几个敌人,换取敌人一丝怜悯般的尊重。
龙韬驾崩了,带着他的文治武功,带着他的千秋大梦,这一切救不了一个国家,也救不了一个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国君。
一个积贫积弱的政府最危险的时刻,是它企图变革的时刻。龙韬没挺过这一关,他的祖国也没有。因为他,他心爱的帝国彻底躺在了废墟上。
月光,还在无边的黑暗中挣扎。可夕阳,已渐渐地落下去了。
“我们决不投降!”
“君主与国家共存亡!”
夕阳让龙韬想起了很多:好多好多年以前,他的先祖,也是庙号里唯一一个冠以太祖称谓的,龙若,也曾面对这夕阳,第一次掣出了他的长剑。
这是——夕阳,无上的荣光。
残垣上的月亮的清辉,照耀着这支孤独的送葬队伍。他们葬送了一位伟大的君主,葬送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葬送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葬送了一个伟大的传奇。
陆章想起了一首古老的歌曲:“……如果我们的将军将我们抛弃,如果我们再也回不到故乡,如果长矛穿透了我们的胸膛,如果我们在劫难逃。那么至少,我们的名字会被后人记住,我们残破的城墙,会给我们最后的坟墓。”
夏天已经快要过去了,最后一只秋蝉在一棵仍旧茂盛的大树上哀鸣,仿佛在哭泣它迟暮的生命,也仿佛在哭泣它的同伴,或者是那个夏天。
螳螂的镰刀终结了它的悲哀。它跳到蝉身旁,准备享受它在这个夏天的最后一次盛宴。
当然,树上的黄雀并没有让那只埋伏已久的螳螂吃完它最后的晚餐。
黄雀的扑棱振动了树梢,茂密的树冠下,一片略泛黄的叶子,脱离了树枝,被西风吹上了无尽的黑暗。
秋天,还是到了。
历史仿佛回到了二百五十三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