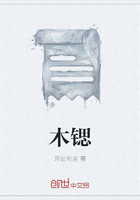高淳语总体来讲是属于“吴语”系列,但我总感觉到与“苏、锡、常”不同,有点更近“上海腔”(我指的是“山乡”音,“圩乡”那边我不太熟悉,不好乱“想当然”)。照说我父母都是“吴语区”人,耳濡目染,加上我有过多次去过“苏锡常”经历,我应更能听懂高淳话,半年多近一年的日子,我仍分辩不出个“赵钱孙李、子丑寅卯”来。尽管如此,各宗祠请来唱“社戏”的无一不是“黄眉戏”班(我仍指“山乡”,“圩乡”什么风俗不知道,也没有兴趣考证),“黄眉”虽然属于湖北省,但唱戏的却是安徽芜湖那段人,心智比一般人高的“韦小娥”应该更容易吸收到“外邦”腔。
谈了一会话,也是什么“父母还好”“家里有几口人”之类的“营养话”,可以说是“没话找话讲”。我说过,那时我们都不抽烟,不懂爱惜,刚抽了几口的烟就丢掉大半踩灭,不象“生伢尼”吸到烟头最后一口还用手捧着吸,是那种完全没有想烟蒂地作派。看着眼前地“狼狈”,于是我们“顺理成章”再各敬了一根烟。“生伢尼”抓过烟就吸,不象“韦小娥”优雅地将新烟揉松,连接上旧烟再吸,仿佛如“大家闺秀”那样细作温柔,全不似我家门口吸烟女翘着小姆指夹烟那样“拉风”,但在我看来,那只是“婉悦派”和“豪放派”之间的各有所长。
通过那次交谈,我总感到“韦小娥”身上存在一种不经意的与众不同的“神秘”,让人不愿也不敢接近,这当然仅是我个人感受,从没与人谈起过。相比当时乡人,“韦小娥”可是说是“博学”的,当然全是“夫子”不论的“鬼神”类杂说;她还约懂“医理”,乡人碰到象蛇虫咬伤定是求到她门上,遇上头昏脑热、跑肚拉稀到她这里也能解决问题,用的无非田头地边的草草棒棒。过去乡人意识,总是“医”“巫”不分的,我就亲眼见过几个小脚老太太当着面在我土墙上贴过“天灵灵,地灵灵,我家有个夜哭郞,过路君子读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治小儿夜哭“仙方”。我不知道“韦小娥”这些“博学”是“家学渊源”,还是“无师之通”,但定然不会出之“黄帝内经”或“麻衣神相”,鉴于“韦小娥”“精灵”,乡人也有人窃窃过说是“黄大仙”附身,所以我认定“无师之通”的成分大一点。关于什么时候成为方圆几里闻名“神婆”,我就搞不清了,应该是七十年代初“生伢尼”不再担任“贫农代表”以后的事。
我们初到村上,“生伢尼”家房子在村中一间草房,就在队长家旁边,我们住的“小队屋”隔着“金头”家而建,和队长家垫了土的泥墙瓦屋相比显出小来,更不能与后面“金头”家砖墙青瓦相论,越加寒酸。“生伢尼”房子与众不同,是呈英文“L”形,竖的一头是两间卧室,开大门是外室,放些桌子、板凳,纺车等物,里间并排放了两张竹床,上面都支有蚊帐防灰尘。这也是当时乡人普通摆设,只不过根据各家条件,床的档次不同。考较一点是雕花木床,就是在做好的木板床加上一个外框,用于支撑蚊帐,床的正面贴一转用薄木板刻些象征“花鸟鱼虫”的镂空画,(我看过的村上花床极为普通,镂空画风格象极了“抽象派”画家的作品,让人不知所云),其实关于“雕花床”仿佛一些“博物馆”有陈列展出,那些都是精品极品版的,乡人这些仅是“山寨版”而已。关于谈到“雕花床”,我觉得应补充一点,其实家里配有“雕花床”不仅是经济条件限制,还需要夫妻是原配的,因为床、箱子、包括床前的踏板均是“新娘”的“陪嫁”,所以也有准备娶“穷”姑娘又想要面子的,事先将陪嫁物品送去岳父母家,结婚时再“风光”抬回,比如“嫂子”。“韦小娥”不属此例,一个“穷”字阻挡了一切,她的家没有“雕花床”。连接的“L”是一间厨房,厨房相对较大,除了灶外,也放些柴草,砌了个鸡笼,乡人那时很少养猪,仅是靠养几只鸡换点“灯油”、“针头线脑”,那时市面上鸡蛋是七分,但只能是“供销社”专卖,乡人都是到较大的旁边村小店兑换,鸡蛋是六分,所以我们七分钱买他们一个鸡蛋乡人都是很开心的。
之从那次拜访过“生伢尼”家后,我们极少再去,道是队长家、“嫩伢”家、少青家我们是常客,每次路过“生伢尼”家门口总见到“韦小娥”坐在门边专心纺纱,或拿起旱烟杆抽上两口。见到我们,总是热情让我们进家门坐坐,也总是被我们“婉转”拒绝,我并没有“嫌贫爱富”的“狗眼”,只是见到她心里总有一种“忐忑的惶恐”,就象站在寺庙前一般,“阴森鬼气”附着全身,“巫”真有这么大能量吗?
七零年上半年,麦收之前,“生伢尼”在村后盖了一大间草房,建房时,我去看过,为五大间,屋内地面也垫高了土,但仍为土墙草顶,只是外形比其他乡人房子高大了许多,快赶上“金头”家的高度。那以后,村里经常有拿着东西的“陌生人”进出。和邻村相比,“前严村”相对闭塞,一般去往何处也不会走到村上,乡人们对来村的“陌生人”视如不见,尽量绕开,心存忌讳。那段日子,我看见“生伢尼”抽起了纸烟,有时也会有“飞马”“南京”这种好一些品牌,见到我们有时也会敬给我们一只,但都被我们拒绝了。
放回来的“韦小娥”并没有“走下神坛”,“陌生人”继续来村里走动,是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半推半就的“力量”让“韦小娥”仍旧坐在神坛上久久不能离去。“少青”那次突然昏迷后,被人叫去的“韦小娥”尽管嘴里“絮絮叨叨”的不知所云,但手上一刻没停,用缝衣针将“少青”十个手指、脚指刺出血来,并在“少青”的“人中穴”、“太阳穴”等处不断挤压、按摩,直到“少青”醒来才停止。
下放时,我看过我姐姐买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上面就有“针刺”急救的方法,这有“科学”论证的,但“韦小娥”嘴里“絮絮叨叨”“咒语”不知是什么意思,是否是“医”“巫”结合,就象后来人们提倡的“中西医”结合一样?
八九年,小黑皮儿子结婚,我到村上还见到“生伢尼”,给他一包“阿诗玛”,他很开心,问到“珍宝乌卖”时,“生伢尼”说她身体还好,能自己种点小菜吃吃。因为我是抽空从单位请假出来的,时间很紧,不可能到各家串门,所以再也没去过他家。
“韦小娥”在我印象里还是那个坐在土屋门边纺纱、不时拿起身边旱烟抽上几口的看到我们总是热情打招呼的中年女人。
几天写下来搞的我迷迷糊糊的,总分不清乡人逝去的和活着的,总会想起各自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的活在眼前,并不断湧现。我的一九六八年,我的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