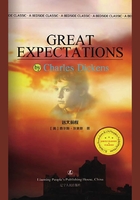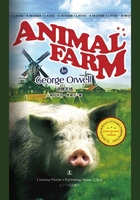王穷通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吐了一口唾沫:“近距离被空包弹射击的滋味,我总算尝到了,这趟没白来,只可惜了这身衣服。”
吴论一看,只见他的肩膀上有一大块黄色的污渍,原来这次用的是染色弹。
孙祥的声音在广播中再次响起:“刚才忘了说了,身中五发子弹当即淘汰。”今夜月光极淡,屋外的黑暗浓的像化不开的墨汁,众人不敢走门,只能从窗户跳出来。这时教室后方响起了密集冲锋的号令,枪声和叫嚷声充塞着每个人的双耳,不知有多少人正在追击他们。这声音忽大忽小,仿佛有人一直在调节音量,吴论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今夜海边的风大得异乎寻常,连海滩上的沙粒都被吹得四处乱跳。
大家只能没命似得乱跑一气,很快就跑散了,但不管他们跑的有多快,子弹似乎都在紧追着他们。好不容易到了岸边,借着微弱的月光,吴论看见冲锋舟散乱地躺在沙滩上,被不时袭上海岸的浪花击打着,张若谷抓起几件泛着荧光的救生衣,火速扔给身边的人,道:“赶紧上船。”此时突然有道黑影被海浪卷着送到了他们面前,海水一退,只见6个人在海滩上东倒西歪地趴着,一只冲锋舟像王八盖儿似的翻在一边。
“这浪……也太大了……”郭来四发出一声感叹。
吴论从小就不喜欢上语文课,尤其是佶屈聱牙的古文,一看就头疼,可他对中学课本里那句“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印象一直很深,此时才算见识到了什么是风浪的愤怒,陆续有人上了冲锋舟,可船桨尚未握稳,就被海浪轻而易举地摔了回来。
“知道这叫什么吗?”郭来四扔了船桨,叹道:“mission impossible。”
刚才跑散的众人此时已不由自主地聚拢在了一起,多半都被海水浸湿了全身,在深夜透骨的凉意中打着哆嗦。四十几双眼睛都看着王穷通,这是个一向是最有主意的人,可他抓了抓湿乎乎地头发,半天才说道:“无动力冲锋舟的破浪航行,在正常气象条件下都极耗体力,现在这个风速,摆明了是不给我们活路,只能等风浪小一点儿的时候再出发。”
话音刚落,一阵枪声透着风刺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顷刻间有六七人身上染了一大片黄。王穷通喝道:“赶紧散开!每个人的间隔都要拉开!”众人只能像丧家犬似的沿着海岸线分散跑开。
或许是因为追击兵力规模有限,当这四十五人在岸边相互之间的距离拉开到了一百米时,身后的枪声开始变得稀稀落落,仿佛铁锅里爆起的油花。但遍布基地的广播此时又突然响起,每一两分钟就会报出一个数字:
“44……43……42……”
这些数字显然意味着,有人正在被子弹淘汰出局。
吴论喘着粗气,不知广播中的信息是真是假,只听几百米开外再次响起了王穷通声嘶力竭的吼叫:“大家快把救生衣脱了!”
是了,救生衣上的荧光把大家都变成了活靶子。长长的海岸线上,王穷通的嘶吼接力似的被每个人传递,沙滩上又恢复了完全的黑暗。
广播中的数字停止了,孙祥古怪的笑声突然出现:“可以,反应挺快,不过我说了三点前必须离岸。”
吴论心想,吹什么牛逼,难不成你在每个人身上都安了闹钟,一到三点自动报警不成?
海浪丝毫没有减弱的征兆,风浪的声音逐渐变形,沉闷中夹杂着奇怪的兽吼和鬼哭,甚至隐隐有刀兵之声,仿佛有一只海底军队即将借浪登岸。
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吴论抬眼一看,海岸线同时有几处起了浓浓的雾。
咳嗽声很快变得密集,吴论知道咳嗽能传染,却不知为什么每个人的咳嗽都仿佛要了命似的,直到那团烟雾终于随着海风钻进了自己的鼻孔,眼泪鼻涕完全不受控制地一起涌出,才明白追击部队正在不停地朝各个方向狂扔催泪弹。不一会儿,广播又恢复了数字通报,显然,咳嗽声为子弹指引了目标。
一分钟,两分钟,催泪弹发出的烟雾越来越浓,吴论匍匐在沙滩上,感觉自己的胸口被慢慢烧干,咳嗽完全抑制不住,甚至能意识到自己吐出的痰中有多少条血丝,记得小时候看《红岩》,经常出现给人灌辣椒水的刑罚,他还觉得不就是辣么,自己一定能挺得过去,可被这高浓度的催泪烟雾呛了几分钟,他已是生不如死了。
先是响起了扑通扑通的声音,是有人受不了跳进了海里,但血肉之躯在恶浪面前显然不堪一击,刚下了水,他们很快又被冲回到了沙滩上,连水下闭气的机会都得不到。紧接着,又有几团黑影离了岸,显然是准备再次乘舟入海,放手一搏,可刚才折腾了这么久,风浪丝毫未减,众人的精力已折了大半,失败是注定的,被冲回来的人仿佛死了似的,趴在岸上一动不动,连咳嗽的力气都没了。
“我退出……”
之前的热身阶段,每个退出的人要么慷慨激昂,要么怒形于色,可这声“退出”是如此的无力和虚弱,与其说是自由选择,倒不如说是举手投降。
王穷通仍像第一次一样,喊了声“不能退!”可他此时的制止也显得底气不足了。没有被催泪弹折腾过的人,无法明白这些烟雾对人的意志力有多大的消耗,所以,在镇压游行示威时,它是比高压水枪和橡皮子弹更有用的利器。
一旦有人开了头,这投降的意志像咳嗽一样,很快沿着海岸线接力传染,广播冷冰冰地一口一口吐出数字,五分钟后,只剩下了25人。
这25人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在坚持着什么。
没有人会想到,这些在前五天不眠不休咬牙挺到现在的硬汉们,居然被小小的催泪弹淘汰了这么多。吴论的手紧紧握住一把沙子,感受到沙粒在指间慢慢溢出,又立马抓起一团。催泪弹呲呲的声音仍不绝于耳,烟雾的浓度已经到了一个极限,能见度几乎为零。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臂,是张若谷。就算近在咫尺,他也看不太清张若谷的脸,只能感受对方抓握的力量,这力量是在说:“拼了。”
他突然想起张若谷为什么不去洗那个热水澡。刚刚退出的二十人,其实不是败给了风浪和催泪弹,而是败给了这几天中仅有的一次舒服。
极度疲累后的舒服最为致命,他将永远记住这一点。
“高浓度的催泪烟雾……有致死的可能。”郭来四的声音也出现在了耳畔。不知何时,他们这一组聚拢在了一起。
又过了一分钟,吴论感觉空气中已没有了多少氧气,意识在渐渐模糊。幸好,强劲的海风有时还能将局部的烟雾吹散一些,让他们能偶尔缓口气。
“还剩10分钟。”孙祥的声音像下达死刑判决:“你们不要以为靠死撑就能熬过去,一会儿呛晕了上了担架,也是退出。”
这是完完全全的绝境,前方是吞噬一切的巨浪,后方是荷枪实弹的追兵,自己则在痛苦的折磨中如待宰羔羊般引颈就戮。
“咱们退吗?”吴论使劲迸出了这几个字。
“贿赂的事……没解决,我绝不会退……”张若谷断断续续地说。
吴论想你这又是何苦。
“真是个书呆子。”郭来四道:“就算……你要……整死我……在这儿……趴着……有什么用?要我说,倒不如往回冲,跟他们拼了……痛快……”
“说得……轻巧。”王穷通的声音也出现了,吴论这才发现,因为自己匍匐的位置处于沙滩的突出部,烟雾被海风略微冲散了一些,剩下的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向自己靠拢。
“你刚才听到……枪声……人声……少说也有五十几号人……回去……是送死……”
“妈的受不了了。”又有人喊了声退出。这次投降发生在身边,对每个人都是沉重的打击。
而这次连王穷通都无力制止了。
子弹又一次追了过来,这一次被打中的人都无力再动了。
等等,枪声?
吴论思索着王穷通的话,刚才半小时内身后的枪声人声开始在脑内回放,又很快变成了一张声音波形图。图中的波峰波谷有规律地出现着,整齐地不可思议。
“你说的对……”吴论握住了郭来四,后者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
“王班长……我们回去跟他们拼了……敌人人数没……那么多。”
王穷通道:“新兵蛋子……瞎几把出主意,没看见……风浪小了吗……”
风浪确实比之前略弱,但此时已无人再有勇气和精力踏入海中。
张若谷抬起头来,再一次握住吴论的手臂:“你是说……敌人可能是……鬼魅部队……”
鬼魅部队是二战中由录音师、画家组成的部队,他们通过播放录制好的武器声,制作模型坦克,佯装出比实际人数多得多的兵力,以此牵制住敌人的主力,这支部队甚至在诺曼底登陆前夕都对纳粹德国的国防军造成了严重的欺骗和干扰,但到了战后,由于故事过于离奇,一直无人相信他们的存在,直到80年代鬼魅部队的幸存者出了详细的回忆录,才造成了军事学界的极大轰动。
此时此刻,除了吴论,没人能听懂张若谷在说什么。吴论朝他点了点头,但心知此时已无法再跟别人解释,他站了起来,喊道:“你们……愿意等死……是你们的事,我……走也要……走个痛快!”
身心俱疲之下,这句话的感染力超过了一切。众人都想,哪怕是退出前能捉住一两个雪狐,猛揍一顿,也算是没白受这份罪。
除了王穷通,剩下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郭来四喊道:“咱们……兵分三路往回跑……他们子弹再多也……不能把我们……全干掉。”
离开了王穷通,他就是资格最老的兵,哪怕他再不靠谱,也胜过无人指挥。众人很快向三个方向同时跑去。当有人从烟雾中露头的一刹那,对方不再扔出催泪弹,密集的枪声再次响起。
吴论很快染上了一身黄,从远处射击的空包弹打在人身上没有什么痛觉,但直觉告诉他短短这么一会儿他身上早就不止中了五弹,但他此时也不再顾忌,带着刚刚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振奋,一路向枪声发出的位置跑去。跑到接近教室的时候,刚刚分开的众人又聚拢在了一起,每个人都成了完完全全的小黄人,仿佛均匀地涂上了一层油漆。
教室门前,孙祥和陈雪枫各拿着一把95,笑意盈盈地站着,他们的身边,是刚刚退出的二十余人,每个人都在尽量躲避他们的目光。
“难道只有你们俩?”吴论愣在原地,虽然已经料到敌人的人数非常少,但仍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郭来四竖起大拇指:“雪狐的枪法,我服,恶心人的手段,我更服。不过……弟兄们,咱们不能打女人,冤有头债有主,大家一起上,跟孙教官领教领教特种兵是怎么一个人单挑二十个的。”
“没个逼数了。”孙祥哈哈大笑,用脚踢了踢地上的一堆黑色物件,拿着对讲机道:“第二关,判断敌人佯装兵力,剩24人。”
“按计划,继续进行。”方鹤洲回道。
“不是说中五弹就淘汰吗?”王穷通此时也已跑了过来。
“那条作废。”孙祥又一次踢了踢脚下的黑物,看了下表:“不过,三点前离岸的规定不能废,现在还剩三分钟,赶紧去吧。”
吴论这才发现,他一直踢着的是冲锋舟的发动机。
这些发动机从一开始就在等待着他们,那刚刚淘汰的21人死死地盯着这些黑家伙,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