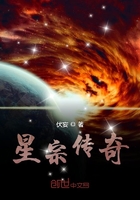文书满头大汗,在营部找到了刚开完会的董振俊。
“连长,不好了,王排长跟四班长闹起来了。”
董振俊吸了口烟,问道:“怎么,打起来了吗?”
“没,没有,被一班长和二班长拉开了。”
“哦,知道了,你先回去问问指导员要不要开支委会研究,我还要找营长谈点事。”
“您不回去看看吗?”
“又没打起来,有什么好看的?赶紧回去吧。”
董振俊是从战士提干的,入伍已经十年。打从新兵起,他接触过的排长几乎没有不跟班长干架的,唯一一个没干起来的,是个考军校分下来的八一队篮球替补队员,一米九几的个子,杵在那儿跟个铁塔似的,没人敢跟他干,其他的或赢或输,但几乎出不了事。排长毕竟是军官,即便热血上脑,做事一般都得考虑影响,真要豁出去干了,班长们就算再看不起或看不惯,毕竟经验丰富,下手也有分寸。
听文书说俩人没打起来,他是失望大于轻松。虽然部队一直讲官兵友爱文明带兵,但是个人就明白,让一帮二十来岁、精力旺盛到无处发泄的小伙子朝夕相处,哪有不打架的呢?再讲纪律,讲作风,也没法完全扼制住男人的本性。他自己上高中的时候,没事就喜欢欺负欺负人,打打架,也没什么理由,就觉得隔段时间不干一架心里就不痛快。到了部队,他是新兵连第一个敢跟班长动手的,虽然结果是七八个班长一起痛揍了他一顿,但他到了也没认错,博了个硬骨头的名声,当时连长还背地里夸过他,说这小子有种。后来当班长、当排长,他也是一路的刀光剑影,直到有一天,他准备跟一个不好好训练的痞子兵动手,刚握紧拳头突然发现自己的怒气无影无踪,这才明白,能让男人不选择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不是什么批评教育谈心引导,而是年龄。
董振俊推开门,徐宏彬正捧着杯热茶慢悠悠地喝,面前摊了张报纸,人却是放空的。他一眼瞥见旁边的茶叶罐子,眼神意味深长:“呦,金骏眉,你老兄很注重生活品质啊。”
徐宏彬回过神来,笑道:“哪的话,这罐茶还是两年前从老丈人那儿顺的,茶喝完了,罐子没舍得扔,现在只装些茉莉花茶之类的便宜货,你要,尽管拿去。”
董振俊说:“你这罐茶倒让我想起当初新任连长时我办公室那只烟灰缸。”
“怎么说?”
“当连长第三天,团里赵政委来连队检查,看了宿舍、炊事班、车库,一路点头满意。到办公室,给他敬根烟,老赵多大的烟瘾,早上睁开眼点第一根,到晚上睡觉都不用打火机续火,你猜怎么着,在办公室跟我谈了半个小时,愣是没抽。”
“烟次?还是烟缸不干净?”
“以老赵的水平,再次的烟他都能抽得两胁生风,何况我还有点存货,领导来了都是中华苏烟。他回去之后跟军务股长说,小董总体表现不错,但艰苦朴素的作风还是要再抓一抓。我一寻思,没干过什么奢侈浪费的事啊,回办公室一看才发现,烟灰缸买大了。也是我自己粗,前任孙连长当了四年,办公生活用品都老旧得不成样子,我琢磨着,新人新气象,得换换面貌,让司务长从伙食结余里抽出一笔,给各班买了扫把拖布,连部的破烂也都换了。没想到这小子见我烟瘾大,为了讨好我特意买了个巨大的玻璃烟缸,我还没往里面弹过一丝烟灰呢,在老赵眼里就成了个败家玩意儿,你说冤不冤。”
“败家倒在其次,一个玻璃烟缸,再贵能值几个钱。问题是,让你摆了这么大个玻璃缸子在这儿,以后团长政委只能拿鱼缸弹烟灰,军区司令员恐怕要用水晶棺喽。”
董振俊笑道:“是啊,听说以前有个指导员不懂事,刻的姓名章比团里的公章还大,送上去的呈报件都成了笑话。政委有次在他的呈报件上写,兹事体大,请直接呈皇上处理,无玉玺朱批概不执行。”
徐宏彬哈哈大笑:“常听人说,当官当到大军区领导这一级,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已经没啥区别,司令员往往比政委还讲政治。我看你老兄已经做好了戴上三颗将星的准备,提醒人都这么委婉,有水平。这份好意我心领了,不过嘛,做人做事,凡事思虑过度,也成不了大气候,我当主官两年,说做事,做了一些事,论结果,团里师里也算都留下了点儿印象,都说徐宏彬心细如发,做事周全,可我听了心里蛮不是滋味儿,我要是个太监,这话是在夸我,可我到底是个兵啊。兵龄渐长,兵味全无,可悲,可怜。”
董振俊愣住了,眼前这人八面玲珑,顺风顺水,跟他认识这么长时间,没瞧出过什么破绽,没想到他骨子里也有一份锋芒和悲凉,以至于要故意露出个大破绽来释放自己。
“刚才骗你的,罐子里就是金骏眉,我冲给你喝。可惜这荒山野岭空有好茶,却无好茶具。”徐宏彬娴熟地捏起一撮茶叶,分量不多不少,开水一泡,满屋都是茶香。
董振俊喝了一口,心里有股暖意,他知道徐宏彬唱的这出戏,是怕王松这事造成彼此的隔阂。张永新是董振俊从机步一连带过来的,张永新一入伍董振俊就是他的排长,两人的关系有多铁不言自明,而指导员对王松的好大家也都看在眼里。这俩人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极有可能上升为连长指导员的矛盾。徐宏彬这番话,让董振俊感觉或许这人可以交个朋友,至少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两人的意见肯定是一致的。
打从中午开始,四班的人都等着看笑话。赵小军沈原他们,既痛恨张永新,又烦王松,不管谁倒霉他们都开心,他们翘首以盼,连长指导员要么批评王松,要么批评张永新,或者各打五十大板,只有吴论和张若谷没有任何兴奋之情。张若谷说,思考这种事只会腐蚀自己。吴论说,你们俩高兴个屁,我看这事肯定就这么过去了,谁也不会再提。赵小军和沈原不服,士官和军官公开发生矛盾,这事连里能不处理?吴论说,不处理就是最好的处理,否则你让连长指导员怎么处理?
当晚点名,连长指导员还是照常讲评训练情况,布置明天任务,王松张永新的事儿果然只字未提。不过原因并非如吴论想的这么简单,董振俊和徐宏彬分别找王张二人谈了心,都说了一句相同的话,在一块儿就呆三个月,何必呢?徐宏彬说:“就算是演戏,你们俩也得把这出戏给我好好唱完。”
董振俊说:“有矛盾,有恩怨,新兵连结束后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在我眼皮子底下找事,那就先跟我过过招。”
王松或许还没明白,这要不是在新兵连,连长指导员肯定是明面上批班长,私下里反而会给他出难题,在主官眼里,他受的这点委屈根本不算什么,但主动挑事,给连队带来的麻烦必须让他买单。张永新这种老兵油子却已是心知肚明,之后也越发不拿王松当回事了。
王松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在之后的岁月里多受些气,吴论却成了这件事最终的买单人。王松越是认为吴论队列不行,张永新越是要练他,还要把他练得比谁都强,那天中午之后,吴论享受的开小灶直接升级为国旗班待遇。
那次濒临中暑,张永新的讲解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但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他的军姿就自我矫正了过来,吓得赵小军以为他是鬼上身。但在张永新眼里,这还远远不够,他不知从哪儿找到个中学数学用的大量角器,告诉吴论,按照队列条令,立正时双脚张开角度为60度,你外八字严重,张开到快100度,还得加练。他也确实有土办法,找了几块砖头,在地上摆出60度的张开角,让吴论站了上去。同时,让他把帽子反顶在头上,只要帽子掉了,或是砖头倒了,再加练半个小时。
除此之外,齐步走时前脚后脚的距离,正步走时脚尖离地面的高度,乃至手臂与躯干的距离,全部精确到厘米。张永新在营区外面找了两棵挨在一块儿的歪脖子老树,绑了七八根棉线,吴论练正步分解动作时,只要碰到其中一根线,加练十五分钟。吴论想,白天你可以这么玩我,到了晚上两眼一抹黑,你奈我何,没想到张永新在线上抹满了滑石粉,借着一点星光,张永新也能看到碰线时滑石粉弹出的烟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