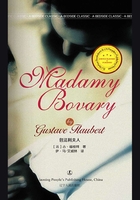新兵连是这么一个奇特的存在,每天跟你睡一间屋里的人,有可能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白天强度太大,吃饭不让说话,晚上还可能加训,一进屋所有人都像是被吸进被子里,连屁都忘了放就被疲劳一拳锤到梦里。能说上几句悄悄话的,一是洗漱时间,可以耳边偷偷讲几句,二是上大号,一旦确定旁边几个坑没人,憋在肚子里几天的闲言碎语便随着大便倾泻出来,而且这些话往往比大便还脏。
沈原和赵小军嘴就够脏的,恶魔,王八蛋,性无能,生儿子没屁眼,给三分颜色就开染坊,拿着鸡毛当令箭,逼崽子,掺和着京骂和东北骂,所有能想到的不良词汇都献给了班长张永新。如果吴论在边上,他们会骂的更起劲,想勾开吴论那张懒洋洋的嘴。通常情况下,吴论耷拉着眼皮,毫无反应,有天他们终于憋不住了,问:“卵,你怎么跟273他们似的,不敢说张永新呢?”吴论说:“你们觉不觉得我们张班长他外公挺能生的?”赵小军说:“听上去像是句骂人的话,可我怎么不明白呢?”吴论说:“不然他怎么每天都跟死了个舅舅似的。”
卵是吴论的外号,新兵连,乃至任何一个男性群体,一个成员要是没人给起外号,只能说明他被大家排斥,外号越脏越让人说不出口,说明你跟大家玩的越好。赵小军一开始管吴论叫吴卵,因为他每天软沓沓蔫乎乎的,不知道一天到晚在琢磨啥,后来吴论抗议,你们也不先看看我姓什么?于是统一称呼为卵。除了赵小军自己,没有人管他叫军哥,因为他走路特别垮,都喊他赵垮,沈原的外号很好起,猴子,他也是从小被人这么叫大的。只有张若谷的外号比较特别,273,是吴论给起的,这些人里也就吴论跟他玩的还可以,吴论没想给他起太脏的绰号,就拿绝对零度命名他了,但别人叫起来总觉得自己是在监狱。赵小军常常愤愤不平:“卵,我被你整的老不愉快了,你看啊,你军哥我每天结束了一天的辛苦训练,准备放松身心拉个屎的时候,一不留神就能碰到那个273,有他在,我就觉得那个牢头狱霸在瞅着我,屎都拉不出来了。”
最先想跟张永新拼命的正是赵小军,新兵连第一周,主要训练科目是军姿和齐步走,齐步走看似简单,却快要了他的命。训练时,张永新把齐步的动作要领吼了三通,就让这7个人走,一走发现不对,队列里有个人走路的时候双手双脚全都抬起来了,定睛一看才发现是赵小军顺拐了。这顺拐的毛病,没当兵的人自己察觉不出来,但一走齐步就原形毕露,齐步走要求迈右脚时挥左手,迈左脚时挥右手,但有人就是同手同脚,费很大力气才能扭过来,还得巩固个十天半个月。而赵小军不但顺拐,平时走路还有股古惑仔赶去受保护费的劲头,所以一走齐步,就像个喝了假酒的黑社会,走不出十米就会裂成两半。
张永新站在赵小军背后,调整了十多分钟也没把他拧过来,脸更难看了:“赵小军,你是不是故意想找刺激?”
赵小军说:“班长,我哪敢啊?”
张永新说:“那行,你现在用最大的声音喊,‘我再也不敢了’,十遍。”
“啥?”
“让你喊你就喊。”
队列训练的地方是一块水泥铺成的、面积上千平米的平地,全新兵营几百号人都在这里训练,这片训练场正对着山谷,赵小军嗓门又大又粗,每喊一句,回声能重复三四声,喊了十声后,整个训练场上仿佛有几十个赵小军在一起求饶。吴论心想,张永新这种残酷倒还有点幽默感。
但赵小军确实不是故意顺拐的,只要不走齐步,他走路除了比较痞比较垮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但只要齐步走口令一下,他的左手左脚和右手右脚就跟用502胶水沾上似的,掰都掰不开。这天早上三连各班本来要教完齐步走全部动作要领,但就因为赵小军,八个人的进度全都慢了。下午训练,张永新不知从哪儿找来跟尼龙绳,下巴朝赵小军戳了戳,后者半天才反应过来是要把自己的双手捆上。
这下赵小军炸了锅,他是最要面子的,上午的那十声“我再也不敢了”已经让他颜面丧尽,这再绑住双手走路,自己不跟囚犯似的,让全营的人看他的笑话?他说:“班长,你这是人格侮辱,我不捆。”张永新说:“你要让其他人的训练进度都被你一个人耽误吗?”赵小军歪了一下头:“耽误就耽误呗,我没看出这齐步走有啥用,真要上了战场,你还傻乎乎走齐步啊,不被人一枪崩了?”
张永新愣了一下,什么都没说,突然伸手抓住赵小军的脖子和腰,将他整个人空中翻了个180度,倒提了起来,这下吴论等人都看傻了,赵小军一米八的个子,体重至少75公斤,而张永新个子一米七不到,居然像拎王八似的一手就把他提起来了。
张永新声音低了下来:“捆不捆?”
赵小军只好就范。
下了操课回到宿舍,赵小军眼角泛出了泪花,嘴里嘟囔着:“妈的太欺负人了,哥哪受过这种气啊,以前哥欺负人的时候也没这么欺负啊。”沈原和吴论都安慰了他几句,张若谷说:“班长的处理方式确实值得商榷,不过你说齐步走没用也不妥当。古斯塔夫二世的时代,瑞士长枪兵正是靠着整齐划一的队列才让欧洲各国的重骑兵束手无策,后来火绳枪时代,步兵对抗以列队射击为主,齐步走的作用是受过战争检验的,现在它或许作用不大,但有利于我们形成服从命令的肌肉记忆,对部队整体的协同指挥来说是必须的。”赵小军说:“273,向后转,齐步走,请你从外面把门关上,然后滚鸡巴蛋。”
第二个想要他命的自然是沈原。
沈原这人遇事有一百个机灵,骨子里却是个懒坯,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就算躺着也不舒服,还恨不得有人给摁摁脚捏捏背,再来个丫头边上点根大烟枪。用吴论的话说,最适合沈原的地方就是晚清的八大胡同。自从张永新教完内务标准,沈原的被子就很少出现在床上了。新兵连规定,每天上午操课,排长要回营房检查内务,第一天沈原的被子就被王松从二楼扔了下来,张永新说,他见过内务最差的兵,是把豆腐块叠成了花卷,沈原有突破,把豆腐块叠成了爆米花,别人想叠成这样都难。张永新这人面子第一,王松扔了一次,他绝不会再让他扔第二次,于是之后不等王松检查,张永新早把沈原的被子扔了下去。一周过后,沈原虽然裹在沙土里睡了七天,也只是略有长进,终于把爆米花叠成了花卷,张永新为表祝贺,终于不再把他的被子扔到楼下。沈原这天回来,发现楼下没有自己的被子,以为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没想到一回宿舍被子还是不在床上。这时赵小军推开门,一股臭气扑面而来,赵小军扔了床被子在地上:“卵,273,老陶,你们身上没凶器吧?别让猴子找到,张永新这傻逼把他被子扔茅坑里啦。”
十月的东北,晚上寒气逼人,沈原本是个仨瓜俩枣就载歌载舞的人,没人理他也能自己逗自己一大跟头,这天一直没说话,晚上睡觉窝在军大衣里瑟瑟发抖,嘴里念念有词,赵小军半夜趁张永新睡着了,凑到他耳边问:“猴子,你别想不开啊,嘴里咕哝啥呢。”沈原说:“一边呆着去,这是我老娘当年南下从一个大师那儿学的咒语,我在给变态下蛊呢。”赵小军擦了擦额头:“没疯就行,没疯就行。”
其实沈原不是叠不好,他是舍不得自己。叠被子这事儿,表面上是个叠,实际上全靠压,把蓬蓬松松的棉花压紧压实了,才能叠出想要的形状。而用人力压棉花,就像《食神》里的莫文蔚锤牛肉似的,不但是个力气活,还是个细活,得不厌其烦反反复复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第一天教叠被子,张永新就说,你们的被子是刚发下来的,想叠成我这样,光压不行,得撒些水,当然你也可以不撒,我只看结果不问过程。这句话一说出来,吴论和赵小军心里飙出几百句脏话,东北这温度,晚上让人睡湿乎乎的被子,这人是吃米饭长大的吗?但腹诽归腹诽,他们还是照要求干了。唯独沈原没洒,一是懒,二是在北京这种干地方呆久了,受不得潮。吴论之前没劝过他,这次看他吃了这么大一苦头,什么话也没说,一脚踹在了张永新的被子上,赵小军吓了一跳,赶紧把被子拍干净重新整成了原样,嘴里不住说:“卵,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而且你自己也得小心,忘了那盆洗脚水吗?”
吴论当然没忘,不过他也没弄明白,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吴论才是张永新的眼中钉,为什么第一周吃亏的是赵垮和沈猴子。这俩人背地里把张永新的所有直系旁系亲属都操了个遍,远远超出五服,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的。而他自己,虽然张永新交代的事他都不折不扣地干了,但从没拿正眼瞧过他。赵小军和沈原劝过吴论,要谨记小平同志的教诲,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他立刻怼了回去:“你们这是老鼠舔猫,纯属找削。”
老鼠跟猫关在一个笼里只有两个结果,配合猫,让它玩开心了,可以晚点死,不配合它,壮烈牺牲,尸骨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