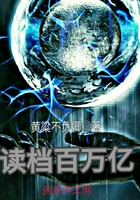一个鲜活的少年就这样殒于皇权斗争,他本身没有一点过错,错就错在他生在了帝王之家,并且是生在了末代帝王之家。临死前,他连生他养他的母亲最后一面也没见着,这种痛苦和遗憾不仅令他,也令后世众多读史者欷歔不已。杨恫的母亲刘良娣,这个被王世充控制的女人,在听到自己的宝贝儿子被杀死的噩耗时,应该是怎样的悲伤、绝望和愤怒!史籍没有记录她自儿子被杀后的任何资料,但在那个乱世,她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一个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一个没有大哥罩着的年轻漂亮的女人,再加上一个前皇帝妈妈的身份,如果能平安终老,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王世充虽然登上了帝位,但他缺乏作为一个明主的领导水平、个人魅力和领袖气质。如果将所有人分成君子和小人两类,那么王世充将名至实归地被划入到小人之列。这当然和他抢夺别人的帝王之位无关,因为本来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既然张三能当皇帝,那李四、王二麻子就也能当,改朝换代只有成和败,没有对与错。
之所以说他是小人,是根据他的自身各项“综合素质”打分评判的。王世充的老师徐文远就将自己的这个学生定性为小人。徐文远是隋朝著名学者,曾担任过洛阳的最高文化机关领导国子祭酒,巧合的是,李密和王世充都是曾经聆听过他教诲的学生。而对于这两个学生,徐老师对他们的态度截然相反,早在王世充还是太尉的时候,徐文远见到这个王学生,老远就恭恭敬敬地行礼,而对李密的态度却很随意。在洛阳被瓦岗军围困那段时间,徐文远有次出城砍柴被瓦岗士兵逮住了,李密见到徐文远后,令老师南面而坐,自己“备弟子礼,北面拜之”。可别小看南北两个方向,在中国古代的很长时间,南北方位一直代表着上下尊卑之别。李学生拜徐老师,而徐老师却拜王学生,整个一笔糊涂的“三角债”。对徐文远这种“厚此薄彼”的现象,时人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倨见李密而敬王公”?
徐文远回答说:“魏公,君子也,能容贤士;王公,小人也,能杀故人,吾何敢不拜!”
知子莫如父,知徒莫如师。徐老师的评语是最权威的道德品性判决书,“王小人”这顶帽子王世充算是戴定了。
如果对王世充在两年短暂的皇帝生涯内的所作所为进行一下归纳总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世充称得上是“两个百出”皇帝——花样百出、洋相百出。这个土皇帝不但喝花酒很老手,花点子也特别多。他上台后想出了不少花里胡哨的施政新点子,在洛阳城内玩了好一把“我行我秀”。其实他亮出的这些点子秀如果能长期坚持秀下去,兴许就秀成一代明君了,只是明君的称号不是靠伪装和作秀就能得到的,就像一个暴发户,无论怎么冒充斯文儒雅,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看上去具有夺人心魄的贵族气息的。王世充也确实只能算是一个政治暴发户,连表面工作也做得假模假样、虎头蛇尾,结果适得其反,徒留给世人暴笑之柄。
他上任后的第一项改革是深入民间基层,和人民群众零距离全接触。身为天子,他骑着高头大马在闹市街道晃趟子的时候,没有警卫开道,不需清场戒严,而是边走边和群众同志们聊自己的先进执政理念,说“昔时天子,深坐九重”,无法真实了解百姓民情,今天我王某人做皇帝,并不是为了贪图皇帝的宝座,而是“欲救恤时危”。按照王皇帝的讲法,他可真是够伟够大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之所以“咬牙”登上帝王之位,是为了拯救多灾多难的现实社会,颇有几分诸葛亮当年“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凛然与崇高。好像皇帝御座直接通往刀山火海和油锅,但为了“救恤时危”,刀山他愿意上,火海他愿意跳,油锅,他也不介意下去冲冲浪。连做皇帝都是为了拯救全世界、解放全人类,这种貌似高耸入云的境界,其实可以嫁接成一句冠冕堂皇又让人忍俊不禁的现代调侃语:如果当皇帝是一种错误的话,我愿意错上加错。
王世充为了标榜自己确实是心甘情愿“错上加错”的,他表示(这次不是发誓哦)自己要像一个州的地方长官刺史那样,亲自处理各种大小不同政务,还要官员百姓畅所欲言,评议朝政。为了杜绝宫廷机关“门难进、脸难看”的现象,他还正儿八经地搞起了现场办公,不但在“阙下及玄武门等数处皆设榻”,而且还“于门外设坐听朝”,同时“令西朝堂纳冤抑,东朝堂纳直谏”。看这架势,年号开明的郑国似乎要进入“开明盛世”了。然而,号称开明的郑帝王世充其实是冒充开明的。当不明就里的广大人民群众被貌似礼贤下士、勤政爱民的好皇帝的一系列开明行为感动到“献策上书者日有数百”时,王世充却“数日后不复更出”。
开明了几天,他就因“条疏既烦,相览难遍”而偃旗息鼓,再也不肯出宫现身了。这种风头只出一阵、笑脸只露一点、认真只有一会儿的虚浮作风,和现在某些领导酷爱在照相机、摄像机面前慷慨激昂、大言不惭地表演如出一辙,建议雅好此道的领导可以认祖归宗,进入王氏族谱。
其实“作秀”这个词已经慢慢由最初的贬义词向中性词过渡,因为即使是最贬义的“作秀”,如果一直坚持作下去,那就变成纯褒义的“优秀”了。但王世充这个宝贝货,恐怕最后连“作秀”都算不上,“充”其量只能是“作”,而且作得洋相百出。早在登基前的三个月,王世充担任权倾一时的太尉时就搞过作秀痕迹十分明显的不了了之的“现场招聘会”。他命人在太尉府门外立起三块写有招聘启事的牌子,写明面向全国公开招录郑国国家机关公务员,并着重点名需求三类人才:“一求文才学识堪济时务者;一求武艺绝人摧锋陷敌者;一求能理冤枉拥抑不申者。”用现代白话文简约归纳出来就是招收政治家、军事家和司法专家。领导如此求贤若渴,而且招聘的又都是福利好、待遇高的热门岗位,所以“三求启事”贴出后,应聘者纷至沓来,“于是上书陈事日有数百”。刚开始时,王世充亲自接见应聘者,亲自翻看他们的简历和文章材料,殷勤询问他们的观点看法,把应聘考生感动得“人人自喜,以为言听计从”。然而,最后“终无所施行”,没有任何结果和下文。
除了花花点子很多外,王世充在朝廷上还经常出洋相,他和因不知道怎么处理公务而在朝廷上一言不发的宇文化及截然相反,是个话痨,每次上朝时,他都“殷勤诲谕,言词重复,千端万绪”。他不知道“话讲三遍比屎臭”,处理朝政时,喋喋不休,絮絮叨叨,云山雾罩,不得要领,差不多能把五十年的老失眠症患者讲到当场睡着。弄得“侍卫之人不胜倦弊,百司奏事,疲于听受”。
大家都怕跟他汇报问题,因为他逮着谁就口沫横飞、不着边际地罗嗦个没完没了,说得甲方乙方甚至丙方丁方都几近神经衰弱、疲惫崩溃,但还不得不强打精神装出认真倾听的样子,毕竟谁也得罪不起皇帝呀。
御史大夫苏良实在忍受不了,便向王世充劝谏道:“陛下语太多而无领要,计云尔即可,何烦许辞也!”苏良的观点很明确,废话不要太多,商议决定问题时,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地说下中心思想就照了。但王世充还是依然故我,“终不能改也”。
王世充在洛阳弄权时的形势和当年宇文化及在江都兵变时的情形很相像,都是手下凶悍猛将比比皆是,秦叔宝、程知节、裴仁基、独孤武都、裴行俨父子、罗士信、刘黑闼等这些在隋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勇将皆是他的部下。但最后这些以一顶百的大将逃的逃、反的反,都弃他而去,绝大多数都归投了唐朝。这些人如果死心塌地跟着王世充,那后来唐郑两国之间洛阳大战的胜负将充满不可预知的变数。
如果一个下级说领导太“猪头”,可能是这个下级对领导有偏见;要是两个或者几个下级抱怨领导太“猪头”,也可能是这些下级对领导有成见;但倘若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领导是“猪头”,那这个领导肯定是太差劲了。王世充就是这样一下级都说他是“二百五”的孬领导。
领导,特别是领袖,除了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本领和才学外,还应该具有一种天生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以及一种让部下心悦诚服、死心塌地追随的人格魅力。而“为人残忍偏隘”的郑政权最高领导王世充却是一个要才没才、要德无德,声望威信更是无从谈起的“婆婆嘴”。所以,他手下的那些勇猛无敌的将领都从心底里瞧不起他,纷纷炒他鱿鱼,离他而去,另择明主。
最有个性和戏剧性的是秦叔宝和程知节。这两人本来都是李密的部下,邙山之败后归顺了战胜方王世充。王世充很看重两人,封秦叔宝为龙骧大将军,程知节为将军,“待之皆厚”。但这两个当世英雄特别憎恨讨厌王世充狡诈恶毒的品行,秘密谋划反水。
程知节对叔宝说:“王公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此乃老巫妪耳,岂拨乱之主乎!”程知节觉得为人浅薄、气量狭隘的王世充跟一个胡言乱语、赌咒发誓的老巫婆似的,连做一个魅力男人都不及格,哪能还指望他成为平定乱世的君主呢。跟在这样没层次的领导后面,岂不是辱没了自己!
于是在一次王世充亲自指挥的和唐军的战斗中,已决定“转会”唐朝的程、秦二人阵前倒戈,两人带着数十名部下突然离开郑军大部队,在骑马奔出百余步之后,秦叔宝和程知节跳下马对目瞪口呆的王世充恭敬地行礼,并对他坦白了离开的原因,说自己得到政府特别优待,深受感动,也曾经想为郑报恩效力,但“公性猜忌,喜信谗言,非仆托身之所”,所以就此别过。
被两人数落了一顿的王世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投入唐军阵营,竟不敢派人追截阻拦。因为谁都知道,要是惹毛了这俩有万夫不挡之勇的猛男,送掉小命那是分分钟的事情。王老板这次被这两个顽主整得太伤自尊了,在编在册的员工反叛跳槽竟然不慌不忙、不藏不掖、镇定自若、礼数周全,地地道道的“我的眼里没有你,只有他”。如此当着拥有千军万马的老板之面,从容不迫、来去自如的秦叔宝和程知节两人完全可称为“史上最牛炒老板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