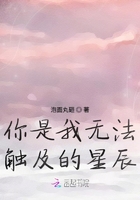“张宗主既然亲自请了,那我们就去通报一声,但我们宗主愿不愿意出来,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了。”为首的长老支会一声就直接离开。
“行了,宗主都来了,我们也撤吧,这件事若是他都不能解决,我们就更没办法。”梁秋水吆喝着,大家也都准备散去。
“你给我站住!自己徒弟惹得麻烦,我出面帮忙就算了,你这个当师傅的要不出点血,怎么对得起我,晚点脸你就别走,可别让我事后找你。”张路远一把抓住了梁秋水的衣襟,就直接把他往回拽。
“姓张的,别给我扯那些有的没得,别人怕你,我可不杵你,要真说责任在谁身上,那还不都是你当年干的破事,要不是你,绿萝宗怎会下达不能异性进入的规定,也不会闹出今日之事。”梁秋水不紧不慢的语气,说的张路远脸色有些尴尬。
其他的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仿佛这段过往他们也都清楚。
“张路远,交出那个弟子,不然就等着开战,你知道的,我们绿萝宗向来无情,对于生死伤亡,从不看重。为了一个弟子,而让众多弟子送命,这可不是你们灵缘宗的风格。”绿萝宗的大长老去而复返,声旁多了一位女子,与她们是同样的打扮,想来可能就是宗主。说话之人,也正是她。
“琉璃,你当真半分情面不讲,此人不光于我,对很多人开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你若懂动了,可不单单是得罪我灵缘宗一家的事。”
“那又如何。”琉璃看着张路远的样子,毫不犹豫的说出这四个字。
“那又如何?你真以为我们怕了你不成。”这四个字似乎是击气了张路远的怒火,天地变色,一股强大的威压落在绿萝宗众人身上,让她们脸色一白。
“你走出那一步了?不可能,这不可能。”琉璃古波不惊的脸上,难得的出现了诧异的表情。
“这一步踏出,我们就是天差地别,你若真有心开战,那就只管前来,我不拦你。”张路远闭着眼睛,似乎不愿见到琉璃如此。
“那便战吧,拖了这么多年,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断。”琉璃似乎是下了决心,闭着双眼,也不去看张路远是何表情。
“你不是一直想斩了我的因果,好助你走出那一步吗?我不反抗,你只管来斩,放过杨云,这是交换的条件,于情于理,我们都不亏。”
“至此以后,两不相欠,互不干搁。”张路远想了很久,才说出来这番话。
此言一出,琉璃的双眼发亮,张路远一直是她走出最后一步的阻碍,若是能斩了他于自己间的因果,她有十足的把握会突破。
况且,这张路远能狠的下心来,自己也能,不然,他又是靠什么突破的。
剑刃直接出鞘,不给张路远任何反悔的机会。
绝情,无情,这一剑如同带着苍天行驶旨意,冷酷干脆,直接斩在了张路远头上,斩在了他冥冥之中的因果线上。
“蹦。”张路远可以清晰的听到这根因果线断掉的声音,琉璃花了太多的时间精力想要弄断它,而自己又不停的将其修复,这根因果线,已经绷的很紧了,现在自己放弃了抵抗,只要轻轻一碰,也就一分为二。
“我们走!”看了琉璃最后一眼,张路远转身离开,他知道,只要自己不去修补这根因果线,一天之内,与那琉璃发生的种种皆会遗忘,这一眼,也就是最后一眼。
众人沉默,都跟着离开。
“各位长老,麻烦你们也斩了我的那根因果线,助我突破。”琉璃不知自己抱着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句话,绝情之人,本应无情,却因为这张路远的闯入,让自己一直停滞不前,如今有机会精进,应该高兴才是,为何自己,一直高兴不起来。
八大长老没有犹豫,直接斩下,琉璃也就此离开,她心里清楚,张路远的没断,自己的也斩不断。
“传令下去,宗门不准异性进入的禁令解除。”说出这番话,也不管八大长老的表情,琉璃直接离开。
“下次再见,大家都是陌生人了,希望,不会成为仇人吧。”琉璃想道,之前的种种画面渐渐消失,直至张路远这个人,从她的记忆之中全部抹去。
“师傅,这一次,真的值吗?”
“这一天早晚也会来的,就算没有杨云,也会有别的事情,希望她能早日堪破,绝情,呵,这世上哪有什么绝情之人,哪里有什么绝情剑道啊。”张路远大口的灌着酒,地上早就已经放了好几个空坛。
往日的一切都在他的脑海中过了一遍,然后逐渐湮灭,再想去寻,也寻觅不到。
八大长老站在外面,没有人进去,或者不知道进去怎么劝导,都是男人,不擅长此时,何况当年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不清楚,只知道两人有着不浅的感情纠葛。
“天丁啊,我们也就只能帮到这里了,这是炼器阁的长老,专门打造的法器,配上阵法,宗主刚刚被抹去的那段记忆都被存在里面,不过这因果一段,哪怕有这记忆,也无济于事,你也别急,之后我们在想办法。”阵法阁的长老,看罗天丁的样子,把炼好的珠子交给了他。
“有劳了。”罗天丁直接拜别,众人也没有阻拦,张路远虽有时严厉,但待这个弟子,犹如亲生一般。
众人在此逗留也没有意义,他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也就纷纷离开,只是这事也勾起了他们的一些回忆,气氛有些惆怅,尤其是梁秋水,回去以后拿着手上的那把勺子,望的出神,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琉璃啊,大劫将至,希望你能早点领悟,好有自保之力啊。”
“琉璃啊,当年若是在给我一次机会,我拼死也不会让你走上绝情之路。”
“琉璃啊,好想在听你叫我一声,路远。”
张路远越喝越多,这些酒都是极品佳酿,哪怕他实力高深,没有用灵气去解,也有些扛不住,半醉半醒间,趴在桌子上,嘴里嘟囔着一些话,机械式的灌着自己一些酒,最后全撒在了身上,打湿头发衣襟。
直到不省人事,他就躺在酒渍之中,如同凡间那些醉酒的老人一般,落魄,狼狈,要是让别人看到,任谁都不会相信他是灵缘宗的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