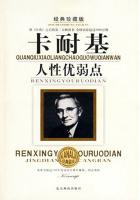我是月儿。
我回了房间,开始给他们清洗。
坐轮椅的老人让我给他端便盆,我问:“在哪?”
他说:“不知道在哪来干嘛的?”我耐住性子说:“我今天刚来......”好脾气的爷爷说:“隔壁就是洗手间。便盆都在那里面。”
我过去一看,是有一排痰盂,但都脏的发臭,恶心的不得了。
我拿了个略干净点的,拿到房间里,轮椅上的老人接过去就开始解裤带,身都不转一下。我连忙走出来,心生嫌弃。
一会儿听见他喊:“快给我端走,快端走!刚来就没人影了,来干什么的!”
我进去,好脾气的老人只笑不说话。我耐住性子,端起痰盂往洗手间走去,一阵阵恶臭,我用袖子捂住鼻子才给他倒了,把痰盂摔一边。
我是不打算去他那屋了,路过他门口,他又喊:“你过来,给我端些水洗脚。”
我想起组长说的话,就假装没听见,一路走过去。听见那人一连串的骂声,不堪入耳。
那个自闭症小女孩,我给她说话,她根本不看我,只给手里的玩具“呜哇呜哇”说两句,也听不清说的什么。
我看得心疼,想过去抱抱她,但她突然抬手打在我的头上,打完就跑了,手里依然拿着那个残缺不全的奥特曼。
给其他几个人做了些清洁,洗了手脸,中午饭就开始了。
徐卿文打电话:“回家来,做好饭喽。”
我说:“中午不回去了。”
虽然我觉得心情阴郁,但是觉得此刻不应离开。
工作人员从厨房里推了个小车出来,小车上是四个不锈钢的大饭桶,和一些餐盘。工作人员从一楼开始,挨个房间给这些人送饭。
我跟在他们身后,负责给一些人戴上吃饭用的围裙。其他几个护理人员,各房间转转看看,若有不能自己吃的,就过去帮忙喂两口。
忙碌了一阵,吃饱的没吃饱的都不吃了,工作人员又挨个房间收餐盘,我再负责解下围裙。自闭症的小女孩没怎么吃,给她说话也并不理睬。
给我吃“桃酥”的老人一口也不吃,说:“你们给我吃海绵,我不吃,我给你们说,这个不能吃。”
护工劝她两句,仍然不肯吃,就收走了。
脑瘫后遗症的男孩用手指挤着勺子,正努力的将饭菜挑进嘴里,动作僵硬又艰难,但每吃到一口,都露出满足的笑来。
我走过去,接过勺子喂了他几口,我说:“吃吧,不着急,慢慢吃。”他竟然一字一顿,含混不清地说一句:“谢谢。”
我听了倍受感动,就坐下来一口口喂下去,他很开心的吃完了盘里所有的饭。
除了脾气大的那个老头,我又给其他几个剪了指甲,擦了一遍手脸。把收集起来的围裙洗了一遍,这些事情做完,已经是半下午了。我也累的直不起腰来了。
我想着这里的护工天天如此,真的是辛苦。的确没有什么精力再与这些人做精神上的沟通。
社会给他们最低生活保障,能吃饱,穿暖,可以不用被抛弃路边,冻死街头,已经是不容易了。
但是人生,真的不止是活着。活着有个会动的躯体就够了,人生却是要用灵魂来充满的。
每个人的灵魂自然不同,但是有的人张开翅膀的时候,有的人却只能蠕动前行。
念及此,我心里升起一阵悲哀,不知为何,不知为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