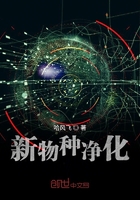天大亮时,二爷醒了。但他不急于起床,躺在床上咳嗽着。等到街上买卖人有了,他才慢慢动身穿好衣裤,脸也懒得洗,上了趟厕所之后,就挽着二海碗大小的小花篮,加入赶集的人流,徐徐晃着。
宽阔的集市像条小河,稀溜溜的人群像鱼儿胡乱穿插着。二爷钻进这条小河,便像所有赶集的人一样慢慢走着、瞅着,时而走马观花地一了,时而又驻足端详,很像在选择什么必需物品。
他溜到南市,那里的空气洋溢着阵阵油香。赶集的人渐渐多起来。他来到一摊炸丸子面前,停下脚步只管注视着。卖者站起来道:“老大爷,称点丸子?”二爷不吱声,趁势夹起一颗丸子塞进嘴里,慢慢嚼咽着,似在品尝。
“我的丸子还中吧?”卖者笑眯眯地恭维。
二爷又夹起一颗不同色泽的丸子咀嚼,品了品,半天才点头:“中。成色好,炸得也老。是茶油炸的?”
“是茶油炸的。称几斤?”
“咱老伴吃呢。她不爱吃茶油炸的,爱吃菜油炸的。”二爷笑笑,似不好意思。
二爷又来到一摊油炸果子跟前。只要脚步一停,卖者心照不宣:“想买吗?咱的油炸果子好吃,不信大爷你尝尝。”
二爷求之不得地尝了许久,终于回话了:“果子好,配料也配得匀。可惜老伴她没牙,嚼不动。下回再买吧。对不起吃了你的东西。”
商品被赞扬,便如得了奖,也是一大招牌呢。果然那卖者转眼对一买者说:“咱不是老王卖瓜,你问刚才这位老爷子……”
二爷粲然一笑,又往前走。前面又有诸多食品摊等着:油炸糕呀,油蛤蟆呀,烤饼干呀……二爷也不怕麻烦,隔个三步五步就停下来,吃了一路。
大约白日中天,肚子里似有东西在滚了,二爷就开始打道回府,依旧加入散集的人流,徐徐晃着。
回到家里,病中的老伴已经起床了,水也烧好了。二爷就和她闲聊起来,谈集上的新闻,谈集上新添的物什,还谈他刚吃的食物哪种好、哪种次。末了,他就帮助老伴熬稀粥、切咸鸭蛋。这样,他们一天的伙食就解决了大半。
“混二爷”其实也就这么容易。二爷想。钻人家的空子呗。可有时也不免出大漏子。
儿女不在跟前,一个月没来打次照面。老两口相濡以沫,常常为最后半碗稀饭归谁吃而互相推让。想到老伴,他就心疼。自己只管吃饱吃好,没带点回来给病中的老伴尝鲜,他总觉得过意不去。那一日他就想:能不能弄点回来呢?可那不成了偷?
他试了试。当他品尝油炸萝卜丸子之类老伴爱吃的东西时,他尽量伸出三根指头夹两颗起来,慢慢嚼着,拖延时间,然后趁人不注意,将余下的一颗揣在手里。走过几步后,送进兜里。
似乎也很成功。谁想一个老头会偷一粒东西藏起来?偏偏一次没留神,东西从兜外滚下地,被卖丸子的发现了;恰巧这卖丸子的又是个不好惹的泼娘们,当即追了过去,大骂二爷偷了她的东西。
“没、没偷呀?”二爷假装糊涂。
“搜!”谁知丸子没搜着,却搜出半兜子红枣、饼干、油炸果子之类。那妇人当场叫街,吆喝人们都来抓贼。人们外三层里三层地将二爷围起来,许多人嚷:“快把他送到派出所。”
“咱老伴要吃,没钱。”二爷低声申辨,可怜巴巴的,老脸无处可藏。
一个邻居挤了进来,大声替他解围:“各位各位,这老头可怜,儿女不愿供养,老伴常年有病,想吃东西买不起。各位权当他是个要饭的。”
一句话说得二爷眼眶湿润了。
“没钱?没钱就明要呗,谁在乎一点东西?”
人们转而又同情二爷,骂二爷的儿女不孝道。卖油炸丸子饼干之类的大多心慈手软,人人往二爷篮里捧东西,一边同情叹息,一面责怪二爷不该偷。
“多谢了多谢了。”二爷又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二爷提着满篮子回家,老伴问他咋整这么多东西,他没说实话,怕老伴埋怨,只说是一个记不清名字的亲戚送的。
后来,大约十天半个月,二爷再没有赶集了。终于他又挽着小花篮出门了,却在门口徘徊半天,又转回来了。他拿定了主意:“混二爷”还有脸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