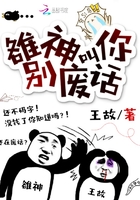周围陷入一片沉寂,好一会儿乔彴才出声说道:“反正我还是不信。”
凌小悠依旧没有基于跟他争论,只是平心静气的靠在矮塌上,缓着气说道:“理由。”
“朝中如今分三派,一是以左相为首的先皇留下的旧部;二是以太后为首的前朝旧臣;三是以右相为首的陛下近臣。从始安之乱之后就一直维持着这个格局。可永安王却不属于这三派中的任何一派。”
凌小悠的一只手轻轻的揉着自己的额角太阳穴,刚刚说话有些急了,气血不够用,脑仁隐隐的有点痛。
“继续说。”
“我不能否认你说的野心,因为人心难测,我也不能肯定永安王如今心境如何?可我知道这三股势力都不想让永安王活的时间太久。”
凌小悠微微掀了掀眼皮:“有仇?”
“准确的说,是碍事。”
“碍事?”凌小悠想了一下,“你之前说左相和永安王之前有些陈年旧事的瓜葛,要说他们心存芥蒂,朝堂不睦,我倒是可以理解。可太后也跟永安王不和?”
“前朝太后,当朝的王爷,你觉得他们应该和睦?”
好像……
不应该。
凌小悠动了动嘴角,“你继续说。”
“至于右相。他们虽然都是陛下信赖的人,可这中间还是要分一个亲疏。”
乔彴说的模糊,可凌小悠却听的明白。
直白的说,这就好比小的时候,孩子们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你是爱爸爸多一点,还是爱妈妈多一点。无论选择哪一个,另外一个都会十分的伤心。
如今陛下就面临同样的问题,只不过这回一个不是妈妈,一个也不是爸爸。
搞基也根本生不出这么大的儿子,所以说连直系血亲都算不上的关系,相比之下就没有公平可言。
而永安王曾经救过陛下的命,这关系自然就会被信任的更多一点。
再加上永安王位高权重,自然也会在很多事上都会碍手碍脚。
凌小悠眸色一沉:“所以你的意思是,栽赃陷害?”
“不无可能,不是吗?”乔彴目光灼灼的说道:“你也不能说,这案子没有诬陷的嫌疑。如今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在永安王一个人的身上,难道不值得怀疑吗?永安王如若真的是幕后主使,难道他不应该把所有痕迹擦的更加干净一点吗?而且一旦永安王出事,军中必然动荡,他的门生必然不会坐视不管。”
凌小悠想了一下,“我同意你的看法,你说服了我。一个人做任何事最忌讳的就是偏颇,而感情用事也是其中的一种。不过你的理由说服了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我接受你的看法。”
“那你之前以为我会感情用事?”
“这要问你自己。你提到永安王的时候,语气中不仅有着敬佩之意,还有着一种极强的信任感。无不透着一股“那些说他不好的人,大概永远不知道他的为人有多好,多正直,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谴责。”
乔彴怔怔的看了凌小悠片刻,“我之前的表现……那么明显?”
凌小悠下巴微微一抬,“你说呢?”
乔彴一时间没了声音,似乎在自我反省着。
而凌小悠却自顾的继续说道:“永安王这个人做事虽然出格,但从你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的性格爱憎分明,有胆识,有谋略,有能力。现在有两种可能:一是,如果他是幕后主使,我们需要知道他的作案动机。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如果真的是他做的,总会有个原因吧?而且他既然冒险做了这事,那付出和回报一定会是等价的。我们需要找到这个等价的点,来证明你手中证据的真假。
二是,如果永安王他不是凶手,那些指向他的证据又是谁布下的?是不是军需造假案的幕后主使者?还有你手中的证据,你是如何查到的?这证据的来源,值得相信吗?”
谁知凌小悠话音刚落,乔彴就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信他。”
他?
凌小悠和他对视了片刻,周围又一次陷入一片沉寂。
只有风从窗口涌了进来,将兄妹俩的发丝吹的盈盈而动。
“你说的他是谁?给你证据的人?”
乔彴看着少女那长长的睫毛浓且卷翘,低低覆在她那双漆黑的眼眸之上。
阳光透过窗棂在她的眼睫上滑过,光华幽微的闪动着。
女孩脸上的稚嫩,丝毫没有影响她话中的犀利。
“是。”
凌小悠冷声笑了出来,“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就你手中的证据而言,说永安王有可能是被栽赃陷害的人是你。如今掷地有声的说这证据存真的人也是你。你知道这两者之间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证据是真,那永安王必定不会无辜被陷害。如果他是被陷害,这证据之中一定会有问题。现在你需要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乔彴此刻的内心也是十分的矛盾和纠结,这也是他一直想要寻找的答案。
“我手里的证据有三个。一是手书。我们截获了郑平东给永安王写的亲笔信。”
“写了什么?”
“一切安好,王爷勿念。属下之忠心,日月可鉴。易林拜上。”
“易林?”
“郑平东的表字。”乔彴解释道。
这手书不长,也没有透露出更多的信息。就像一封定时请安的折子,可如果只是一封请安的信件,这语气又太过奇怪了。
试想一下,谁会在一封请安的信件中时时刻刻的表忠心?
再说他安不安好,为什么会得到一个王爷的关心?
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两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可这句里行间又让人怎么感觉有着几分疏离感呢?
“郑平东是永安王的下属?”
乔彴摇了摇头,“不是。永安王戍边之后,他的亲信都在滇南。宛平水师是七年前组建的,就官职来说,也不分属永安王。”
“那他为什么用属下这两个字?”
“如果只论官职的高低,他是可以这样说的。”
凌小悠那清素的眉角微微一挑,“那如果换做你,你会用属下之忠心这五个字给永安王写信吗?既然不是永安王的下属,为什么不称呼我,臣,在下……偏偏说属下?”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说郑平东和永安王的关系不一般。”
“是郑平东的这封信给人的感觉,他和永安王的关系不一般。至于是事实,还是故意为之,需要佐证。难道他们之间就没有别的手书了?”
“没了。”
“只有一封?”
乔彴抿着嘴角,点了点头。
凌小悠皱着眉头道:“这一封手书能说明什么?难道他们之间就没有其他的信件往来?”
“应该有。只不过之前没有人截到过。”
我呵呵。
凌小悠嘲讽的抖了两下嘴角,“所以呢?这封手书的真假都要另当别论,能当什么证据呢?说说你的第二件证据。”
“是一笔银子,一笔一百六十万两的军饷流向。”
凌小悠想了一下,没头没尾的一笔军饷也能联系到永安王,难道是——
“这比军饷的流向是滇南?永安王手握军队?”
“是。”
“那你能确定这比银子的源头吗?”
“就是这批军需造假其中的一部分牟利。”
“怎么确定?”
“我手里还有一本账簿,闽州六郡近三年来军需造假的所有明细。而且这笔银子我查过,进了滇南之后,却没有出现在户部和兵部的账簿上,所以这笔银子根本对不上账,户部没有拨款,兵部没有运银。这是一笔脏银。”
凌小悠深吸了一口气,“所以你认为这笔银子就是军需牟利的脏银?”
“数目能对上,时间也对得上。”
“但你却没有直接证据。”凌小悠眸色沉凉的看向他,那一眼乔彴似乎能感觉到一盆冷水已经挂在了他的头顶,随时准备当头淋下。
“你现在只能说这笔军饷来历不明。至于闽州六郡近三年来的军需造假明细,你也说了,这一百六十万两白银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牟利。那也就说明,闽州六郡近三年来军需造假的牟利大于这一百六十万两白银。所以你所说的数目并没有对上,至于时间?一句巧合足够将你手里这些证据都变成废纸。
四哥,你手里所谓的三个证据只是三个线索。证据可不是模棱两可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