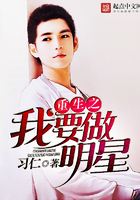邢博特拿着链子把小白挂在门后,邢永宪又去单位了,领导总是忙的,还好家人已经习惯,单身的,自由的,忙碌的,落寞的,又能如何,我只能更好地活下去。幸好先离开的是你,倘若是我先离开,留下你承受相同的煎熬,我不忍。以前没有觉得你多么好,现在感到你的好,你走了,再不肯回来再看我一眼,我的世界变得空白。
你我太晚相遇。失落,不是因为你是最好的,怀念,是因为永远失落,所以才因为失落而怀念。我的爱,发现爱了,来不及了,你不在了。总是这样,总是这样。
“精神不大好,我去房间里睡。”付天怜的力气好像被谁一针筒抽走了,掀开毯子的力气都无。
“姐姐,你看起来脸色很难看。”小白说。
邢博特摸摸它的头:“别吵,乖点。”
付天怜双脚着地,双脚却一软,瘫软在客厅的大理石地面上。
“我抱你。”
付天怜搂着他的脖子,他总是这样温和,眼神、动作、说话,他不是韩旭,韩旭是夏天霸道的雷雨,他是春天的绵绵细雨,有条不紊。但眼睛忽然睁不开,放到床上时,邢博特吻她,不是额头,是嘴。
“请我来替你生病。”邢博特关好门。
付天怜依稀感觉窗帘被拉上,没有阳光照到感觉舒服了些,那是她喜欢的深蓝色的窗帘,上面有星星月亮和太阳,只要一拉下,世界从此隔开,不要复仇,不要情敌,不要离弃,只是要那些昏暗的奢侈的睡眠。
我怎么会这样?付天怜睡了过去,仍有梦,那个黑漆漆的地狱,席伟剑拿着一盏灯喜悦的表情,还有姑姑付青珠,两朵云在互相追逐,一个长发女人穿着薄纱,付天怜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让人敬畏的美,嘴唇也掩饰不住那些微笑。
那盏灯,在黑暗中的光芒那么温暖,照着的每个人的脸上满是希望。空空色色,付天怜不明白,她只是听到两个字,妖折。
什么意思,谁说的。
妖折?夭折?
年少而亡;短命,那孩子夭折了,事情中途废止。太刚正则易断,太完美则易夭折。
昏沉中,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想听。头很痛,心也很痛。好像有些恐惧,但又不知为何而惧。我是谁,要干什么,身体好像有另一个自己要冲出体外。
医生来了,这次可不是山羊胡,是个女医生,邢博特CALL来的,中年,认真地问了问付天怜的详细情况,也说不出个之所以然来。
她不是兽医。
开了感冒药、退烧药、咳嗽药,吊了瓶,在门外看电视,邢博特拿水果给医生吃,一边询问着病情和注意事项。
付天怜用左手打了韩旭电话,仍然在通话中。十分钟了,打了十次,每隔一分钟打一次,十次的结果都是如此。
韩旭在跟崔雪通话。
“给我十分钟,只要十分钟,以后我永远不再有任何非分之想,回到我原来的位置,我只要十分钟。”崔雪蜷缩在公用电话亭。这里,没有养父母的窃听,动感地带的服务密码养父母是知道的,每隔三天都要查一次短信、通话记录。家里的电话都要严格查清单。而这一切都是崔雪忘了锁日记本后发生的,只有买了IC卡,坐车到远远的公用电话亭。
不管怎样,我都要努力争取,无论如何,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要去尝试,没有谁一生下来就属于谁。我不要将来后悔,哪怕被打击,受到挫折,我不要认命。
养父的话言犹在耳:“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在心里想,我恋爱,没有影响到学习是否就有可以恋爱的权利。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说出来了。
吃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耳膜嗡嗡的。
毕竟不是亲生的,崔雪夺门而去,不顾后面养母的叫喊,跑,也跑不了,天黑了还是要回家,而现在,只是想有多远奔多远。
一辆公共汽车停在站台,想也不想跳了上去,气喘吁吁地拿起钱包买票,售票员问,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我也不知道。
蹲在透明玻璃绿色顶棚的电话亭,手有点冻,但不至于冻到生冻疮的地步,也快了。用力地按了按那十一个数字,好像把自己的心都交了出去。
“你说吧。”韩旭拿棉签掏耳朵,还是耳朵舒服,开始还以为是付天怜打电话来了,等下再给她打问那只狗在她家是否习惯,然后以买些狗粮过去为借口看她是否一个人在家。估计不会一个人在家,那姓邢的。
“我,喜欢你,是真的。”崔雪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说,要喘不过气了。
“嗯,我知道,继续说。”韩旭拿着手机走近房间,他们都没起床,昨天半夜又听见那些奇怪的呻吟声音,像是在耳边,这狗屁房间隔音效果真烂,装修据说还是五六十万,打水漂。想建议老妈注意点影响,隔壁还有个无辜少年正处于青春发育期。
“其实我知道你喜欢的是付天怜,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你每次看我的时候,你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心里都好紧张,我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但我现在语无伦次了。”崔雪努力组织语言。
“so?”韩旭觉得崔雪的语气很怪。
“我知道你不会喜欢我的,但我喜欢你,怎么办啊?”崔雪蹲在地上,电话的钢线拉得笔直,“我不漂亮,但我努力地靠近你,每天买两份早餐,希望你偶尔没吃早餐的时候可以递到你手里,我也不会织围巾但我努力地学,第一次送男生礼物,第一次为了你打扮漂亮,圣诞节是我最幸福的一天,你吻了我。可是现在,我一无所有了。我想你,想见到你,但是我更想念我的爸爸妈妈,不是养母养父,是我亲生的爸爸妈妈,如果他们知道我有喜欢的人,不会打我的吧。”
“你不要哭了,谁打你了?”韩旭站在阳台,阳光忽然暗淡,还是上午,却是带些阴森的冬天的气候。
“我忍不住要哭,韩旭,你愿意听我说话我很开心,我从来没有跟你这样长长地说话,我很感谢你。谢谢你,虽然不可能,我仍然是希望见到你,只要见到你,我就很开心了。不过没关系,开学后还是可以见面的。”崔雪泣不成声,为什么要哭。孩子在挨打中一天天成长,爱情在背叛中一点点坚强。
“可是,你还是别哭了好吗?”韩旭有点不知所措,“你在哪里,回家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
“那不是我的家。我从来都没有家。”崔雪拿手背擦了擦眼泪,“我今天想在外面走走。”
“嗯,也好。”韩旭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要不,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们见面?”
“不用了,十分钟已经到了,不打搅你,总之就是谢谢你听我电话,我现在好多了。感谢你,你第一次跟我讲这么多。”
“那,我挂了。”韩旭有点头晕,今天莫名其妙地头晕,眼前晃动黑色的影子,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难道是昨夜SY伤身?也不会啊,一天一次罢了。天知道这些年轻的身体里面一天到晚哪里来的这么多欲望。
崔雪挂电话后忽然腿软,扶着电话亭的边缘,眼前幻影重重,人群都变成蜥蜴的头,流着血,张着嘴,舌头都是黑色,幸福和苦难都是幻影。
邢博特送走医生,自己差点昏倒在沙发上,不会传染得那么快吧。邢博特的嘴角流出一缕白沫,像吃了洗衣粉。
孙小丽打来电话,邢博特接了,跌跌撞撞。
小白惊恐不安,绕着房间的门团团转,它嗅了嗅邢博特的脚,这个人到底是谁?
“你好,在家吗?”孙小丽在电话里道,“想跟你们见面。”
邢博特麻木地点头:“是的,我在家里,你可以过来。”
冬天,我们就要见面,彼此温暖混乱的幼稚的世界,假如魔不诱惑,我依然甘心堕落,魔给我借口,等待我醒来,青春已经不在。
韩旭朝付天怜家中走去。
崔雪朝付天怜家中走去。
孙小丽朝付天怜家中走去。
付天怜用防御术抵抗内心的黑影,而那股力量异常强大,似乎控制了少许,扶着床沿挣扎着起来。邢博特在客厅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
小白见付天怜出来,狂吠:“有魔,有魔啊。”
门铃一个接一个响。
“知道你生病的消息,我马上就过来了。”韩旭的眼神变得越来越迷糊。
付天怜看见韩旭发红的眼睛大叫:“快点走啊!”奋力摆手,“出去,出去!”
她并没有告诉韩旭自己生病了。
再进来的是崔雪,她接到韩旭的电话说在这里见面。
韩旭缓缓回头看看她:“你怎么到这里来?谁告诉你我来这里的?”
孙小丽紧跟到,看着邢博特,像旅途疲惫的人看着一只脆生生的苹果。
小白被拴得牢固,拼命地咬着那条坚固的链子。脖子勒出血,付天怜明白了一切,他们不是他们,他们只是被黑蜥魔控制灵魂的肉体,趁自己还清醒拿起电话给柏华子。
“你一定马上过来。我的朋友们都变得很奇怪,救救我们啊。”付天怜此时最信任的人只有柏华子了。
“我一定会过来。”柏华子接着电话,“我想他们大概是中了黑蜥魔的疯心咒。你们别太靠近。”
柏超超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找吃的了。她经常坐的那个沙发空荡荡。
付天怜的腹部膨胀,里面有一股洪水在暗涌。越来越急往上涌到喉咙口的时候付天怜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视线模糊,模糊中,邢博特渐渐走近,搭上她的肩膀,嘴唇强行上来:“你知道吗,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他算什么?”
付天怜恍惚中推开他,摇头,身体又不由自主地靠近:“我知道,我的心里是需要你的,在任何时候。”
付天怜的身体暴露在邢博特的眼中,他发红的眼睛,因为欲望膨胀得很大的瞳孔对准付天怜雪白的脖子。
吻下去。一路吻下去了。一直到脚趾,衣服是碎片。
吻到脚时,付天怜浑身颤抖发软,绝望的,是怎样的世界,仰头倒着看窗外的树叶,枯萎的叶脉,春天怎么还没来。那团黑影渐渐清晰,黑蜥魔的脸狰狞微笑,心里的魔鬼,放纵的恶念,终有报答。
孙小丽进来了。她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有一个人,邢博特。
邢博特看到付天怜两腿之间的血,他一阵幸福,而后面的陌生双手环绕着他的腰,回头,那是孙小丽的脸,一脸的无辜和渴望:“我第一次看见你,喜欢上你。”
孙小丽跪在地上,伸出肉色舌头,从后面吻邢博特的双腿之间,对付天怜道:“请让我与你分享。”
很多东西可以分享,一枚糖果、一个莲蓬、一只肥羊、一条美鱼。
唯独爱是不能分享的。如果愿意,除非是中了疯心咒。
崔雪和韩旭进行着最原始的姿势,那是最舒服的男上女下,崔雪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大,那是压抑很久的,在客厅的沙发上,抬头仰望,抬头见他的宽阔肩膀,那是放脚的好地方。
被占有的幸福,幸福地被占有,韩旭,定定地看着崔雪,她看起来苍白,惊恐,这刺激了他。
我给予她的爱,就连自己都不明白。
小白继续挣扎着,那条链子是用特殊钢做的,咬不断,不停缠绕,不停狂叫,它不要他们这样混乱,脖子被勒出血印更多,牙齿断了几颗,小白站起来,爪子抓门,叫声大得足以将房顶掀开。却无人敢投诉,顶多在心里诅咒一声,狗叫得这么大声,怎么不去住别墅。
人的声音也很大,混合着,客厅的、房间的、男人的、女人的,床上的、地下的、天堂的、地狱的。
婧的佛灯在手,希望就在手。付青珠感激地看着席伟剑,仍然是这个熟悉的男人,宽容、勇敢、坚持,却内疚,想说些什么,欲言又止,只有眼泪滑落。
遇见你的瞬间,我选择沉溺;你昔日为我受千般苦,我今日用万般宠爱来补偿;我欠你的,要用一生的爱来还。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是老天给的这次机会。”席伟剑伸出手拥抱她,真实、美艳憔悴的她。
地藏云:“无间地狱,粗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器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摩耶夫人闻已。”于是愁忧合掌,顶礼而退。
桑叶云最是高兴,但又担心,好不容易邂逅粉红棉花糖,现在又将离去。也好,也好,人生相逢如浮云。
“我要跟随我的主人去人间了。后会有期,如果我变成一个小男孩,如果抬头看你,你还会认识我吧?”桑叶云一脸认真与不舍。
“当然会。”粉红棉花糖在婧的脚下,抬头望它。
婧也是难得的笑容,小心护着那盏佛灯,桑叶云驾席伟剑徐徐前行,一边和粉红棉花糖说话,掩饰不住得意,“他以为我是不回来了。我定让他吃惊。”
到出口,准备互相道别。
婧仿佛看见奇宁仙期待的眼神,当我拿着佛灯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会拥抱我,一切又恢复如初。
谢雯在黑暗的魂池里看见了那盏佛灯。
谢雯在众冤鬼的叫声中听见春风拂面的付青珠说着以后的生活。
谢雯一跃而起,从婧的手中瞬间夺过佛灯,光芒四射,照着谢雯兴奋的脸,照着四周贪婪的手。
“还给我。”婧的喊声凄厉无比。
谢雯哈哈大笑:“我才是要重生的,付青珠,你肯定没有告诉你亲爱的丈夫你杀了我这件事吧,你得到了宽恕,我呢?谁来宽恕我,是佛灯,我知道,只有它。”
付青珠尖叫一声,捂着脑袋,头炸开,眼珠爆裂出眼眶。席伟剑看着谢雯:“你说什么,她杀了你?”
是的,还有我的孩子,我肚子里的孩子。我找不到她。谢雯咬牙切齿:“这样的机会应该给我吧。她这样的,走不出去的。”
付青珠对席伟剑道:“我是无法跟你去了的,罪孽深重。”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留恋又何妨,失去了的,注定是失去。那我何必为失去的伤心而伤心,为得到的喜悦而奔走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