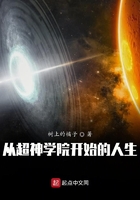在29路公交车上,他仔细察看着自己拿到的工作凭证。这只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上面潦草地写道:“持此凭证人为新抵达者,请为他考虑一份工作。”没有官方图章,没有签名,只有首字母缩写P.X.,看上去很不正式的样子。就凭这个能让他得到工作?
他们是最后下车的乘客。看到这个港区是如此之大——往上游看去,一眼望不到头——他们两个显得格外孤零零。似乎只有一个码头上有人在忙活:一艘货轮不知是在装货还是卸货,人们上上下下地在跳板上过往。
他向一个监工模样的高个儿男人走去,那人穿一身连体工作服。“你好,”他说,“我是来找工作的。安置中心那边的人说我应该来这儿找。我是不是该找你?我有一张凭证。”
“你找我没错。”那男人说,“不过,你做estibador[9]不觉得年纪大了点?”
Estibador?他看上去肯定是一脸困惑,因为那男人(工头吗?)身子一扭,表演哑剧似的拎起一袋东西甩到背上,脚步蹒跚地做出一副像是不堪重负的样子。
“哦,码头工人!”他喊道,“对不起,我的西班牙语不好。不过我一点都不老。”
是吗?他听到自己说的话是真的吗?难道他干重体力活儿还不算太老?他倒不觉得自己老,可也不觉得自己年轻。他没有什么特定的年龄概念。他觉得自己没有年龄,如果这可能的话。
“让我试试吧,”他提议说,“如果你觉得我不行,我就马上走人,不会有什么为难的。”
“好吧。”工头答应了,他把那张凭证揉成一团扔进水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这孩子是跟你一起来的?如果你觉得放心,他可以跟我一起在这儿等你,我会留心照看他的。至于你的西班牙语,这倒不必担心,只要坚持说下去,总有一天你就不再把它当成一门语言,而是世界存在的方式了。”
他转向男孩:“我去帮忙扛包的时候,你跟这位先生在一起好吗?”
男孩点点头,又把大拇指含在嘴里。
跳板的宽度正好可以走一个人。他等着那边的装卸工过来,那人背上扛着鼓鼓囊囊的麻袋,从跳板上下来了。随后他登上甲板,沿着粗重的木梯下到货舱。他过了一会儿才适应里面半明半暗的光线。货舱里堆着一模一样的麻袋,都撑得很鼓,有好几百包,也许有几千包。
“麻袋里是什么?”他问旁边一个工人。
那人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Granos[10]。”人家说。
他想问这袋子有多重,可根本没时间问,因为轮到他背了。
麻袋垛顶上是一个上臂粗壮、咧嘴笑着的大汉,他的工作显然就是把麻袋搁到一个个排队过来的装卸工人的肩上。他把背脊转过去,麻袋就落下来了,他一个趔趄,接着,就像其他工人那样拽住麻袋一角,迈出第一步、第二步。他真的能像别人那样,扛着这般沉重的东西爬上梯子?他有这份能耐吗?
“站稳了,viejo[11],”一个声音在他后面喊道,“不用忙。”
他左脚踏上梯子最下面一级。最重要的是平衡,他告诉自己,要稳住脚步,以防麻袋滑落或是袋子里的东西左右晃动。一旦里面的东西晃动起来或是麻袋滑落下来,你就玩完。你就做不成装卸工了,只能做一个乞丐,在陌生人后院搭起的铁皮窝棚里瑟瑟发抖。
他伸出右脚。他开始熟悉这梯子的特性:如果你将胸膛贴在梯子上,背上麻袋的重量不但不会让你失去平衡摔下去,反倒起了稳定身体的作用。他左脚探到梯子的第二级。下面传来一阵轻轻的欢呼。他咬了咬牙。要攀上十八级阶梯(他数过)。他不会失败的。
慢慢地,他一次攀一级,每一级都歇一下,一边倾听着自己心脏的狂跳(如果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可怎么办?那该有多丢人!)一边往上攀爬。爬到最顶端时,他身子摇摇晃晃,然后向前扑去,麻袋滑落到甲板上。
他站起来,指着袋子。“有人能帮我一把吗?”他喊着,竭力控制着喘息,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正常一些。有人帮着将麻袋举上他肩膀。
跳板本来看上去就挺可怕:随着船身颤动,它轻轻地左右摇晃着,而且这玩意儿不像梯子那样能有支撑的地方。他尽了最大努力稳住自己,走上跳板时直起了身子,可这样一来,他就看不见自己脚步的挪动了。他把目光盯在男孩身上,男孩一动不动地站在工头旁边看着他。我不能给他丢脸!他对自己说。
这回他没打一个趔趄就到了码头上。“左边来!”工头喊道。他吃力地转过身。一辆运货马车正慢慢停下,是那种低矮的平板车,拉车的是两匹蹄后丛毛蓬乱的大马。佩什尔马吗[12]?他还从来没见过一匹活生生的佩什尔马。它们身上的恶臭和尿臊味几乎将他全身裹了起来。
他转过身,让谷物包落进车斗里。一个头戴破帽的小伙子轻轻一跃跳上车,把麻袋拽到前边,有匹马拉出一堆冒着热气的粪便。“别挡路!”他身后一个声音在喊。是他身后的装卸工,他的工友,扛着麻袋跟在他后面。
他折回货舱又去扛第二个麻袋,接着是第三个。他比别的工友动作慢(他们有时要等他),但也不算慢得太多,一旦习惯了,身体强壮了,他会做得更好。毕竟,还不算太老。
虽然他总是碍着别人,但他不觉得人家对他有什么敌意。相反,他们总会说几句给他打气的话,或是往他后背上亲热地拍一下。如果这就是码头工的活儿,那也不算太坏。至少让人有些成就感。至少你是在搬动谷物,谷物将变成面包,那是生命的支柱。
哨音响了。“休息了,”他身边的一个人对他说,“你可以去——你知道。”
他们两个在货棚后边撒了尿,凑着水龙头洗了手。“有什么地方能喝杯茶吗?”他问,“或者有什么吃的吗?”
“茶?”那人似乎感到有些好笑,“我不知道哪儿有这东西。如果你口渴,可以用我的杯子,不过记得明天把你自己的杯子带来。”他把马克杯凑到水龙头下,接满了水递给他,“还得带一条或是半条面包来。空肚子干一整天活可吃不消。”
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接着继续卸货作业。到工头吹哨宣布一天作业结束时,他已将三十一袋货物从货舱扛到了码头上。也许按一整天计算,他能扛五十袋。一天五十袋:大约两吨的样子。不算太了不起。吊车能把两吨东西一下子搬走。为什么他们不用吊车?
“真是个好小伙子,你的儿子,”那工头说,“一点都不调皮捣蛋。”他称他为小伙子,un jovencito[13],无疑是为了让他感觉好。一个好小伙子将来也会成为码头工人。
“如果你们用吊车干这活儿,”他建议道,“效率可以提高十倍,就算是一台小吊车也行。”
“你说得没错,”工头说,“可那有什么意义?效率提高十倍有什么意义?又不是说有什么紧急的情况,比如需要紧急调运食物。”
可那有什么意义?这话听上去是一个真挚的提问,而不是扇在脸上的一个巴掌。“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精力用在更好的地方了。”他说。
“更好的什么地方?还有什么比供给人们面包更有价值的事儿吗?”
他耸耸肩。他本不该多嘴。他当然不会说:总比让人像负重的牲口那样扛东西要好。
“我和这男孩得赶快走了,”他说,“我们得在六点钟之前赶回安置中心,否则就得露天睡了。我明早可以再回这里来吗?”
“当然,当然,你干得挺不错。”
“这么说,我可以预支一些工钱吗?”
“恐怕不行。工薪出纳星期五才来。不过,如果你手头紧的话——”他去掏口袋,掏出了一把硬币,“给,你需要多少就拿多少吧。”
“我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我是新来的,我一点都不知道这儿东西的价格。”
“那就全拿去吧,星期五还我好了。”
“谢谢你。你真太好了。”
这是真心话。你干活的时候帮你照看年轻人,还把钱借给你:这可不是一个工头该做的事情。
“没什么。你也会这样做的。再见,小伙子,”他转向男孩说,“明儿一早见。”
他们赶到办事处,一个神色严厉的女人正要关门。安娜那个柜台里没有人。
“我们的房间有着落了吗?”他问,“你们找到那把钥匙了?”
那女人皱起眉头,“顺着这条路,第一个路口向右拐,那排长长的平房就是C幢。去找魏兹太太。她会带你们去看房间。再问一下魏兹太太,你们是否可以使用公共盥洗间洗衣服。”
他不禁红了脸,从这话里听出了某种暗示。他和男孩有一个星期没洗澡了,孩子身上都有股味儿了,他自己身上的味儿更糟。
他掏出那些钱给她看,“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有多少钱?”
“你不会数数吗?”
“我是说这些钱能买些什么?够吃一顿饭吗?”
“这里不供应饭食,只有一顿早餐。不过,你可以跟魏兹太太说这事儿,把你们的情况告诉她。也许她会帮你们的。”
C-41,魏兹太太的办公室,门紧闭着,和之前一样关门落锁了。不过,通往地下室的台阶拐角处有亮光,那儿孤零零地点着一盏不带灯罩的电灯泡,他迎面撞见一个小伙子,叉开两腿坐在椅子上看杂志。这人也穿着安置中心的巧克力色制服,不过头上还戴一顶小圆帽,脖子上箍着一条带子,像是街头耍猴戴的那种。
“晚上好,”他招呼说,“我在找那位实在难找的魏兹太太。你知不知道她在哪儿?这幢房子里有一个房间是分配给我们的,房间钥匙在她那儿,至少她管着总钥匙。”
小伙子站起来,清清嗓子回答他的问题。他回答得彬彬有礼,却毫无帮助。如果魏兹太太的办公室锁着,那就是说她可能回家去了。至于钥匙嘛,如果有钥匙的话,那也可能锁在办公室里了。公共盥洗间的钥匙同样也锁在办公室里。
“那么,你总能够带我们去找C-55房间吧?”他说,“C-55是分配给我们的。”
小伙子二话没说,带着他们沿着长长的走廊一路走过去,走过C-49,C-50……C-54,他们走到C-55了。他推了一下门。居然没锁。“你们的麻烦结束了。”他微笑着说了一句,就离开了。
C-55房间很小,没有窗子,只是布置了极少的几件家具:一张单人床,一个抽屉柜,一个洗脸盆。抽屉柜上面有一个碟子,里面搁着两块半方糖。他拿了一块给男孩。
“我们只能住这儿?”男孩问。
“是的,我们只能住这儿。不过就住一小段时间,等找到更好的地方就走。”
在走廊尽头,他找到一个淋浴间。里面没有肥皂。他把男孩脱光了,自己也脱光了。他们一起站到水龙头下,在不冷不热的细细的水流中,他尽可能把两人洗干净。然后,在男孩的等待中,他凑着细细的水流搓洗两人的内衣(水流变凉了,接着就变冷了),洗完后绞干。然后坦然地裸着身子,领着男孩啪嗒啪嗒穿过走廊回到房间,闩上门。他用唯一的一条毛巾把男孩擦干。“赶快上床去。”他说。
“我饿了。”男孩抱怨道。
“忍忍吧。我们明早能美美地吃上一顿早餐,我保证。想着那顿早餐吧。”他自己也缩到床上,吻了男孩向他道晚安。
可是男孩不肯睡。“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西蒙?”他轻声问道。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只是在这儿住上一两个晚上,等找到更好的地方就走。”
“不,我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他做了个绕圈的手势,指这个屋子,指这个安置中心,指这个诺维拉市,指所有的一切。
“你来这儿是要找你母亲,我是帮你来找母亲的。”
“找到她以后呢,我们来这儿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我们到这儿来,理由跟别人一样。我们有机会活着,于是我们接受了这个机会。这是一件大事,活着。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们非得在这儿生活吗?”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跟这儿相比呢?除了这儿没有别的地方了。快闭上眼睛,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