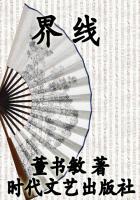卿汉禾又来拍我了,趁大家不注意,我一把扭住他大腿上的一块肉,压低嗓门说:“你再拍我一下试试看!是不是以为当着同学们的面我就不敢打你了?”卿汉禾的脸红了,他看了我一眼,终于让自己冷静下来。中午回去见到哥哥,很亲切,我放下书包就挤着他坐下了。嘻嘻一笑,我对哥哥说:“你真厉害!毛新国吓得一直趴在桌子上,就连下课都不敢出门了,怕碰上你又挨打。”哥哥斜了我一眼,摇晃着头说:“你不是一向横行霸道吗?怎么连那么个东西都斗不过呢?我瞪大眼睛说:“你是不知道,毛新国可凶了,我们班根本没有谁敢惹他。”哥哥说:“再凶也凶不过你吧?三天两头就给我难堪的人,出去可能怕谁吗?”我惊讶地问:“我哪天给你难堪了?”哥哥哼了一声,说:“装模作样!”哥哥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平时说他偷山楂的事,脸一下就热了。赶快转了个话头,我说:“知道吗?你走了以后我们班半天都没有人敢说话,对卿汉禾都客客气气的,生怕被你打。”哥哥点着头说:“好啊!你俩只管张牙舞爪地出去欺负人喽。”我摇着头说:“我才不会呢,他们只要不把我揪到台上去斗就行了。
”哥哥咂巴着嘴说:“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在昆明隔三差五你就有本事出去把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突然间你告诉我说狼不吃人了,这话谁信?”我争辩道:“那是因为他们打我嘛,难道让我呆呆地站着让他们打不成?”哥哥摆摆手说:“不要跟我解释,你是什么东西我还不清楚吗?把在昆明的那股子狠劲拿出来,我包你不出一个星期就可以在班上称王。”我小声地嘀咕道:“我又不是男生怎么能称王呢?”哥哥拖长声音说:“真难得你还记得自己是个女人啊!”哥哥又在拐着弯地骂我了,换在平时我肯定会说他偷山楂的事,但今天我忍住了。想着哥哥帮我打毛新国的事,我叫自己不要生气,还装出一副没听到哥哥说难听话的样子。往哥哥身边挤了挤,我问他:“哥哥,你今天下午要到哪里去?”哥哥反问我:“你问这事干什么?”我撒娇地摇晃着他的手说:“反正不管你到哪里,我都要跟你去!”哥哥哼了一声,挣开我的手说:“你少来跟我套近乎!”学校又出现一条反动标语,听人说标点符号都跟上次一模一样,堂哥已经被抓到很远的地方关起来了,他不可能半夜三更变成鬼跑回来写吧!两天后,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意外地见到堂哥,他正走在回家的小路上。
飞快追上堂哥,我拉住他的手,兴奋地问:“堂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堂哥说:“刚回来不久。”踮起脚尖看看堂哥的脸,我又问他:“他们给你抹黑脸游街了没有?”堂哥看着我,没有再说什么,那样子像在生气。不好意思问下去了,我依旧拉着堂哥的手,一路小跑地跟着他往家走去。妈妈正在堂屋做饭,一眼见到堂哥,她冲过来就拉住了他的手。妈妈的脸涨得通红,一个劲地摇晃着堂哥的手,说:“我就知道那事跟你无关!”堂哥看了妈妈一眼,委屈地说:“还不是因为叔叔有历史问题,学校这才怀疑反动标语是我写的。”妈妈说:“怀疑归怀疑,事实归事实,相信我们的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堂哥没好气地说:“反动标语又出现了,所以现在说什么都简单了,如果那人不再写,我这一生就毁了!”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管怎么说,回来了就好。”堂哥又看了妈妈一眼,不再说话。听到堂哥的声音,伯娘衣服都没扣好就从家里冲了出来,她嘴里“娘的崽哎娘的崽哎”地喊着,抓住堂哥再也不肯松手了。自堂哥被抓走后,除了上厕所伯娘一直躺在床上,她天天刮痧,刮得全身紫黑紫黑的,就像电影上的地下党被日本人打得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那样。
搂住堂哥的胳膊,伯娘的眼睛慌乱地在他脸上看来看去,看着看着,伯娘的眼泪滚落下来,她伤心哽咽道:“娘的崽哎!瞧你瘦的,是他们打的?”堂哥推开伯娘的手,心烦地说:“他们不打人咧,他们只让你活着比死了难受。”伯娘破涕为哭了,她一把抹去脸上的泪水,拍打着堂哥的肩头说:“不打就好不打就好,他们爱说么子让他们去说个够!”堂哥挣开伯娘,板着脸说:“你知道么子?”不等伯娘再说什么,堂哥一头就钻进了家里。下午我去扯草,很晚才回到家里。一进门,伯娘拉住我说:“四妹子哎,到我屋里呷饭,今日有鸡呷咧。”我高兴地点点头,顺手把篮子往堂屋里一扔就到伯娘家去了。伯伯在桌前抽烟,伯娘进里屋叫了声堂哥,然后去厨房端来一大盆鸡,又端来几个小菜。给每人舀了碗饭,给伯伯倒了一杯酒,堂哥坐下后大家便开始吃饭了。家里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伯娘给这个夹块鸡给那个舀勺汤的,一个劲地叫堂哥多吃。扭头看了我一眼,伯娘给我夹了一块大大的鸡肉,说:“四妹子也多呷些!”伯伯一直不说话,他低垂着眼帘大块地吃肉,把碗里的汤喝得稀里哗啦的响。
很快,伯伯吃完了,他张开手抹去嘴上的油,慢悠悠地卷好一支烟点燃。眯起眼睛吐出一口烟后,他问堂哥:“那反动标语不是你写的?”一听这话,堂哥的脸就涨红了,他生气地嚷嚷道:“我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绝对不会去做那种无聊透顶的事!”伯伯哼了一声,说:“以后不要到屋里来谈么子理想,你醒着梦着的想入那个球党,到头来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你抓走了。算你命硬咧!写反动标语的人又出来写了,他要不写不定那些娘卖×咯就把你拉去枪毙了,就是不枪毙,他们也会让你在牢里蹲一辈子,到那时我看你还说你的理想啦?”堂哥理直气壮地说:“乌云遮不住艳阳天!”伯伯哟嗬了一声,说:“现在雄了,有本事不要让人带走啊?你以后少到我面前耍嘴皮子!”堂哥不再吱声,拉下脸就往嘴里扒饭。伯伯沉沉地叹了口气,盯着窗外悠悠地说:“还是早些把媳妇娶到屋里来咧,生个崽你也就安分了,我活了一辈子么子党都不加入,到头来也不见哪个党来把我的球咬去了。
”堂哥严肃地说:“爹爹,你不要胡言乱语,说这种话会断送掉我的前途的!”伯伯骂道:“娘卖×咯我断送你么子前途?我是你爹爹会害你啦?就怕你为了这球的前途稀里糊涂把命送了都不晓得是么子事咧!”堂哥听不下去了,碗一扔走了出去,伯娘追出老远都没能叫住他。伯伯也生气了,他脖子一挺,用那只不中用的眼睛盯着小窗户吼道:“娘卖×咯有种你不要回这屋里来!”伯娘进门就跟伯伯吵了起来,“你索性跟那些土匪说说把我也拉去枪毙了,横竖我娘俩活着碍你的眼了!”伯伯哧溜吸了下口水,斜了一眼伯娘,骂道:“你撑多了是啦,凑么子热闹?”伯娘抹着泪出去了,嘀咕道:“我晓得我不入你的眼,只管去找小呀?”伯伯扯开嗓门冲着伯娘的背影吼道:“今日你有完没完?”我不敢坐下去了,端着碗擦着门边就跑出去。
学校的空气又变得紧张起来,大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悄声地在底下议论了,而是积极地投入到这场抓反革命的战斗中。每天都有许多新的线索,大家来学校的目的不再是学习,变成了破案,老师在讲台上讲课都挡不住同学们挤眉弄眼地说悄悄话。堂哥回来后继续教他的书,这就说明我们家没什么问题,加上新的反动标语出现,同学们的心思很快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再也不把我当反革命看待了。让我激动的是他们来和我讨论反革命的事了,告诉我他们的猜测,还问我是怎么想的。我不敢乱说乱讲,因为我没发现什么,也没亲眼见谁去写反动标语。尽管这样,我心里已经很愉快,起码我和大家是一样的人了,不再孤零零地让人看不起了。就在堂哥放回来的第三天,学校突然来了一个古怪的人,他穿得像山里人,但一看就不是山里人,眼神冷冰冰的。
他成天拿把扫帚这里扫一下那里扫一下,帽檐压得很低,眼睛东张西望,一看到你就让你紧张。说不出为什么,我很怕他,远远见他就想办法绕开,心里总觉得沾了这人会惹麻烦。回到家里,我老是想起这个人,便忍不住问哥哥:“哥哥你说,新来的那个打铃人会不会是个特务?”哥哥说:“白痴!这鬼地方怎么会有特务?看不出他是个警察吗?”我惊讶得不得了,问哥哥:“他是警察为什么不穿警察的衣服?”哥哥哼了一声,说:“就他那模样,穿上警服也像个贼!”我吓了一跳,小声地说:“你敢说警察是贼呀?”哥哥满不在乎地说:“你以为警察全是好人?告诉你吧!现如今披着人皮的狼大有人在!”我不敢再听下去,扭头就往门外蹿。哥哥在说反动话,如果让外人听到了还以为我跟他是一伙的,这事说得清吗?独自一人坐在红叶子树下,我想起宫建民和妈妈说的那些话,想起伯伯和伯娘说的反动话,还想起哥哥说警察是贼。可怕呀!除我之外这个家里还有谁是好人?万一他们被抓走了我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