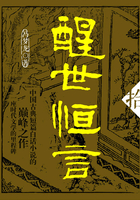我第一次对谭欣表白是又两个星期后,夏日傍晚,美院的宿舍楼下。两个小时有上千个女生出出进进,我还真认真比较了一下,最好的那几个也没谭欣好看。差不多十点半,我打算不行先回去,明天再来的时候,谭欣和几个女孩出来了。她们每人端着一个塑料盆,穿着夹指拖鞋从我身边过。我故意咳两声,除了她所有女孩回头,发现我不是熟人,继续前行。我追两步叫住她。她隐形眼镜摘了,都快贴上了才认出我,“咦?咦?咦?”地说不出话来。我说刚在附近办完事,路过你们学校,就过来看看。
“办什么事儿啊,这么晚才完事?”
“都是小事,拯救世界和平一类的。”
“顺利吗?”
“呃?不是很顺利,明天重启和谈。”
“行了吧。”她让同学先走,她等下追过去。“你不是说我消失到北京两千万人里,就找不到了吗?”
“但是美院只有三千六百名学生,这个好找一点儿。”
“有那么多吗?”仿佛真想一个个查出来似的,她想半天。那几个同学在浴池门口喊她,催她快点。她对我说:“我要去洗澡了,你要去吗?”然后她觉得这笑话不错,比我世界和平那个好玩多了,自己笑半天。
“你真请我?走吧。”
“你倒是有便宜就占。你早点回去吧,明天的世界和平还得靠你呢。”
“你多长时间洗一次澡?”
“你干吗?”她退后一步,审视我。
“我在这儿等三个晚上了,这是头一回见你出来洗澡。”
“胡说,我们还有一个门,好吗?”很快她抓住重点了,“你等三个晚上干吗?”
“找你啊。”
“你别弄得跟追高利贷似的,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回头看看,好像有人在后面叫我似的,背对着她快速说出来:“我喜欢你啊。”
“什么?你转过来说!”她把我身子扳回来。
“喜欢。”
“什么玩意儿?谁喜欢谁啊?”
“我喜欢你,我讲完了。”
她眯眼看看我,确定我这次没开玩笑,点点头说:“哦,我知道了,你走吧。”
“没了?”
“你要什么呀,我给你打车钱啊?”她问。
“我不要什么,但你发我张好人卡也行啊,许佳明,你人不错,又聪明又英俊,可我谭欣真心觉得配不上你。你这么说也能让我舒服点啊。”
她笑了,过了几秒说:“许佳明,你知道我讨厌你吧?被一个讨厌的人说喜欢,我也不好受。我得消化几年。”
“那我喜欢一个讨厌我的人,不是更难受?三生三世都消化不完。”
“有那么久吗?你先回去试试,下辈子还难受,就来找我。”
“你总给我留个电话吧,也不算我白来。这你怕什么呀?我又强奸不了你号码。”
她又哈哈笑几声,“这样,我说一遍,看你能不能记住,记不住就说明,咱俩真没缘分。”
十一个数字她一秒钟就说完了。我回味了半天,确实没记住。她往浴区看看,那几个女孩早进去了。她说她再不去,浴区就关门了。
“但是,我等三天了。”
她面冲我倒着走,一时心软了,许诺我:“明天再说行吗,许佳明?我跟你保证,明天一天,我吃饭、上课、洗澡,都从这个门走。”
5
我继父知道外面那个人叫钱金翔,我继父还知道林莎二十年前就想嫁给他,哪怕他有家室,只做小老婆也心甘情愿。但是人家没娶她,林莎嫁进了哑巴楼,这两个人还牵牵扯扯藕断丝连。有那么几年钱金翔消失了,和老婆孩子搬去外地。我继父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他们两口子带上许佳明,从此以后好好赚钱过日子。我相信林莎也是这么想的,我相信她还是把于勒当自己男人的。
只是那男人又回来了,正月刚过钱金翔又出现在长春,以前银白的头发基本掉光,但人还是这个人,那双深情的眼睛还是令林莎无法抗拒。他说他老婆冬天车祸去世了,他一下子老了十几岁。打击过后,他只剩下一个心愿,娶林莎为妻。这是最好的时间,唯一的机会。以前不行,他有家室,以后也没戏,他老了,活不了太多年了。
我不清楚他们怎么过来的,什么样的爱情,能让林莎打少女时代就苦守着这个有妇之夫,即使她做了妓女,即使她有了丈夫,她还是可以为这个男人随时随地地融化。一个月后林莎摊牌的时候,她对我继父写道:“老钱六十五了,快死的人了,这辈子总要做一次他的女人。”
谁都不是一开始就动杀机的。过完五十岁生日,我继父同意放手,让林莎跟他走。林莎在题板上写,一日夫妻百日恩,老钱有些积蓄,已经同意给他留二十万。我继父先写不要,犹豫下擦掉水笔字,写下了最差劲的一句话——给许佳明出国留学吧。
两人连写带比划,都哭得一塌糊涂,夜里他把自己的老婆送出门,对她打手语说,十年二十年后,这个人没了,我要是不死,就在哑巴楼等着你。五年的时光,林莎已经会一些简单的手语,她握紧拳头,拇指伸出来弯了两下,又指了指于勒,含着眼泪重复打这个手势,嘴里喊着谢谢你,谢谢你。我继父挥挥手,走吧,走吧。真是的,他想要的可不是这句话。
林莎和钱金翔打算去南方生活。出发以前她要再回家一趟,把衣物打包带走。上一次已经彻底分别,他不想再为她哭第二回。他请他最好的哥们郝叔叔报了大连的五日团,他算准日子了,老虎滩归来,家里就他一个人了。
郝叔叔跟我继父刚好互补,他只是哑巴,能听懂导游的介绍安排。他坚持要自己掏团费,不让我继父请他。他清楚我们家的状况,清楚这次的任务是要陪好于勒,帮他挺过来。在火车上他们就喝多了,于勒憋着火讲,他俩就在他眼皮底下,给他带了五年的绿帽子,五年的绿帽子!还好只是手语,这么大的怒气也没有把卧铺的乘客吵醒。
大连是东北第一旅游城市,被誉为北方明珠,能玩的景点数不胜数。头一天是金石滩,他俩在宾馆喝了一天酒;第二天是森林动物园,他俩在宾馆喝了一天酒。于勒跟他保证,明天老虎滩肯定出门,不能白来。然后他又说起了林莎,连喝两天他有些恍惚,他说我应该离婚的,我本来有机会的,我应该离婚的。
两种表达的又一区别,说话嘴瓢的不多,但手语着急了经常漏字。郝叔叔确定他原话是“我不应该离婚的”。他闭上眼睛,这几天他被折磨得够呛,不想再看于勒打车轱辘话了。小睡一会儿他被一阵晚风吹醒了,那是最惬意的时刻,躺在夕阳下的海景房,任凭海风把自己酒醒后的汗水吹干。只是那不是海风,是窗户和楼道形成的过堂风,有人把门打开了,有人回到了长春。
林莎两人是次日上午的机票,坐火车肯定来不及。大连到长春又没有飞机,于勒举块“到长春1500”的牌子站在路边,二十分钟后他改成“到长春2000”,一个尾号3330的出租车司机让他上了车。三天后警察奔赴大连找到这个人,他死也没想到,这个出手阔绰的哑巴是着急去长春杀人。
我相信他并不是想杀人,我相信他只是要争取最后一丝希望。我在拘留所见他时,他依然对林莎无法释怀。他跟我讲,他早该听林莎的,去离婚。隔着玻璃窗我打手语说当时问过林莎,你们的问题能解决吗?她说离婚,离婚就行,她不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女人。我继父看完我的话,气都喘不上来了。我有些绕晕了,如果你和林莎没离婚,她怎么可以跟钱金翔就那么跑了?
他哑语说,我俩离不了,因为我和林莎没结过婚,当年就办了酒席而已。
那她说离婚是什么意思,跟谁离?
他把椅子往前搬,仿佛怕我看不清他说什么似的。他哑语说:你知道吗,我从来就没跟你母亲离过婚,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娶林莎。
我被吓到了,我妈住进精神病院已经二十年了,我以为他俩早完了。我问他为什么不离。他一个劲地摇头。我说,你知道林莎过去是干什么的,她想好,不当小姐了,这辈子的理想其实很简单,就是嫁一个男人,跟他好好过日子,钱金翔那么多年没娶她,她跟你五年你还不娶她。你这样会让她感觉,她是你白睡五年的鸡。我眼睛有点酸,我跟他说林莎挺好的,对得起咱们爷俩儿,你不该这样,你不该让她命苦一辈子。
他直点头,我看见泪水一滴滴地往地上掉。
为什么不离婚,为什么不跟我妈先离了?他看着我手语答不上来。我拍拍玻璃窗,让他看着我:喊出来!你只是聋子,还不是哑巴!你给喊出来,你欠林莎的!你为什么不离婚!
我继父天生失聪,虽然理论上可以说话,可他无法明白那些音是怎么发出来的,语言的节奏有多奇妙。他嘴唇拱一个圈,他知道人家说“我”的时候,嘴唇都是这样的,鼓了半天才胸腔发出“吾”,像是被逼急的野兽。我在他面前打手语,喊出来,你个哑巴!他吼了几遍“吾”,又连说几声“不”,第三个音他知道嘴型,说了半天都听不出是什么字。我反复打,喊出来,你个哑巴!他努力对几次口型,失败后他干嚎着乱叫起来。
我右侧两个探监的家属和犯人扭过头看着他。关在铁北监狱的都是重犯,早晚拉出去枪毙的那种。可能和家里在十五分钟的探视里在强颜欢笑,报喜不报忧。而我的父亲的情绪让他们一下子绷不住了。一个中年犯人侧过身来对着我继父泪流满面,他们清楚,这个哑巴也要死了。
看守员过来架他双臂。他挣脱几下打着手语告诉我:我不跟你妈离婚是因为,离了婚,你就不是我儿子了。
他被看守员拉走,我看着他背影“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他听不见,我砸着玻璃窗冲他喊:“你个傻逼!这么大的事,你不找我商量拿主意,好像就你最明白!你他妈杀了人家两个人,毁了林莎她一生!你个老傻逼!”
6
我和谭欣第一次吵架是在798,好像是每年一届某种世界级的画展移师北京,让中国人见识一下二十一世纪的艺术家都在干什么。因为谭欣想去,我才想去。我不喜欢那次展览,798里的艺术品无非是点子和创意,而这本应该是最廉价的。他们处心积虑想标新立异,吸引评论家文化解读,让买家掏钱买走,我仿佛看见798的艺术家躲在画布后面偷笑。
上千幅画挂在展厅,旁边标注上百位画家的生平及成就。我想谭欣且得逛上几个小时。我出去抽烟,回来看见她还在,又出去抽烟,再回来她不高兴了,嘟着嘴问我,不是答应戒烟了吗。我跟她说我真戒了,只不过我刚才领悟到,上帝把一天二十四小时划分成一千个单位,有些单位就是给抽烟准备的,比如现在,陪你来没事干,就是老天赐给我的抽烟时间,不抽烟我会逆天的!
“我跟你说,你最神奇的一点就是,你总能把错误诡辩得理所当然。”她笑眯眯地说,“又不是让你陪我逛街,这是画展,文艺一点会死吗?”
我站在身后听她讲解波普、超现实、野兽、涂鸦,然后她如期中小考一般,指着一组问我怎么看。那是三幅油画,命名为《崇高一组》,头一幅是红白蓝三种颜色无序地铺满画布;第二幅更夸张,画一幅美国星条旗;第三幅呢,谁他妈把第三幅画偷走啦?那就是一张白画布,右下角是署名和落款。
“你让我说什么?”我问。
“谈谈你觉得哪里好?”
“我不觉得好,它不该摆在这儿,应该放在朝阳区环卫局。”
“什么意思?”
“垃圾就应该扔到垃圾站嘛。”
“你不用这么说吧?你可以看看这个艺术家的生平。”
左边有画家简介,一幅自画像,一脸的褶子,估计年纪不小了。下面是他的介绍,Lee Choi,1952—。真够装逼的,百十个单位介绍他一生。中国人,十几岁到美国学艺术。年轻时穷困潦倒,什么苦都吃过,难得的是坚持,2000年以后,年纪大了,人品也攒足了,他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顶尖大师。
“你想说什么呢?我无知者无畏,是吗?”
“我不想打击你,许佳明。术业有专攻,如果你不懂,就承认你不懂,没什么的,但你没必要说人家垃圾。每一幅作品都有它的立意和想法,就算与你无关,你也应该对他的思想心存敬畏。”
“头一幅,红白蓝三色,自由民主博爱;第二幅,美国是人类的希望;第三幅,一片空白才是崇高的本质,空无?禅宗的境界?不过如此,他把这些陈词滥调翻译成画,再沽名钓誉地等着评论家翻译回去,但还是改变不了它陈词滥调的本质。这能叫大师吗?”
“他是我偶像。”
“那你得抓紧时间换一个。”
她咬着嘴唇,鼻子一抽一抽的,我觉得她都要哭出来了。好像多大事似的,她转身往外走。我跟在她后面,穿过三条小路,一个池塘,翻过一座假山,经过798大门的时候,我说我错了。她没回头,看着街上的车说你没错,是我无理取闹。于是我又管不住我的嘴,我说:“其实我是真觉得我没有错。”
这时她停下来,转身问我:“许佳明,你有偶像吗?”
我过了一遍这二十二年,告诉她:“没有。”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骨子里是一个非常挑剔、非常刻薄的人。”
“那又怎样呢?”
“这样,你永远不会对这个世界有敬畏之心。”
好像喉咙被她扎了一针,她说得对,我能隐约感觉到这次不可以诡辩。就是不敬任何事,我觉得自己活得跟行尸走肉一般,没理想,没方向。但是,又能怎样呢?我想岔话题,哄她开心:“可能长这么大我只觉得,全世界只有你才是完美的。我说真的,没有油嘴滑舌。”
“有一天你也会挑我的缺点,不一定是缺点,仅仅我和你不一样的地方,也会被你说成可耻的缺点。因为你太聪明了,你真是万能青年旅店,什么都懂,什么都能一击致命。我会被你完全洗脑,认为过去的我就是一坨屎,你的生活才是最高尚的人生,我得努力去追赶才配和你在一起。你太可怕了。”
“我不会那样的,尽量不会。”
“那个画家,我的偶像,我十三岁看见他的作品,就此有了梦想。学绘画,考美院,坚持这么多年,这时候你来了,你用你的聪明三言两语就摧毁了我的偶像,但事实上,你在摧毁我一直坚持的东西,我的梦想,我的信仰。我没气你,我气的是我自己,我气自己刚才差那么一点点就被你洗脑了,那一瞬间我都考虑过,如果放弃画画,我谭欣还能做什么?”
“我知道我有多可悲,我一直以为这世界没有什么是值得我许佳明穷尽一生去追求的。我二十二岁了,我不屑A,不屑B,我都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要怎么过。但是,什么艺术、理工,我一眼就能看出这些行业的软弱和致命缺陷。我没法敬畏啊。”
她左右看看,跟我要支烟抽,头一口便呛得把眼泪都咳出来了。她食指揉揉眼睛说:“我们先冷静一段时间?”
我害怕了,双腿抖得站不稳。
“我不是说分手,那太俗了。我相信咱们俩肯定比那些人的恋爱高一个层次,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自己强大起来,等我明确鉴定,不会善变,才敢跟你在一起。”
“那是多久?一分钟?”我抬手看表,“五十九,五十八,五十七,五十六,那是多久?你告诉我,我什么也不干地等你。”
“别着急。这一个月没白过,起码你让我知道全北京两千万人,”她摸摸我头发,保证道,“只有你和我是天生一对。”
7
尸检报告表明,林莎和钱金翔死于十四日凌晨一点前后。我继父在钱金翔的箱子里翻出一张存折,不小的数目,他动了心。由于存折一定要在开户点取款,五个小时后我继父搭上了去松原的客车。在松原的银行职员李文娟后来对李警官交代,十四日上午九点半她在窗口等下一位客人,有人从窗口递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全取出来”。她开始还以为碰上了劫匪,准备弯腰取抽屉里的家伙。后半句她忍住没说,她早就把电棍和小刀藏在柜子里,银行枯燥的三年里她一直幻想能碰上一次抢银行,她见义勇为制服歹徒。她觉得那才是改变她命运的唯一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