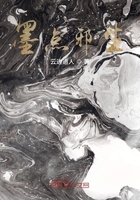村里的佃户长工们听着从庄大力家的传出的消息,都差点以为是天上掉的馅饼。
他们自幼在山下长大,经常出入这座不大不小的羽山,攀爬玩耍实则如履平地。
去山中剪裁花枝,还给工钱。
村里的妇女都想去报名参加,奈何人家归家只要五名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庄大力因着自家媳妇在归家做学徒工,更是率先抢了一个名额。
归承志见着每日的蔷薇花除了能满足之前的那个大户的订单,余下的还能接着去别处售卖,心里不觉放松了起来。随着天气的转暖,他也能听着归明月的话,每日清晨下床活动一下,月儿说那叫“做复健”。
归承齐则日夜不离的跟在归承志身边,小心搀扶,甚至抢过俞氏手中的湿毛巾给大哥擦拭身体。
俞氏一开始见着他就来气,后来渐渐的见他对自己大哥如此尽心,连日来操劳的小脸都瘦了。再加上俞氏本来也不是什么硬性子的,便很难再对他这摆脸色了。
归明月每日都来新宅子这边,眼见着堆山凿池,起宅竖墙,宽宽敞敞的十余间房舍,逐日而起。
前厅后舍皆全,房屋左端的那湾常年清澈满滢的溪流,也被分流了一小股,从西北墙角出迎入。
这下归氏的新宅子,便有了活水。
另外墙外种竹,墙内栽花,围起了篱笆,铺就了鹅卵小道……一应还有归鸿远特意挖得的一棵老杏树、一颗大梨树,前者种在了静雪的南窗下,后者还栽到明月的屋门前。
蔷薇枝剪到一个月,便开到了荼蘼。春天一过,大东朝的人们便鲜少簪鲜花了。不为别的,只为这夏日骄阳日渐猖狂,发髻上攒着的花儿,不出一个时辰便失了鲜活颜色。
归氏这边趁着这最后一个月的日夜兼工,赚了近五百两银子,五个帮工每人都得有十余两的尽显。也算是皆大欢喜了,临了,大伙推出了庄大力去归鸿远那里说项,大意无非是以后再有如此的活计,大伙儿保准是随叫随到。
搬了新宅子,归氏一家又免不了大大的操持了一番,设了流水席,宴请了村里的乡亲们。
看着归家眼下这气派,也算是方圆十里独一份儿了,就连那王大户家都不遑多让。
“归……大人,老朽有一事相求,还请归大人听老朽一言。”村里的庄姓人家最多,端着酒杯走到归鸿远面前,磕磕绊绊说这些话的是年近六十的庄老三。
“大叔,您有话但说无妨,就是别在喊什么大人了。”归鸿远赶紧起身说道。
“事情是今年我家大小子,本来在郡里给人做伙计赚了几个银子。可是回家来闷闷不乐,说他还是赚的最少的,远远不及人家那些识字的哥儿。还劝小老儿让家中的幼弟进学识字……”庄老三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可那些学堂都远在县城,小儿还小,每日步行来回县里,实在令人不放心;寄宿的话,这寄宿费又……哎,都怪小老儿没能耐。”
“庄老三说的对,归先生,听闻您之前在县衙做主簿,想必也是功名在身、学识渊博,这几个村子都一直就缺着一名教书先生,万望您出山啊!”